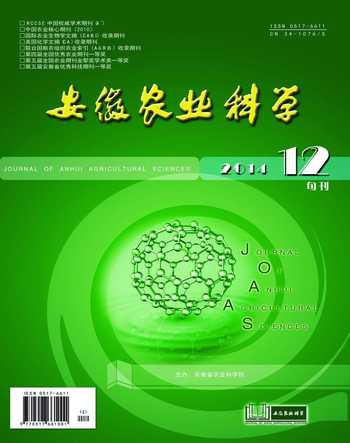三江平原佳木斯草溫和雪溫變化分析
呂紅玉 張宏茹 李文福 魏迎
摘要利用2007~2011年佳木斯逐日草溫、雪溫、0 cm地溫、氣溫資料,研究草溫和雪溫變化規律。結果表明,近5年佳木斯年平均草溫和雪溫分別為5.7和-11.7 ℃,草溫最高出現在夏季,雪溫在春季;1年中5~10月觀測草溫,其他季節雪溫和草溫交替觀測,月平均草溫最高在7月,雪溫在4月,最低均出現在1月;1 d中草溫和雪溫的最大值均出現在12:00,到次日日出前后出現最小值。草溫和雪溫各季晴天時日較差最大,且明顯大于氣溫日較差;月平均草溫(或雪溫)與氣溫、地溫變化趨勢基本一致,草溫和雪溫與氣溫、地溫呈明顯的正相關,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990、0.999。
關鍵詞草溫;雪溫;0 cm地溫;氣溫;變化特征;佳木斯
中圖分類號S16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17-6611(2014)12-03659-04
作者簡介呂紅玉(1970-),女,黑龍江寶清人,高級工程師,從事地面、酸雨、生態氣象等研究。
自1968年起,儀器和觀測方法委員會開始收集儀器開發信息和業務化經驗,在技術會議期間會舉辦氣象儀器展覽,展出廠家最新開發的產品[1]。自動氣象站傳感器可達到業務要求的準確度,2007年佳木斯國家基準站新增了草溫(或雪溫)傳感器,進行草溫或雪溫觀測。由于近地面層的氣象要素存在空間分布的不均勻性和時間變化上的脈動性,因此下墊面溫度觀測包括裸露土壤表面的地面溫度、草溫(或雪溫)[2]。近年來,許多學者對草溫(雪溫)、地溫、氣溫及其之間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3-7]。如趙艷玲等研究指出草溫在夜間比地面溫度低,在秋冬季更容易達到0 ℃以下,草溫能更好地反映出形成霜的溫度變化過程[5];周曉香等研究發現草溫與地面溫度為正相關,草溫在不同季度的升溫和降溫速度與地面溫度不一致[6-8]。佳木斯自1948年建站以來,已經積累了60多年地溫和氣溫資料,筆者利用2007~2011年佳木斯逐日草溫、雪溫、0 cm地溫、氣溫資料,通過分析草溫、雪溫與0 cm地溫、氣溫間變化關系,進一步了解草溫和雪溫的變化規律,對判斷天氣現象(如露、霜)很有意義[9]。
1 資料與方法
在沒有積雪的季節,依據《地面氣象觀測規范》儀器安裝的規定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表安放在地溫場內,草溫傳感器安裝在地溫場西側,氣溫安裝在百葉箱內[2] 。在冬季,降雪后人工站地面0 cm溫度表安放在雪面上;當積雪淹沒草層,草溫觀測轉換為雪溫觀測。
在此使用2007~2011年三江平原佳木斯國家基準氣候站(130°18′E、46°47′N)逐日人工站地面0 cm溫度、草溫、雪溫、氣溫觀測資料,經過嚴格的質量控制得到原始數據,符合氣象探測環境和《地面氣象觀測規范》的要求,數據測量準確、真實。按12月~次年2月為冬季、3~5月為春季、6~8月為夏季、9~11月為秋季生成逐季序列以及年序列,通過變溫、變率、相關、回歸分析草溫和雪溫的變化規律,以及與其他氣象要素的相關性。
2 結果與分析
2.1草溫和雪溫變化特征分析
2.1.1 年和季變化。由表1可知,佳木斯2007~2011年平均草溫為5.7 ℃,年平均雪溫為-11.7 ℃;季平均草溫在夏季最高,為23.9 ℃,春季次之,為7.8 ℃,秋季為5.9 ℃,冬季草溫最低,為-14.4 ℃;雪溫在夏季沒有出現,春季平均雪溫最高,為-5.1 ℃,秋季次之,為-11.5 ℃,冬季雪溫最低,為-18.5 ℃。
2.1.2 月變化。由圖1可知, 一年中5~10月沒有降雪全部觀測草溫,2月積雪淹沒草層全部進行雪溫觀測,其他月草溫和雪溫交替觀測,雪溫比同季節的草溫低。佳木斯月平均草溫變化范圍為-18.0~25.1 ℃,月平均草溫最高出現在7月,為25.1 ℃,月平均草溫最低出現在1月,為-18.0 ℃;月平均雪溫變化范圍為-0.1~-20.0 ℃,月平均雪溫最高出現在4月,為-0.1 ℃,月平均雪溫最低出現在12和1月,為-20.0 ℃。采用變溫(當月草面溫度-上月草面溫度)來說明草溫月變化幅度,結果發現,4~6月草溫呈升高趨勢,其中4月變溫最大,為8.8 ℃;9月~次年1月草溫呈下降趨勢,其中11月變溫最大,為-11.0 ℃,這是由于秋季受蒙古冷高壓影響,深秋多東北風,時有寒潮發生,這與王琳琳等研究石景山站草面溫度變化特征分析相一致[10]。
由佳木斯2007~2011年11月~次年4月平均積雪深度和雪溫實際觀測日期(表2)可以看出,佳木斯11月中、下旬開始降雪,月平均積雪深度2.9 cm,在2009年11月14日和2010年11月12~13日降雪量大,造成積雪淹沒草層,轉換為雪溫觀測。隨著季節變化,氣溫逐步下降,冬季積雪融化圖12007~2011年佳木斯草溫和雪溫月變化慢,隨著降雪量的增加,12月平均積雪深度逐步增加至8.4 cm,觀測員應隨時巡視積雪深度變化,保證雪溫傳感器一半密貼雪中一半露在雪面。1和2月平均積雪深度達17.2和18.5 cm,1月大部分時間和2月份全部時間均觀測雪溫,3月隨著氣溫上升,積雪開始融化,如果露出草層應轉為草溫觀測,所以在初春、初冬季節,隨時注意早溫和雪溫觀測的轉換。
2.1.3 日變化。利用佳木斯2007~2011年逐時草溫和雪溫資料分析發現草溫和雪溫日變化基本一致(圖2),草溫和雪溫的最大值均出現在12:00,以后溫度逐漸下降到次日日出前后出現最小值。由草溫日變化曲線可以看出,05:00~11:00草面溫度呈升高趨勢,其中06:00~10:00升幅較大,這是由于日出后隨著太陽高度的升高,太陽直接輻射和散射輻射逐步增加[11-13],草層由于吸收的熱量大于草面所支出的熱量,輻射差額為正,使草面升溫,08:00變溫最大,為3.94 ℃;13:00~次日03:00草面溫度呈下降趨勢,其中15:00~19:00降幅較大,16:00變溫最大,為-2.87 ℃,21:00~次日03:00降幅較為平緩,04:00變溫最小,為0 ℃,這是由于午后太陽輻射的進一步減弱,草層所吸收能量逐漸減少,草溫逐步下降,到日出前后,草層由于草面水汽凝結所收入的熱量與草面所支出的熱量接近平衡,使草面溫度變化平緩[14]。比較草溫和氣溫日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夜間草溫比氣溫低,在日出后06:00左右草溫和氣溫基本相同,草溫比氣溫升溫速度快,在11:00~12:00,草溫比氣溫高出8.0 ℃,午后草溫逐漸下降,在17:00左右草溫和氣溫基本一致,隨后草溫快速下降,草溫比氣溫低2.1~2.9 ℃。
由雪面溫度日變化曲線(圖2)可以看出,08:00~12:00雪溫呈升高趨勢,其中08:00~11:00升幅較大,09:00變溫最大,為5.63 ℃, 03:00~次日03:00雪面溫度呈下降趨勢,其中14:00~18:00降幅較大,16:00變溫最大,為-4.03 ℃,雪溫降溫速度比草溫快;20:00~次日06:00降幅較為平緩,04:00~06:00變溫最小,為-0.01 ℃。比較雪溫和氣溫日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夜間雪溫比氣溫低,這是由于積雪層相當于土壤和空氣之間的一個圖22007~2011年佳木斯草溫、雪溫和氣溫日變化42卷12期呂紅玉等三江平原佳木斯草溫和雪溫變化分析絕熱層,使雪溫迅速下降,在04:00~06:00雪面溫度變化才平緩[15-17];在08:00左右雪溫和氣溫基本相同,雪溫傳感器一半裸露在空氣中,受太陽直接輻射的影響,比氣溫升溫速度快,在11:00~12:00雪溫比氣溫高出5.8 ℃,午后雪溫逐漸下降,在15:00左右雪溫和氣溫基本一致,隨后雪溫繼續下降,比氣溫低-4.1~-4.8 ℃。
將2007~2011年逐時草溫(或雪溫)資料分晴天、多云、陰天、雨天,以1、4、7、10月代表冬、春、夏、秋季,給出各季不同天氣狀況時雪溫、草溫和氣溫極值日變化統計結果(表3)。由表3可見,草溫和雪溫各季晴天時日較差最大,云越多日較差越小,雨天日較差最小,與氣溫變化一致;晴天時草溫夏季日較差最大,為34.1 ℃。最高草面溫度在一年四季比氣溫高,最低雪面溫度比氣溫低,草溫和雪溫日較差明顯大于氣
2.2 草溫、雪溫與氣溫、地面0 cm溫度關系分析
2.2.1草溫(或雪溫)、氣溫、地面0 cm溫度的變化特征。由圖3可見,2007~2011年佳木斯月平均草溫(或雪溫)與氣溫、人工站地面0 cm溫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16],年平均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5.2 ℃)>草溫和雪溫(4.6 ℃)>氣溫(4.1 ℃)。從季節分析,草溫(或雪溫)與氣溫的季平均值絕對差值夏季最大、冬季次之、秋季最小,這是由于夏季人工站0 cm地溫傳感器在土壤表面,太陽直接輻射地面溫度表升溫速度快,但也會有相當大的輻射誤差[14];草溫傳感器放置于草面或草層中(草高6~10 cm),植物覆蓋草溫傳感器使其溫度變化減小,造成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變化大于草面溫度,而氣溫傳感器放置在離地1.5 m高度處的百葉箱內(防止太陽對儀器的直接輻射和地面對儀器的反射輻射),所以夏季草溫比地面溫度變化小,比氣溫變化大;冬季雪溫傳感器放置在雪面上,由于雪面對太陽輻射的反輻射作用很強,雪的導熱率小,積雪層就相當于土壤和空氣之間的一個絕熱層,所以雪溫比它上面的空氣溫度低,也比裸露土壤表面及雪下土壤表面的溫度低[10]。冬季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和雪溫傳感器均放置在雪面上,所以冬季雪溫和地面0 cm地溫變化基本一致。春秋季節草溫變化與氣溫和地面溫度變化相一致,季平均值絕對差值最小。
圖32007~2011年佳木斯草溫、雪溫、氣溫、地面溫度月變化2.2.2 草溫(或雪溫)與氣溫的關系。利用佳木斯2007~2011年逐日平均草溫(或雪溫)與日平均氣溫進行回歸分析(圖4a),得到線性回歸方程為:Y=0.884 7X+1.183,式中,Y為逐日平均草溫(或雪溫),X為當日的日平均氣溫,其相關系數0.990,說明二者呈明顯的正相關,氣溫越高,草溫和雪溫也越高。年平均草溫比氣溫高0.5 ℃,從季節分析,草溫(或雪溫)與氣溫的季平均值之差,夏季相差最大,為2.3 ℃,冬季次之,為-1.9 ℃,春季為1.5 ℃,秋季相差最小,為0.3 ℃。
圖42007~2011年佳木斯日平均草溫(或雪溫)與氣溫(a)和地溫(b)線性擬合2.2.3 草溫、雪溫與地溫的關系。利用佳木斯2007~2011年逐日平均草溫(或雪溫)與逐日平均人工站地面0 cm溫度進行回歸分析(圖4b),得到線性回歸方程為:Y=0.934 6X-0.397 9,式中,Y為逐日平均草溫(或雪溫),X為當日的日平均地溫,其相關系數為0.999,說明二者呈明顯的正相關,人工站地面溫度越高,草溫(或雪溫)也越高。年平均草溫比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低-0.6 ℃,從季節分析,草溫比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的季平均值夏季相差最大,為-2.1 ℃,秋季次之,為-0.7 ℃,冬季為0.6 ℃,春季相差最小,為-0.2 ℃。利用2007~2011年02:00、08:00、14:00、20:00草溫、雪溫與同時間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比較分析(表4),發現草溫在08:00與地溫相差最大,比地溫高4.2 ℃,14:00次之,20:00與地面溫度一致;雪溫在08:00與地溫相差最大,比地溫高2.0 ℃,14:00次之,02:00與地面溫度一致。
3小結
(1) 2007~2011年佳木斯觀測資料表明, 佳木斯草溫年平均為5.7 ℃,雪溫年平均為-11.7 ℃。季平均草溫在夏季最高、春季次之、冬季最低;雪溫在夏季沒有出現,春季平均雪溫最高,秋季次之,冬季最低。一年中5~10月份沒有降雪全部觀測草溫,2月積雪淹沒草層全部進行雪溫觀測,其他季節是雪溫和草溫交替觀測,雪溫比同期的草溫低。佳木斯月平均草溫變化范圍為-18.0~25.1 ℃,月平均草溫最高出現在7月,最低出現在1月;月平均雪溫變化范圍為-0.1~-20.0 ℃,月平均雪溫最高出現在4月,最低出現在12和1月。
(2) 草溫和雪溫日最大值均出現在12:00,以后溫度逐漸下降到次日日出前出現最小值。草溫和雪溫在晴天時日較差最大,云越多日較差越小,雨天日較差最小;最高草面溫度在一年四季比氣溫高,最低比氣溫低,草溫和雪溫日較差明顯大于氣溫的日較差。
(3)月平均草溫(或雪溫)與氣溫、人工站地面0 cm溫度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從季節分析夏季草溫比地面溫度變化小,比氣溫變化大;冬季雪溫比它上面的空氣溫度低,也比裸露土壤表面及雪下土壤表面的溫度低;冬季人工站地面地溫和雪溫變化基本一致;春秋季節草溫變化與氣溫和地面溫度變化相一致,季平均值絕對差值最小。形成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近地面層傳感器和溫度表安裝高度、不同下墊面、儀器不同等造成的。
(4)草溫、雪溫與氣溫、人工站地面0 cm地溫呈明顯的正相關,其相關系數分別為0.990、0.999,氣溫和地面溫度越高,草溫和雪溫也越高。夜間草溫比氣溫低,在日出后06:00、17:00左右草溫和氣溫基本相同,夜間草溫比氣溫低2.1~2.9 ℃;夜間雪溫比氣溫低-4.1~-4.8 ℃,在08:00、15:00左右雪溫和氣溫基本相同,11:00~12:00雪溫比氣溫高出5.8 ℃。草溫在08:00與地溫相差最大, 20:00與地面溫度一致;雪溫在08:00與地溫相差最大,02:00與地面溫度一致。
(5)夏季草溫傳感器的下墊面植被的性質、高度以及傳感器在草面、草中的位置、太陽直接輻射傳感器、溫度表等原因是否對草溫、地溫觀測數據帶來誤差影響,以及這些影響的大小有待進一步研究。另外,草溫觀測場要求草高小于10 cm,冬季積雪淹沒草層就開始雪溫觀測,此時草高也許在1~10 cm,造成每年可能積雪深度不一,雪溫觀測高度也不一就開始雪溫觀測,這些影響將帶來多大偏差,也有待進一步研究。建議對草溫傳感器多層安裝、各種植被安裝、冬季雪深不同高度安裝進行對比分析,得出儀器安裝的正確方法,減少因下墊面植被和儀器安裝錯誤帶來的誤差。
參考文獻
[1] 章澄昌.氣象儀器和觀測方法指南[M].6版.中國氣象局監測網絡司,2005.
[2] 宗曼華,王曉輝,劉小寧,等.地面氣象觀測規范[M].北京:氣象出版社,2003.
[3] 賀慶棠,閻海平,任云卯,等.北京地區植物表面溫度的初步研究[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5(3):94-96.
[4] 沈瑾,羅慧,甘泉,等.西安世園會園區5-6月草溫與氣溫對比分析[J].陜西氣象,2011(5):22-24.
[5] 趙艷玲,李靜鋒,劉泳梅.利用草面溫度預報霜的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09(3):1248-1250.
[6] 周曉香,黃少平,劉冬梅.江西省草面溫度變化特征及與氣象因子的相關分析[J].江西科學,2009(8):517-521.
[7] 陳玲,張勁梅,李秀艷.東莞市草溫與地溫\氣溫的差異[J].廣東氣象,2010(5):274-278.
[8] 張景哲,劉啟明.北京城市氣溫與下墊面結構關系的時相變化[J].地理學報,1988(2):159-168.
[9] 賈楊,高春鈴.利用自動站草面溫度判定霜的形成[J].黑龍江氣象,2008(2):31.
[10] 王琳琳,苗鳳梅,李蓓莉,等. 石景山站草面溫度變化特征分析[C]//第二屆全國氣象觀測技術經驗交流會文集.北京,2012.
[11] 周淑貞,張如一,張超,等.氣象學與氣候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2] 孫學金,王曉蕾,李浩,等.大氣探測學[M].北京:氣象出版社,2010.
[13] 于梅,刑俊江,于洪敏.黑龍江省近46年的氣溫變化[J].自然災害學報,2009,18(3):158-164.
[14] 鄧天宏,王國按,焦建麗,等.草溫、0 cm地溫氣溫間變化規律分析[J].氣象與環境科學,2009(4):47-50.
[15] 鄭紅,蔣慧亮,潘華盛.黑龍江省氣候變暖及其影響分析[J].黑龍江水專學報,2007,34(1):82-85.
[16] 謝安,孫永罡,白人海.中國東北近50年干旱發展及對全球氣候變暖的響應[J].地理學報,2003,58(Z1):75-82.
[17] 李鳳云,王玉山,吳澤新,等.地面溫度與雪面溫度對比[J].氣象科技,2010(1):71-74.
(上接第3638頁)
[27] 張云林.天北麓的黃土堆積[J].新疆地質,1981,42(1):21-39.
[28] 張威,郭善莉,李永化,等.遼東半島黃土粒度分維特征及其環境意義[J].地理科學進展,2010,29(1):79-86.
[29] 孫東懷.黃土粒度分布中的超細粒組分及其成因[J].第四紀研究,2006,26(6):928-936.
[30] 孫東懷,鹿化煜,DAVID R, 等.中國黃土粒度的雙峰分布及其古氣候意義[J].沉積學報,2000,18(3):327-335.
[31] 郭峰,孫懷東,王飛,等.巴丹吉林沙漠地層序列的粒度分布及其組分成因分析[J].海洋地質與第四紀地質,2014,34(1):165-173.
[32] 陳惠中,金炯,董光榮.全新世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演化和氣候變化[J].中國沙漠,2001,21(4):33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