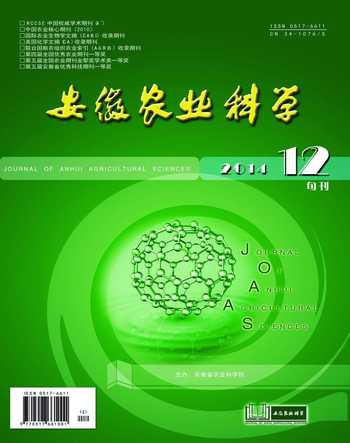中原貧困地區鄉村民間信仰及其對村民生活影響研究
張波 劉漫麗 賴韋文 向安強
摘要利用人類學田野調查手段,通過無結構訪談及參與式深度觀察,綜合社會學相關理論,以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小劉莊行政村為研究對象,圍繞民間信仰與村民生活的相互影響之主題,闡述中原貧困地區鄉村村民的民間信仰及信仰儀式的變遷,以及變遷過程中村民在生產、生活、人際關系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分析民間信仰對村民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認為鄉村民間信仰是一種維護農村生活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
關鍵詞村民信仰;村民生活;人際關系;中原貧困地區;小劉莊
中圖分類號S-05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517-6611(2014)12-03768-04
作者簡介張波(1973- ),男,廣東信宜人,講師,碩士,從事農業生態與三農問題研究。*通訊作者,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農村社會學、科技史方面的研究。
在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中,鄉村民間信仰儀式及其對村民的影響都在發生明顯變化。然而關于鄉村民間信仰儀式及其對村民影響的變化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研究,尤其是對北方貧困地區鄉村村民信仰的研究則顯得相對薄弱。研究中原貧困地區鄉村村民的民間信仰,分析其民間信仰的變遷與發展趨勢,有助于了解不同生活環境下,信仰對村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人際關系的影響。筆者利用人類學田野調查手段,通過無結構訪談及參與式深度觀察,綜合社會學相關理論,圍繞民間信仰與村民生活的相互影響之主題,闡述中原貧困地區鄉村村民的民間信仰及信仰儀式的變遷,以及變遷過程中村民在生產、生活、人際關系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變化,分析民間信仰對村民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1研究對象與概念界定
選取第二作者生活20多年的家鄉——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小劉莊行政村為研究對象。該村位于河南省東南部,經濟發展相對比較落后,約有村民103 戶,總居住人口約400人,主要種植小麥、玉米、大豆等農作物,人均年收入不足2 000元。鄉村管理有失規范,鄉村民居也無規劃,零零落落,樓房甚少。村西有兩座廟宇,近年有過修整,是村民祭拜的主要場所。
“民間信仰”的定義,大致有3種觀點:第1種認為民間信仰不是宗教,而是一種信仰形態。這種說法強調民間信仰的自發性和民俗性,否定其宗教的本質屬性[1]。第2種認為民間信仰本質上是宗教稱之為“普化宗教”[2]。第3種認為對民間信仰的界定不必太精確,相反模糊一點還更有利于研究的進行[3]。筆者認為民間信仰在本質上是具有宗教性質的,但不完全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苗月霞認為我國鄉村民間信仰可分為2種類型,一是外來宗教例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在鄉村的傳播,從而形成的正統宗教系統;二是我國傳統的儒、道等鄉村信仰的延續,包括鬼神和祖先崇拜的民間信仰系統[4]。該文所指的村民信仰為第2種類型,即鬼神和祖先崇拜的民間信仰系統,它包括普通民眾的神靈信仰,以及與此相關的儀式活動,它沒有明確的教義、戒律以及組織系統。
村民信仰是農村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村民的精神寄托,影響著村民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為人處事方式等等。概括而言,研究對象的村民信仰主要具有以下特征:①從意識形態上講,它是非官方的文化,是村民自發組織和發展的一種地方性民間文化。②從文化形態上講,它重在實踐、沒有具體的文字形式的規章制度并以地方的語言形式傳承[5]。③從支持對象上來說,它的信仰者中以村中的老年人及中年婦女占絕大部分,男性信仰者較少,并且少有的男性信仰者中90%的人年齡都在50歲以上。
2小劉莊的村民信仰儀式及變遷
變遷與消逝是人類學中最常見的2個概念,任何事物都存在于這2種范疇之中,民間信仰儀式也不例外。通過對小劉莊村民間信仰活動的調查,筆者發現民間信仰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于守舊與變遷的徘徊之中。村民信仰的主要對象是神、祖先和鬼,這些信仰儀式有一個共同的祭拜特點,就是燒香和磕頭,與村里信奉基督教的儀式——誦經唱歌有明顯區別,村里稱前者為燒香的,后者為信主的。前者的信仰活動主要包括廟祭、家祭、墓祭、歲時節慶、人生禮儀和象征等。在村西有2座廟,是廟祭的主要場所,村民一般在初一、十五去廟里進行燒香和活動。家祭相對簡單,大多數村民家里供奉有各種神位,如觀音、財神、灶神等。信仰基督教的儀式主要有周期性的聚會,即團契,場所或是在某位信徒的家里或是在教堂。村民信仰儀式的變遷不僅與村民的生活方式在不斷改變有關,也與村民的文化程度以及對科學的認知程度相關。非常明顯的是,在農村地區,信奉神或是基督教的村民絕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和老年男性,普遍具有學歷低的特點。
2.1祭天儀式及變遷老天爺是村里信奉者最多的神,除基督教徒不信奉外,其余村民幾乎過年時都會有祭拜儀式。虔誠的信仰者在每月初一、十五都會上香、磕頭,但儀式比10多年前明顯簡化。過年時的拜天儀式最為隆重,一般是在堂屋的正中間放上一個香爐,沒有香爐的則用類似香爐的器皿代替,為能固定香,器皿里一般放有玉米、小麥或草木灰。香爐的后面放有棗圓(一種過年時才有的面食,用面粉做出的花拼湊成一個圓,花上安放紅棗,非常好看),正對香爐的桌子上擺滿貢品,有水果、豬肉、饅頭、炸好的魚,還要再擺上一副筷子,這樣老天爺才能享受貢品。給神的貢品數量和擺放也很有講究,神三鬼四,給神獻水果或饅頭時,要3個放一堆,因為村民認為三是陽數,而四是陰數。擺好貢品后,就要放炮、點蠟燭、焚香、燒紙錢、磕頭。蠟燭一般要用紅色的,放在桌子的兩端,用蠟燭把分好的香點燃,據說香燃的越旺,老天爺就越高興,就越喜歡主人家的貢品,就會滿足主人的愿望。為神燒紙錢也要遵守神三鬼四的原則,3張疊在一起,稱一份。一份一份的燒給老天爺,磕頭也是3個、3個的磕,磕頭前,主人一般先向老天爺許下自己的愿望,祈求老天爺保佑。祈求的內容多為保佑家里出門在外的人健康平安、生財有道,祈求家里風調雨順、來年有個好收成。過年時祭拜老天爺的儀式在虔誠的信仰者那里一直保存到現在,但也有部分村民的過年祭拜儀式也很簡單,只焚香、不燒紙和磕頭,這些村民往往只有過年時才會在家里簡單辦個祭拜儀式,而平時不會到村廟里進行拜神的村民活動。該文第二作者的大娘(伯妻)是一位非常虔誠的信仰者,現在擔任著什么神的一個職位,傳說能夠與神進行溝通,村民大都深信不疑。以前,大娘經常與村里的那些同道信仰者出入廟里,每年都會到各個地方參加廟會,到各個地方燒香。但近10年來她已經很少去外地拜神,去廟里燒香的次數也很少了,并且在家拜神的次數也減少了很多,只有一些比較重要的節日才會參加拜神儀式。
2.2灶神祭拜儀式及變遷灶神在村里是一個重要的神靈,平時不祭拜,只有在年臘月二十三和大年初一的時候才有祭拜儀式。它的供位在每戶灶臺的上方,一般在墻上貼有灶王爺和灶王奶奶的神像,據說在年臘月二十三,他們會向玉帝奏報各家及家人的功過是非,因此每逢臘月二十三人們都供奉祭灶糖(一種黃色的像石膏一樣硬的黏牙的糖,用菜刀切成小塊)以封住灶王爺的嘴,使其上天后不能多言。但近年來,對灶神的供奉雖沒有消失,但祭拜的時候,很少有人家買祭灶糖來獻給灶神,也買不到這樣的糖了,大部分人不奉灶糖,或直接以平時吃的糖果來祭拜,或是買芝麻棒糖(一種白色黏黏的沾滿芝麻的長柱空心糖)來代替。
2.3喪葬儀式及變遷村民家中老人去世后,首先要舉行一個名為“摔盆”(瓦盆的底部鑿有很多洞,據說洞鑿的越大越好,這樣去世的老人就會少喝一點洗腳水)的儀式。這種儀式的過程是:老人的兒子抱著老人的紙牌位領著奔喪的親人到村里的廟前,然后燒香、磕頭、放鞭炮。此外,還會在對堂屋的門口外,設一個靈堂一樣的棚子,放有房屋型的紙扎,這些紙扎是去世的人在陰間的房子,房子前設有紙牌位,供親人行禮、祭拜。埋葬的時候,還會在墳前進行喪葬的招魂儀式,然后由孝子先填土,進行埋葬。現在的喪葬儀式有所簡化,由于禁止土葬,在家中設靈堂的儀式已經取消,但為去世者燒紙扎(企求他們在陰間能夠住的舒服,過得安穩)這樣的儀式仍然存在。
2.4清明祭祖儀式及變遷清明時節,村民們都會舉行祭祖掃墓儀式。到清明時,每家每戶都會折柳枝,并在家中所有的門兩邊插上柳枝,以表示對家中去世者的思念。并要到自家祖墳上插一個大大的柳枝(意為夏天快要來了,要為死去的先人遮涼),還要為祖先們添墳、燒紙、燒元寶(意在保證他們在陰間有錢花)。民間傳說如果去世先人們若在陰間過得不好,便會想念陽間的家,會經常回來的。近年來,清明祭祖儀式簡化了很多,它是村民信仰儀式簡化最為明顯的。
2.5叫魂儀式及變遷叫魂在村里是最經常發生的事情。經常被叫魂的是一些小孩,因為村民們認為兒童的眼睛能看到一些“不干凈”的東西,往往容易受到驚嚇。受到驚嚇的小孩會大哭不止,晚上睡覺不踏實,有的甚至會無緣無故的發燒,吃藥打針都不管用。村里人稱 “丟了魂”,此時就會請專人來“叫魂兒”,專人就是村里叫魂很靈驗的燒香人。小劉莊村里公認的叫魂最靈驗的就是前文提及的該文第二作者大娘(伯妻),她不僅能把丟了的魂叫回來,還能“看出”小孩是哪個地方被什么東西給嚇著的,往往被認為說得很準。叫魂儀式有2種,一種是在晴天,只需在地上畫一個十字,小孩子站在或是蹲在十字上,叫魂的人雙手合十,瞇眼,嘴里喊著“***(孩子姓名)的魂兒來吧”,一邊伸手向有太陽的地方抓,代表招魂兒,然后把手放在孩子的額頭上,如此重復幾次,最后說“來了,來了”,儀式就此結束。另一種是在陰天(村里人認為這種天氣情況下叫魂兒的效果不如晴天,但孩子的病不能耽誤),叫魂兒的人就會在自家堂屋的四方大桌上焚上香,點上蠟燭,嘴里念上兩句祈禱的話語,接下來就開始叫魂兒了。招魂兒的方向不再是手向天空抓魂兒,而是雙手像捧水一樣,捧蠟燭的火焰,嘴里念著“***(孩子姓名)魂兒來吧”,一邊把手放在孩子的額頭上,如此重復幾次,就完成了叫魂兒的儀式。據說有些孩子通過一次叫魂兒就真的好了,晚上不再哭鬧,睡覺也踏實了,也不發燒了。但有的孩子叫了幾次魂兒也不見好轉。盡管如此,村里的人還是普遍十分相信招魂兒這種說法。招魂兒的儀式少有收費的,大部分都免費。近年來這種招魂儀式仍在鄉村保留著,但由于村里燒香的人數減少,對鬼神虔誠信仰的人數也在減少,認為叫魂兒靈驗的人數也就就隨之減少了,導致招魂師人數銳減,周邊幾個村里的人甚至會跑到小劉莊找大娘去叫魂兒。
3村民信仰與村民生活
村民在鬼神崇拜、祖先崇拜中所展示的儀式活動顯示,人們對它們的信仰更多地是出自于自身的心理需求,人們通過某種儀式祈求消災祛病、風調雨順等。正如費孝通先生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對鬼神也很實際,供奉他們為的是風調雨順,為的是免災避禍。我們的祭祀很有點像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愿、哀乞。鬼神在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6]但是這種信仰的功利性,對村民之間的相處、人際關系處理以及村民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安徽農業科學2014年3.1村民信仰與村民的思維方式村民對神的堅定信仰,促使他們必須遵循一些準側,例如不能罵人、不能害人、不能偷東西等等,否則神靈就不會保佑他們,他們許下的愿也不能實現。這些行為和思想的約束很大的促進了村民間的和諧相處,同時這種信仰也是他們精神的一種寄托。但對于具有不同信仰的村民來說,這反而是一種人際交往的阻礙。
3.1.1 村民信仰的心理慰藉思維。村民信仰的功能方面,體現最為突出的就是心理慰藉功能。在社會生活中,人們總是要有精神寄托、心靈慰藉和心態的平衡,人人都向往和平幸福。但現實卻是人們往往遭遇無妄之災,在古代人們對生老病死以及超自然現象無法解釋,因此衍生出了“萬物有靈”。并延傳至今,人們對自然萬物、神鬼的祭拜產生了心理依賴,認為它們是萬能的,因此當遇到自身所無法控制的突發事件時便會求助于神靈,不管祈求是否有效,它們從精神上安慰了人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情緒、安定社會的作用,成為了一種安全閥[7]。前文提到,當村民在進行信仰儀式時,人們處于精神專一狀態,為了實現自己心中的愿望,就會在一個特定的場合下主動投入去信。儀式的神秘性加深了人們信的氛圍,以致在這一過程中產生出一種心理效應的回收,感到確實是接受到了某種強大的力量。這其實是信仰主體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它不僅僅為人們解脫自我開了方便之門,也為自己找到了一種回歸的方式,用一種膜拜至誠的手段,把自身的愿望融入到信仰儀式中,從而達到一種心理滿足[8]。
3.1.2村民信仰的功利性思維。不論是對神的信仰還是對基督宗教的信仰,大多數信仰者都帶著較強的功利性。這些信仰者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種宗教,常常基于祛病去災、求財得子等需求[9]。在小劉莊的信徒中,不少人都是在自己或家人患病的情況下開始信教的,其信教動機非常明顯,主要是想通過信奉神明而達到祛病的目的。該文第二作者的奶奶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早年,由于其爺爺哮喘病發作,其奶奶便開始了自己間斷已久的民間信仰;另外該文第二作者的母親也是在其父親經常身體不適的情況下,開始間斷已久的神的信仰。村里無論是信仰鬼神或是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在他們信教之前,一般都有長期求醫的經歷,在求醫無果后才將自己的最后一絲希望寄托于神明。此外,也有一些信徒是因為家里突遭變故或生活艱難無助,逐漸產生迷茫的心態,最終求助于宗教。也許與較強的功利性有關,不少信徒的信仰對象經常會發生變化。比如,有前佛教信徒在受到某件事情觸動后,又改信基督宗教或其他宗教了;也有先前信奉基督教后改信佛教的。這些信徒并不一定也不需要對教會宗旨有著深刻理解,很多人對要信奉的宗教基本教義都不甚了解,便在鄰居或朋友的勸說下加入該教了。
民間信仰的功利性特征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有需要,神就可以被創造出來[10]。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一些儀式在不斷地簡化,一些神被逐漸祛除,比如送子觀音,在醫學不發達的時候,求觀音送子是村民心里最靈驗的方式,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求觀音送子這種方式逐漸成為一種輔助手段。另外如今在小劉莊村里,最受歡迎的神靈往往不是那些處于譜系頂層的神仙,而是與民眾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的,或者是那些據說十分靈驗的神。當村民認為某一神靈幫助自己實現愿望時,會不惜花費重金為其塑金身、請戲班。這也是村里每年的重要活動之一,請戲班唱戲是現在最常見的感謝神靈的方式,村民稱之為還愿。
3.2村民信仰與人際關系民間信仰有利于增強人們的認同感和凝聚力,實現社會的安定統一[11]。在鄉村社會的人際關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從夜不閉戶到大門緊鎖,被盜事件不斷發生,這雖與社會發展和社會治安有著緊密聯系,但村民信仰對人與人之間信任的影響也是值得注意及研究的。前文曾論述,在每年的祭廟或紅白喜事中,村民都會祭拜祖先,通過對共同祖先的供奉,重申他們血緣上的聯系。
3.2.1村民信仰與人際信任。許多研究者均認為我國社會中的人際信任是一種差序格局的模式。王佳和司徒劍萍曾將人際信任具體區分為親緣信任、熟人信任和外人信任,指出信任水平從親緣、熟人到外人依次降低,并且宗教信仰對不同的人際信任類型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12]。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研究中國傳統社會時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來代表我國的人際關系格局。他認為,中國鄉土社會以宗法群體為本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以親屬關系為主軸的網絡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個人都以自己為中心結成網絡。這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湖水里,以這個石頭(個人)為中心點,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紋,波紋的遠近可以標示社會關系的親疏。整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制度安排和權力運作,都是以這樣的一種社會關系模式為基礎[13]。
農村人際信任也是延續著“差序格局”展開的。村民對親人和熟人的信任程度普遍比較高,主要體現在婚姻方面和錢財的轉借方面,與村民是否有神或基督教的信仰無關,但對外人或是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方面,兩者卻表現出了顯著的差異。有宗教信仰的村民更容易相信外人或是陌生人。近代社會學的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在《道教與儒教》一書中,也對傳統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格局做了精辟的論斷。他認為傳統的中國宗教——儒教和道教的倫理原則使得個人只信賴自己的血緣關系,只在自己的血緣團體中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新教則強調一種教內的信任與誠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分享,這些都有助于打斷氏族的紐帶,建立起一種優越的信仰共同體[12,14]。
此外,宗教參與行為越頻繁的教徒傾向于具有更高的信任水平。可能是更頻繁的宗教活動幫助個人更深刻地理解其宗教信仰以及更廣泛的宗教價值觀,從而減輕了只堅持教義對信任所造成膚淺負面影響。另外,認為宗教信仰越重要的人越能超越狹隘教義的束縛而具有高水平的信任,宗教活動參與頻率越高的人,與家人、親戚和朋友或者是陌生人的交往互動也越多,有利于增進互相了解,提高信任[12]。
3.2.2村民信仰與村民關系。村民之間的關系相對簡單,沒有更多的利益關系,主要是血緣關系為主。在村子里親人關系中的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受宗教信仰的影響變化十分大。正如楊慶堃在研究中所提到的,傳統的中國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都強調個人的修行;相反,基督教則更強調教徒之間的“分享”,強調每周固定的禮拜、聚會,特別是基督教的團契,“團契”一詞在《圣經》中為“相交”的意思,即相互交往和建立關系,旨在上帝與人之間的相交和基督徒之間相交的親密關系。通過基督教徒穩定的聚會,通過講經、交流體會、團隊活動,彼此間通過相互了解,達到感情的升華也增強了人的包容心[15]。相對于信奉鬼神的村民來說,信奉基督教的村民在村里的人緣更好,激烈的家庭矛盾發生次數也更少,另外非常明顯的就是夫妻間、婆媳間的沖突相對也減少了很多。
4結語
綜前論述,民間信仰是根植于老百姓當中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為表現[16]。在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形勢下,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復雜背景下,我國農村最容易出現所謂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諸如生產生活的不確定性、信仰價值體系不確定性、社會道德標準的模糊性等等。面對轉型期的各種“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很多農民感到精神迷茫、無所適從并充滿著恐懼與焦慮,而對穩定性的追求使得社會行為的主體對規范和意義系統表現出一種努力予以捍衛的慣性。然而,有些事件和經歷卻不容易在現存的意義系統之內得到解釋,因此,這些事件既威脅到現存的意義系統的普適性,也威脅到其穩定性。當人們無法通過現實生活中的信仰系統和制度化組織系統、文化系統、生產生活系統對自己的世界觀和生產生活意義進行建構并以此來理解周圍世界的時候,人們往往通過宗教獲取解釋。宗教之中的神靈被認為是正義和公正的化身,能夠為信徒帶來幸福和美好,消除現實生活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17]。所以鄉村民間信仰是一種維護農村生活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但農村信仰最終要形成什么樣的文化格局,需要更多的探索。
參考文獻
[1] 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5120;1999年彩圖珍藏本4543.
[2] 李亦園.文化的圖像(下卷)[M].臺北: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3] 路遙,迪木拉提,姜生,等.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研究的若干學術視角[J].山東社會科學,2006(5):20-31.
[4] 苗月霞.鄉村民間宗教與村民自治:一項社會資本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06(6):99-104.
[5] 王銘銘.中國民間宗教:國外人類學研究綜述[J].世界宗教研究,1996(2):125-134.
[6] 費孝通.美國和美國人[M].上海:三聯書店,1985.
[7] 蔡少卿.中國民間信仰的特點與社會功能——以關帝、觀音和媽祖為例[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32-35.
[8] 王淑娟,李朝旭.迷信的信息加工機制和心理安慰功能[J].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2):41-45.
[9] 邱國良.農村宗教信仰的特征與趨勢——以中部J省佛教與基督宗教為例[J].中國宗教,2011(7):62-63.
[10] 王燕琴.民間信仰對中國宗教發展的影響[J].宗教學研究,2006(3):215-218.
[11] 王存奎,孫先偉.民俗信仰與社會控制[J].民俗研究,2008(4):5-15.
[12] 王佳,司徒劍萍.當代中國社會的宗教信仰和人際信任[J].世界宗教文化, 2010(4):78-85.
[13] 費考通.鄉土中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4] 馬克思·韋伯.道教與儒教[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15] 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6] 金澤.能否和諧發展:民間信仰面臨的挑戰與選擇[J].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1):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