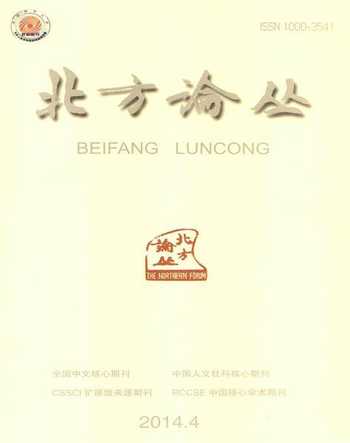南京國民政府對孫中山憲政思想的背離
李曄曄 孫紅艷
[摘 要]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標榜孫中山的憲政思想,開始實行憲政,從形式上看繼承了孫中山的憲政主張,但從實質上看完全背離了孫中山實現憲政的途徑、政權組織形式、黨政關系、三民主義等憲政主張,結果沒能挽救其失敗命運。
[關鍵詞]南京國民政府;憲政;孫中山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4)05-0090-05
[收稿日期]2014-06-30
1946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違背政協決議,于11月召開國民大會,12月25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元旦,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這部憲法。南京國民政府標榜是遵循孫中山憲政思想,從形式上看,南京國民政府是按照孫中山五權分立的形式組織中央政府的,但在憲政實施的具體過程中,卻背離了中山思想。
一、與孫中山實現憲政途徑的大相徑庭
孫中山對于憲政實施途徑有獨特設計。政實施前,必須經過軍政、訓政階段。該程序設計是經過長期探索形成的。同盟會成立不久,孫中山于1906年制定了革命方略,將革命次序分為三期: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1914年中華革命黨成立時,又進一步演化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在破壞時則行軍政,在建設時期則行訓政。”[1](p.89)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通過孫中山起草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再次確認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訓政時期的主要工作是實施地方自治,孫中山在革命方略中提出的約法之治,明確規定了地方自治是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部分,“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后,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2](p.297)孫中山認為:“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3](p.327)《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也強調:“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4](p.27)
孫中山憲政實施途徑是以訓政來完成憲政的前期準備工作的。在此階段完成地方自治,并在地方自治中培育人民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項權利,由地方自治達成憲政基礎,自下而上順利步入憲政階段。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實施過程表面上按照孫中山設計的途徑經歷了訓政,但實際上在訓政階段并未實現地方自治,即使如此,仍宣布進入憲政,背離了孫中山憲政思想。1928年8月,南京政府宣布進入訓政。訓政之初,南京國民政府以遵循總理遺教為名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但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背離孫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地方自治不但沒有成為憲政的基礎,地方自治的實施反而異化為南京國民政府加強基層控制的工具。20年代末,南京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訓政時期完成縣自治實施方案分年進行程序表》《縣組織法實施法》《鄉鎮自治施行法》等一系列地方自治法令、條例,并提出縣為地方自治單位,縣以下地方自治的體系為區鄉(鎮)閭鄰制,試圖造成完全遵循孫中山地方自治設想的假象。在地方自治推行方面,南京國民政府成績慘淡。至1934年,全國沒有一個省完成了規定的自治內容,“能達到預期的成績者,卻百不一見”,即使是自治稍有進展的省市,亦不過做到充分自治區域和籌設自治機關兩步功夫,關于自治精神和民眾福利所寄托的自治事業,絕未舉辦。”[5]在地方自治進展不利的同時,保甲制作為國民黨一黨專制的工具得到大力推廣。訓政開始不久,南京國民政府頒布了《保衛團法》和《清鄉條例》,到30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為了壓制革命在“剿匪區”推行保甲制,并逐漸推向全國。保甲與地方自治在性質上完全不同,本質上不相兼容。當時就有人敏銳地看到:“保甲制度與國府奠都南京后所訂立的一套地方自治制度,精神上是不協調的。” [6](pp.278-279)1939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新縣制,提出鄉鎮以下為保甲,實質上將保甲制改造成自治的基礎單位,對于新縣制實施的效果,時人認為:“縣各級組織綱要實行了三年余后,中國地方自治的實施的情況最大的特點是國家行政占據了縣各級組織最大部分的力量,以致自治行政沒有方法切實推動。”[7](p.123)
1947年,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進入憲政,此時全國沒有一個縣完成了孫中山要求的地方自治,恰恰相反的是保甲制托自治之名普遍建立,選舉、復決、創制、罷免四大民權毫無進展。由此可見,京國民政府雖然經歷了訓政階段,但卻沒有按照孫中山設想完成地方自治,待地方自治完成之后才能開始憲政的途徑,在地方卻始終沒有形成自治局面下,宣布進入憲政,當時就有評論指出,孫中山的遺教的憲政是“由下而上,由縣而省,最后及于中央,即是先有基礎而后有大廈的,合于科學的道里與政治原理;今天的憲政是自上而下,由中央而省最后才到縣,是空中樓閣沒有基礎的,是本末倒置有名無實。”[8]國民黨在獲得政權后,既要標榜繼承孫中山遺教獲取合法性,又企圖維持一黨專政,因此,對于地方自治采取了表面實施,實際上推行保甲制的策略,并巧妙地將保甲與自治糅合在一起,因為推行地方自治的過程也正是民眾民權意識覺醒的過程,顯然是與國民黨企圖維持一黨專政不一致,所以,訓政十幾年后地方自治仍然沒有成效,民眾更是無法享有四大民權,南京國民政府的憲政實質上是無源之水,毫無基礎可言。這種地方自治實施過程是對孫中山憲政思想的嚴重背離。
二、與孫中山憲政政權組織形式迥然有異
孫中山在規劃未來政體時,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是五權憲法論。1906年11月15日,孫中山在《與該魯學尼等的談話》中提出:“希望在中國實施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外還有考選和糾察權的五權分立的共和政治。”[2](p.319)12月2日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明確表示:“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的主義,叫做‘五權分立。”[2](p.331)孫中山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真正實現民權。考察了歐美各國政治后,孫中山認為:“在民權發達的國家,多數的政府都是弄到無能的;民權不發達的國家,政府多是有能的。”[4](p.321)英、法、美等國實行民權上百年,但現在所實行的民權與百年前沒有多大區別,“如果仿效歐美,一定是辦不通的。歐美既無從仿效,我們自己便應該想一種新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4](p.324)中國要實行民權,必須在借鑒歐美的基礎上,重新想出一個新的辦法,避免歐美代議民主制的弊端,改變人民對政府的態度,這個新的方法就是孫中山提出的五權憲法理論。1924年,《建國大綱》中明確指出:“在憲法開始時期,中央政府當完成設立五院,以試行五權之治。其序列如下:曰行政院;曰立法院;曰司法院;曰考試院;曰監察院。”[9](p.37)
概括地看,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是獨創的政體模式,其內容可分為:(1)權能分治、以權治能。權能分治理論將國家權力分為兩部分,一為政權、一為治權,人民享有政權,政府享有治權,“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4](p.345)在孫中山的設想中,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行使直接民權,以此來制約政府,“人民有了這四個權,才算是充分的民權;能夠實行這四個權,才算是徹底的直接民權。”[4](p.350)此即為以權治能,充分體現了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內容。(2)五權憲法。五權憲法是權能分治、以權制能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對于政府的權力,孫中山將之一分為五,“五權憲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各個獨立。”[10](p.29)雖然在形式上中央政府職權一分為五,五權中以行政權居首,但五權是相互平等、相互協作的關系,而不是分權學說所強調的制衡關系。
南京國民政府于1947年12月25日實施的《中華民國憲法》,標榜“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11](p.1104)進入憲政,但實際上完全背離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論。
首先,以權治能未能實現,民權未有成效,民眾依舊處于無權狀態,突出體現在地方自治未能實現及國民大會的職能方面。孫中山設想的以權治能,在地方層面,通過地方自治的實現使得民眾掌握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大民權;中央層面由各縣選出一名代表組成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憲政之下,民眾以此對政府進行制約,形成以權治能,政府必須依據人民意志行使五種治權。但實際上在南京國民政府進入所謂憲政后,民眾無權,一切權力與訓政時期相同,掌控在國民黨手中。一方面,地方自治未能實現,不但是革命程序論的背離,更是對孫中山民權思想的背離;另一方面,國民大會不能代表廣大民眾,并且無法做到對政府的有效制約。在國大代表的選舉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于1947年3月、5月相繼頒布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國民大會選舉罷免法施行條例》等相關法律,標榜選舉以直接選舉的方式達到公平、公正,但這都是表象,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完全由國民黨控制。國民黨不僅控制國民黨內的候選人,候選人的提名權控制在國民黨各級黨部手中,而且控制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經本黨代辦提名簽署之無黨派人士,各承辦選舉之同志盡力協助其當選。”[12](pp.282-283)在選舉過程中,國民黨各級黨部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動用軍警等強制力量操縱、改變選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不可能代表廣大民眾,恰而是國民黨操控的具。即使如此,國民大會對于南京國民政府仍然缺乏有效的制約權。《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于每屆總統任期前九十日集會,由總統召集。”[11](p.1104)總統任期6年,并且在《中華民國憲法》中沒有規定國民大會的常設機構,只是規定有四種情形之一時,國民大會可以召集臨時會:“一、依本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應補選總統、副總統時;二、依監察院之決議,對于總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時;三、依立法院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時;四、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以上請求召集時。”[11](p.1105)按照正常情況,國民大會6年中只能開會3個月,其他時間體現不了政權對治權的制約,很難達到以權制能的目的。
其次,五權憲法名實不符。在中央政府的機構設置上,《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實行五院制,從表面上看是繼承了孫中山的五權分立學說,但實際上在五院的關系上,卻與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迥然不同。在立法院的定位上,《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11](p.1107)行政院實際上是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的地位要高于行政院,行政院受制于立法院,而行政院卻不能對立法院有所制約,存在著單項的制約關系,頗有內閣制的特點。《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司法院有“解釋憲法,并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按照這一規定,司法院就擁有了對立法院、總統、行政院的制約權力。監察院又對司法院有制約權,并握有對總統、副總統的制約權。從《中華民國憲法》的內容可以看出,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政權形式上保留了五權憲法的框架,但實質上是回歸到西方三權分立的道路上來,孫中山創立五權憲法就是避免英美等國三權分立、代議制帶來的弊端,1947年頒行的憲法重回三權分立的模式是對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的背離。
綜觀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政府體制,國民大會完全為國民黨操控,五院制實為三權分立,不但不能實現孫中山五權憲法論中要求的權能分治、以權治能,相反南京國民政府以五權憲法繼承于孫中山遺教為由,將之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掩蓋一黨專政的裝飾,更具有欺騙性。
三、與孫中山的憲政黨政關系漸行漸遠
孫中山對于黨政關系有獨到見解。民國成立之初,孫中山一度傾心于西方的政黨政治,希望在中國能實現在議會民主框架下的良性黨爭,但終以失敗結束。此后,孫中山汲取蘇俄成功的經驗,提出了“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理念,“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后再去愛之。”[4](p.104)“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然后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民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12](pp.281-282)并且孫中山的“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理論與革命程序論有機結合,依據革命程序論規劃,軍政時期,以黨建國;訓政時期,以黨治國;憲政時期,還政于民,實現民主政治。
同時對于民主政治的實現途徑,孫中山一直以來是以實用主義態度實踐的。辛亥革命后,南北對峙,為了早日實現民主共和,孫中山讓出大總統位置。袁世凱倒行逆施,民國陷入存亡生死關頭,孫中山號召各地反袁,進而導致護國運動;袁世凱死后,中央政權落入北洋各軍閥手中,孫中山依靠西南軍閥的力量先后掀起幾次護法運動;在屢屢失敗后,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將一盤散沙的國民黨重新變成為主義、理想奮斗的革命黨。但就在國共合作,革命聲勢日漲,前途光明之時,孫中山在得知北京政變,毅然北上,并發表《北上宣言》,提出由各黨派、團體、反對曹吳各軍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決定國是,希望通過此舉能達到國內和平,實現民主共和的夢想。從孫中山的奮斗歷史可以看出,孫中山試圖用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民主政治的奮斗目標,并在具體實踐中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共同反對當時對民主政治威脅最大的政治勢力,強調將當時有政治活動能量的政治力量全部納入統一框架之內。南京政府于1947年宣布進入憲政,表面上頒布了憲法,實際上完全背離了孫中山憲政思想。
首先,在能夠實施民主政治的歷史關頭,國民黨只顧一黨私利,導致錯過和平民主的機會。1946年政協會議的召開為全國人民帶來了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會議通過的政協憲草得到中共和民主黨派的認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有望打破,社會輿論對國民黨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國民黨能夠按照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協議,沿著和平民主的道路前行,但國民黨內部關于政協決議的爭論一刻也沒有停止,1946年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會上政協協議內容受到抵制,并通過了《對政協報告之決議案》,提出5條與政協協議相反的憲草修改原則,推翻了政協確定的民主憲政原則,不久政協決議就被蔣介石撕毀,國共內戰爆發。
依據政協協議及其規定的程序,國民大會的召集需要在政協各項協議次第付諸實施之后,必須在和平環境中,由改組后的政府負責召集,各黨派共同參加,國大通過的憲法,應是政協審議完成的草案,召集日期亦由各方協商確定。但是,蔣介石為了標榜繼承孫中山的思想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和取得美國的軍援,加緊了“制憲”步驟,于1946年7月3日,單方面宣布當年11月12日召開國大,此舉當即遭到中國共產黨和中間勢力的反對,但國民黨方面置若罔聞。對于國民黨的非法國大,中共進行了堅決抵制。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民盟也對國大采取了抵制態度。許多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國民黨內民主分子代表,也紛紛拒絕參加國民黨的一黨國大。國民黨一黨國大于12月25日通過了所謂《中華民國憲法》,隨即宣告閉會。12月28日,周恩來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說:“蔣政府的國大和憲章既未經政協一致同意,又無聯合政府召集,更無中共和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和制定,我們及全國民主人士決不會承認它為合法為有效”[13](p.712)。從表面上看,南京國民政府召開了國大,頒布了憲法,但實質上卻違背了民意。在制定憲法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既沒有按照孫中山的設想,也沒有順應時代要求,仍然要將國家政權牢牢抓在手中,并沒有充分吸納其他政治力量參加國家政權,沒有實現對各種政治資源的有效整合,民主政治難以實現,不僅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而使矛盾進一步激化,只能說是頒布了憲法,沒有實現憲政。
其次,孫中山憲政思想強調的還政于民未能實現,仍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只是國民黨對于政府的控制更加隱秘。在訓政階段,國民黨通過《訓政綱領》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政治全權,對政府采取“以黨控政”的方式,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正式施行后,雖然從條文上取消了國民黨的黨治原則,但這絕不意味著國民黨要放棄原有的一黨專政地位。其實,憲政在國民黨的政治觀念中,僅僅是裝飾,但國民黨在統治方法上有所調整,提出了“以黨透政”的方針和實施方法。所謂“以黨透政”,即以國民黨黨員來參加競選,以全黨之力使之成為從政黨員,通過從政黨員使得國民黨的意志左右政府決定并付諸實施,實際上是以國民黨黨員治國。為了使得從政黨員能夠履行國民黨中央的意志,1947年4月,國民黨中央恢復了帶有明顯訓政烙印的中政會,企圖以此來監督從政黨員,同時對于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需要通過選舉產生代表的機構中的國民黨黨員采取嚴格紀律措施,在《中國國民黨當前組織綱領》中強調:“黨員出任各級政府之重要職務或參加各項重要職位之競選,須經黨之同意,并受黨之指導……不執行黨之政綱、政策、決議與命令者,予以處分;情節重大者,開除黨籍。”[14](pp.1173-1174)國民黨通過這種“以黨透政”達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南京國民政府在解放戰爭中節節敗退,國民黨中央加強了對政府的控制,其黨政關系回到“以黨控政”。1949年7月,國民黨中央又創立了非常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南京國民政府只是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的執行機構,“政府一切措施必須先經‘非常委員會決議通過,方為有效”[15](p.702),“非常委員會”的設立,是國民黨延續訓政時期“以黨控政”的形式,突出反映出國民黨視憲政為裝飾,積極維護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目的。
四、與孫中山憲政思想核心的背道而馳
孫中山憲政思想的核心即為三民主義。孫中山奮斗終身所為實現者是實現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在孫中山的奮斗歷程中有一個顯著的發展變化,辛亥革命前,民族主義內容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中華民國成立后,民族主義逐漸有了新的內容,《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義對于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4](p.118)民族主義不但要求反對國內的民族壓迫,而且反對一切外來侵略。
民權主義的主體為人民主權,孫中山在早年主張實行英美式的政黨政治,其實是以代議制的形式實現民權,也即間接民權,1916年孫中山提出直接民權的目標,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指出:“國民黨之民權主義,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也……凡此既以濟代議政治之窮,亦以矯選舉制度之弊。”[4](p.120)實現民權的途徑為革命程序論,即軍政——訓政——憲政次序,訓政期間培育民權,憲政時期民眾充分運用民權;五權憲法是民權決定下的治權結構形式,中央政府采取五院制,五院之間分工協作,國民大會代表全國民眾行使政權,以此達到以權治能。
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即提出:“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于國家,為國民所共享。”[16](p.552)概括而言,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以和平方式達成社會變革,通過核定地價,照價納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方式實現平均地權,其間并不采取激烈手段,以此實現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變革,最終實現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一是為了防止私人資本壟斷;二是發展國家資本,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對于孫中山憲政思想來說,三民主義既是如何實現憲政的指導思想,又是憲政實施后的理想狀態。南京國民政府在這兩方面都背離了三民主義的原則。
在憲政實施前的訓政階段,國民黨中央于1928年10月通過《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其確定的原則就是將政權交給國民黨,治權交給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會議負責指導監督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是國民黨將政權與治權全部掌控在其一黨手中。孫中山提出訓政時期“以黨治國”,并未拒絕其他政治力量的參政訴求,國民黨卻在訓政時期實行一黨專政,并且為了獨裁大權,對其他政治力量要求開放政權呼聲視若罔聞,一方面不斷拖延憲政開始實施時間,直斥民眾毫無憲政基礎,更對中共及中間黨派采取武力壓制,導致社會矛盾劇烈,國家動蕩不安;另一方面,卻對民權訓練陽奉陰違,訓政時期的國民黨掌握國家大權,非但沒有按照《建國大綱》中要求將地方自治完成,相反對于專制的工具保甲制情有獨鐘,其結果就是自治為保甲取代,對于孫中山民權主義要求培育的四大民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毫無進展,民權主義未能實現。孫中山要求在地方自治過程中核定地價、增價歸公,既能為自治籌集經費,又可以逐漸變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但南京國民政府一直未能實行此主張,同時依靠國家政權力量發展起來的官僚資本惡性膨脹,通過對金融、交通、工礦等行業的壟斷,官僚資本逐漸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
不但在憲政準備階段不是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在進入憲政后,三民主義也只是作為裝飾,根本未能實現。
在進入憲政之后,南京國民政府也未能實現三民主義。國民黨仍然實行一黨專政,不顧中共及中間黨派存在事實,一意孤行,將其他政治力量排斥于憲政體系之外。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雖然進入憲政,卻不斷強化軍事統治,在1948年5月實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中規定在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宣布戒嚴和發布緊急命令,不受憲法規定的限制,實際上在憲政體制下賦予了總統在政府中的獨裁權力和地位,使得蔣介石個人獨裁得到強化,即使蔣介石下野后,仍然保持著對政府的實際控制,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占據國民黨內及政府內的主導地位。進入憲政階段的南京國民政府地方自治并未實現,民眾未能掌握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四權,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在國民黨操縱下,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粉飾民主的工具,以權治能成為空話,甚至在南京國民政府頒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后,民眾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保障。全面內戰爆發后,南京國民政府大肆擴大內戰軍費,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導致社會矛盾叢生,國統區民眾進行各種形式的反抗,同時整個廣大農村經濟凋敝,封建落后的經濟因素占據主導,至憲政開始時,農村除了解放區外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生活極端困苦,國民政府在農村中的統治趨于瓦解。
從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憲政的過程考察,形式上繼承了孫中山的憲政思想,以孫中山設計的方向推行憲政,即由軍政——訓政——憲政這一程序過渡,在訓政時期實施地方自治,在行憲的中央政府制度設計上采取五院制,實際上卻背離了孫中山的憲政思想。雖然強調實施地方自治,但在地方自治實施過程中,以保甲代替自治,并不管地方自治是否完成,即施行憲政;中央政府組成方面表面上奉行無權憲法,實際上卻無法以權制能,人民依舊無權;更為突出的是,南京國民政府在1947年宣布實施憲政明顯與民主政治背道而馳,不顧國內中共及中間黨派的政治訴求,頑固堅持一黨專政,企圖以實施所謂的“憲政”來鞏固政權。從根本上看,南京國民政府憲政是對孫中山憲政核心的完全背離,不但憲政準備階段沒有以三民主義為指導原則,進入憲政后,三民主義更是無從談起。
孫中山的憲政思想從本質上看是一種理想狀態的政治生態,是在他所處時代對民主政治的良好愿望。南京國民政府如果以憲政為契機,吸收其他政治力量進入政權體系,緩和各階層利益沖突,將各方納入到憲政這一體制中來,則中國有可能得到和平發展機遇,但是南京國民政府只顧一己私利,在對待憲政這一問題表現出,既無法繞開孫中山憲政思想,又在現實層面以此為幌子繼續進行一黨獨裁專政,其實是以一種工具性的態度來看待孫中山憲政思想,導致在形式上繼承了孫中山憲政思想,實質上卻嚴重背離,憲政的實施既沒有改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又沒有挽救其統治,最終只能被歷史的潮流淹沒。
[參 考 文 獻]
[1]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5卷)[Z].北京:中華書局,1985.
[2]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1卷)[Z].北京:中華書局,1981.
[3]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3卷)[Z].北京:中華書局,1984.
[4]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9卷)[Z].北京:中華書局,1981.
[5]陳柏心.自治法案評議[J].東方雜志,1934,(10).
[6]陳柏心.中國縣制改造[M].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
[7]陳之邁.中國政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6.
[8]李時友.中國國民黨訓政的經過與檢討[J].東方雜志,1948,(44).
[9]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Z).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10]黃彥:孫文選集(下冊)[Z].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11]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Z].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
[12]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 第 8 卷) [Z].北京: 中華書局,1986.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
[14]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Z).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15]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Z].廣州: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16]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孫中山全集(第2卷)[Z].北京:中華書局,1985.
(李曄曄: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流動站科研人員,長春大學講師,歷史學博士;孫紅艷:長春大學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