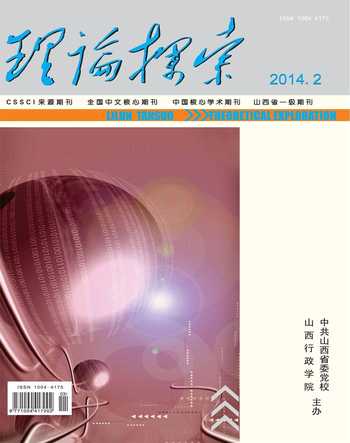“司法三段論”的語境考量
聶長建 景春蘭
〔摘要〕 三段論適用于司法判決的難處在于,“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與三段論大小前提的屬性不同,“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之間不具備三段論大小前提之間的確定關系。三段論的大小前提是超語境的,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是語境化的,具有或然性,大前提是針對特定語境的,小前提存在于特定語境中,特定語境勾連了“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司法三段論”的中心并非在三段論的推理形式上,而是在大小前提共同語境的判斷上。
〔關鍵詞〕 “司法三段論”,大前提,小前提,刑法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4)02-0125-04
三段論本是邏輯學的概念,就是大前提通過涵攝關系賦予小前提以確定性結論。確定性是司法判決的追求,大陸法系在司法判決中普遍采用三段論模式。但在司法實踐中,三段論模式暴露了其固有的缺陷,那種把“司法三段論”等同于三段論的機械司法模式更為學界所詬病。三段論只具有確定性一個維度,而司法三段論則具有正確性和確定性兩個維度。司法三段論的確定性要接受正確性的調整,并不像三段論的確定性那樣絕對化,只有大小前提的語境一致時,結論才具有確定性。語境因素使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具有開放性,這就打破了“法律是一門精確科學”的神話,這對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司法三段論”中大小前提關系的實質
在邏輯三段論中,大小前提均為事實命題,都具有或真或假的確定性,大小前提具有同質性,二者構成機械關系,可以得出確定的結論。說三段論是機械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對采用三段論形式的司法三段論的機械司法的指責,則是錯誤的。因為在司法三段論中,大前提均為規范命題,小前提或為規范命題或為事實命題,規范命題既具有真、假的事實性維度,又具有對、錯的價值性維度,規范性命題具有復合維度,而事實性命題只具有“真、假”的單一維度。在三段論中,由于大小前提都是單一的維度,這就形成了大小前提之間的一一對應的、機械的確定關系,因為“真、假”是不相容的,要么為真,要么為假。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和結論都是描述性的“真假”判斷,它只有一種描述方式,而不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反命題是假命題,“凡人必死、張三是人”是成立的,“凡人不必死,張三不是人”就是不成立的假命題,這就保證了結論的唯一確定性,所以也就不會有對它的爭論,人們不會爭論凡人是否必死和張三是否是人這樣的問題。而且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和結論都不是評判性的,所以加上“(不)應當”的評判,如“凡人(不)應當必死”、“張三(不)應當是人”都是令人捉摸不透、表述混亂的病句。〔1 〕
但是在司法三段論中,我們分析小前提是規范命題的情況,由于大小前提都是復合維度,大小前提不可能是一一對應的機械關系,因為“對、錯”作為人的主觀判斷是可以相容的,在不同的主體間仁智互見通常是存在的,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和結論既是描述性的“真假判斷”,又是評判性的“對錯判斷”,它就有兩種描述方式,反命題也是真命題,如“故意殺人罪判死刑、張三犯故意殺人罪”是成立的,“故意殺人罪不判死刑、張三沒犯故意殺人罪”也是成立的真命題。這樣司法三段論的結論就不具有機械的確定性,人們會爭論是否應該判故意殺人罪死刑,也會爭論張三是否應該以故意殺人罪定性,這都是對正確性的爭論,都影響了判決結果的走向,消解了確定性的絕對唯一性。而且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和結論都是評判性的,可以加上“(不)應當”的評判。可見,盡管司法三段論和三段論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大小前提的性質是迥異的,這就導致了它們的關系也是不一樣的:在三段論中,大小前提是確定的機械關系,大小前提本身是確定的;而在司法三段論中,大小前提是不確定的開放關系,因為大小前提本身也不是確定的,都可以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如果司法三段論的小前提是事實命題,固然具有確定性,但大前提仍然是不具有確定性的規范命題,大小前提是異質的,二者之間仍然是不確定的關系。
二、“司法三段論”中大前提的語境考量
語境包括語言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心理、身份、地位、職業、時間、空間、閱歷、目的、信仰、愛好以及使用言語的場合、對象、前言后語、上下文、背景等,簡單地說,就是具體的情境、情形、情況。因為語境之不同,必然引起價值判斷的不同并因此改變對象之于主體的意義。法律作為規范系統是價值對事實的統攝,法律規范里的事實并非指一切事實,而是經過價值檢查、篩選和過濾后的事實,這就使法律規范作為大前提時表現出不確定的一面,喪失了普遍必然性,這與三段論中大前提的屬性是不同的。刑法第232條規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條規定看似很明確,法官依據此條法律規范判決在一般情況下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警察擊斃歹徒、精神病人殺人、9歲小孩殺人該怎么判?沒有哪個法官否認這三種情形都是“故意殺人”,但沒有哪個法官對這三種情形以“故意殺人”罪定性并賦予刑法第232條的法律效果。這就是說,在司法三段中,大前提中“故意殺人的”并非指一切故意殺人行為;相應地,在確定小前提時,也不能把所有“故意殺人的”行為都定性為“故意殺人罪”,這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就是語境。語境猶如篩子、過濾器,排除一部分法律規范對案件事實在概念上的涵攝關系,“9歲小孩殺人就不能被法律上的‘故意殺人的所涵攝,因為從法律的價值判斷出發,9歲小孩并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主體。” 〔2 〕具體來說,司法三段論的大前提要考慮如下語境因素:
(一) 性別。如為保護胎兒的生命權,刑法第49條規定,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對其中懷孕的婦女應當宣告緩刑。
(二)年齡。如考慮到青少年心智不成熟,為保護青少年的權利,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刑法第17條規定,不滿14周歲的人不負刑事責任。出于尊敬老年人的傳統價值觀,新刑法修訂案(八)規定,審判時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刑法第72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三)心理。如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實施安樂死,由于主觀沒有惡意,在有的國家如荷蘭不是犯罪,在我國仍是犯罪,但量刑減輕。
(四)時間、時效。如刑法第109條“叛逃罪”的時間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履行公務期間。刑法第87條規定,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不再追訴。如果二十年以后認為必須追訴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五)空間。如刑法第263條規定對搶劫罪加重處罰的情形:入戶搶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搶劫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
(六)目的。由于社會發展處于變動不居中,過去符合立法者目的法律規范如今可能違背立法者的目的,所以拉倫茨認為,由于當下案件事實性質的改變,如果適用法規范使原來的目的不可能再達成,“那么在今天適用該法律就會造成全無目的、全無意義的結果,因此即不宜再予適用。于此極端情況,即可適用羅馬法諺:‘法律理由停止之處,法律本身也停止。如果某規范恰好是針對特定暫時的事實關系制定的,一旦此關系不存在,前述情況就會發生。” 〔3 〕 (P226 )
通過對以上語境因素的分析,我們發現,刑法的規范如第232條不是封閉性的概念,而呈現出開放性和不確定性,依據此條規范所作出的司法判決,也不具備絕對的確定性。法律規范就受到語境的限制,并隨著語境變化而調整和進行相應的廢、立、改,作為司法三段論大前提的法律規范不是全稱判斷,不是一個普遍性的概念,而是一個普遍與特殊相結合、具有程度上差別的“近似性”而非“全真”的概念。我們比較三段論“凡人必死,張三是人,張三必死”和司法三段論“故意殺人的判處死刑,張三故意殺人,判處張三死刑”,通過以上的語境分析,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發現。因為三段論與語境無關,“凡人必死”是個普遍性的“全真”概念,不因為該人的性別、年齡、時間、空間、身份、心理、目的、背景等變化而變化,是靜態的,張三不管是多大年齡、什么性別、正常人還是精神病人、做官的還是百姓、善良的還是邪惡的,在“凡”這個普遍性修飾語的統攝下,都逃不掉死的命運。在三段論中,真值之所以可以傳遞,就因為三段論只是事實判斷,大前提是“全真”的和普遍的,又不受外界的干擾,其賦予小前提結果的傳遞因此不會出現偏差,大小前提為真,結論必為真,真值可以傳遞。而司法三段論卻與語境相關,“故意殺人的”不是普遍性的概念,也不是“全真”的概念,因為司法三段論的大前提作為規范系統,既有真、假的事實性維度,又有對、錯的價值性維度,規范性命題具有復合維度,規范性命題的“真”維度要受到“價值”維度基于語境的統攝,就變得不是“全真”,變得不是“普遍”了,“故意殺人的”法律價值因為該人的性別、年齡、時間、空間、身份、心理、目的、背景等變化而變化,是動態的,張三的年齡、性別、正常人還是精神病人、善良的還是邪惡的等語境因素,決定其是否在刑法第232條的“故意殺人的”的涵攝之列。如果他是9歲小孩、或是一個精神病人、或是一個孕婦,亦然是“人”,在事實上是“故意殺人”,但在價值上不在死刑之列,作為價值對事實統攝的法律規范系統也不對這樣的人判處死刑。在司法三段論中,真值之所以不可以完全傳遞,就因為司法三段論是規范判斷,大前提是不是“全真”的、不是普遍的,其賦予小前提結果的傳遞因此可能出現偏差,大前提并非全真,也就不可能必然性地得出全真的結論。
三、“司法三段論”中小前提的語境考量
學界將案件分為占大多數的一般案件和占極少數的疑難案件,語境是重要依據。一般案件就是本案的情境和法律規則針對的情境相一致,語境已經將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聯系起來;疑難案件就是本案的情境和法律規則針對的情境出現了不能逾越的裂縫,當大前提明顯不適合小前提時,要重新尋找適合的大前提,也就是制定出和新的情境相適應的法律規則;在適合的法律規則制定出之前,應該適用不受語境之限的法律原則。
在一般案件中,法律規則所針對的情境和案件的情境是一致的,依照現有的法律規則判決不僅是確定的,也是正確的;但在疑難案件中,法律規則所針對的情境和案件的情境是不一致的,依照現有的法律規則判決雖然是確定的,但不是正確的。
法律規范作為三段論的大前提,不具備完全的有效性,這說明人的理性能力和法律并非盡善盡美。法官的司法判決,要彌補抽象法律規范和具體案件事實之間的縫隙,應將注意力放在對案件事實的定性上。任何法律規范總是針對特定的情境制定出來的,當我們對一個案件事實進行定性時,一定要考慮到案件事實的情境和法律規范所針對的情境是否一致,如果情境不一致,一個法律規范就不能夠涵攝在其語境之外的案件事實。當我們比較法律規范所針對的情境與案件事實的情境時,就是在關注語境問題,因為價值判斷是法律的靈魂,是法律推理的靈魂,是司法判決的靈魂,而價值判斷不是抽象的,必然體現在具體的語境中,安樂死的主觀惡性不大,十四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七十五周歲以上的老年人不判死刑等具體的語境因素,都體現了立法者的價值判斷。
判斷案件事實的語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法律規范的語境相對照的,要有相當的生活閱歷、經驗積累、洞察力和知識儲備等要求,而不能單憑文字表述做判斷,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是經驗”也是指這個意思,邏輯本身與案件事實的定性沒有關系。法律規定用武器傷人者加重處罰,某人用鹽酸傷人,那么鹽酸是否被認定為武器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把這種情形當作刑法意義上的使用武器,認為“以往的語言用法雖然只稱機械的工具為‘武器,然而,因為技術的發展,這種語言已經有所轉變,發生化學作用的工具也被視為‘武器。依其見解,對‘武器一詞,依今日的語言用法作廣義的理解,事實上也能配合刑法規定的意義及目的。” 〔3 〕 (P203 )拉倫茨也認同聯邦法院的解釋。這說明,對案件事實的定性,也不能僅作抽象的字面解釋,而是要放在整個法律體系中去解釋,個別法律規則必須和整個法律體系的基本精神相融貫,不能拘于文字之限而機械地認定。
法律是一門說理的藝術,無說理就無判決,但法律之“理”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存在于具體案件的語境中,語境是對案件事實定性首先考慮的問題。對語境的考量顯示了法官的判斷力,也說明三段論的中心在于大小前提的邏輯關系上,司法三段論的中心則在法官的判斷上,即判斷大前提(法律規范)所針對的語境和小前提(案件事實)的語境是否一致,是否體現出大致相同的價值判斷。三段論只不過是反映大小前提之間的邏輯關系,卻不能決定對大前提的選擇是否適當,對小前提的定性是否正確,它不能決定司法三段論的有效性。盡管司法三段論的邏輯性順序是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但我們確定司法三段論時,并非首先選擇出一個大前提,因為法律規范那么多,我們只需要一條或少數幾條適于本案的法律規范。那么,為避免選擇大前提的漫無邊際,我們要有一定的方向和依據,那就是確定本案的語境,然后依照小前提的語境回溯尋找與之吻合的大前提,如果我們找到了與語境吻合的大前提,就說明這是一個一般案件,可以直接適用法律規則;如果找不到與語境吻合的大前提,就說明出現規則漏洞,這就是一個疑難案件,適用不受語境之限的法律原則,然后制定出與本案語境相吻合的新的法律規則。
四、語境是溝通“司法三段論”大小前提的紐帶
司法三段論不等于三段論,法律邏輯不等于形式邏輯,原因在于司法三段論和法律邏輯都是有對象和內容的,而三段論和形式邏輯只是純形式的。三段論只提供司法裁判的邏輯形式,“所以邏輯素有‘形式邏輯之稱。就是說,邏輯只與形式有關,與內容沒有關系。” 〔4 〕 (P155 )如果把司法三段論比作有機的人體,三段論只是提供了司法三段論的邏輯形式“骨架”,但這“骨架”上的法律內容“血”和“肉”是三段論無法解決的。康德深刻地指出:“全部理性知識,或者是質料的,與某一對象有關;或者是形式的,它自身僅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一般地涉及思維的普遍規律,而不涉及對象的差別。形式哲學稱為邏輯學。” 〔5 〕 (P1 )邏輯學沒有經驗部分,是先天科學。法律是經驗科學,作為司法三段論大前提的法律規范是針對特定對象的,作為司法三段論小前提的案件事實就是對象本身,而處在特定語境中的個別對象是有差別的,它們被大前提所賦予的效果也就不同。語境是溝通抽象法律規范和具體案件事實的橋梁,司法判決就是將抽象的法律規范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事實,要解決“抽象”與“具體”之間的空隙,就是要分析抽象法律規范所針對的具體情境,對比案件事實的具體情境,如果二者一致,就表明“抽象”和“具體”之間的空隙被填滿了,法官所選擇的法律規范對本案件事實是適當的。否則,法律規范對本案件事實是不適當的,法官應該重新選擇適當的法律規范。
法律在適用中采用了邏輯的形式,但是邏輯的適用只是法律適用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伽達默爾指出:“如果有人認為法律在某個具體案件上的運用只是把個別置于一般之中的邏輯歸屬過程,那顯然是一種外行的看法。” 〔6 〕 (P685 )顯然,法律的適用不僅是邏輯歸屬的過程,更是語境判斷的過程,因為司法三段論的大小前提依靠語境聯系,邏輯三段論的大小前提之間沒有語境關系。一個司法三段論的結論,不僅出自大前提對小前提的邏輯涵攝關系,即小前提的外延包含于大前提的外延之中;更要求大小前提在語境上是相吻合的,“當大前提明顯不適合小前提時,要重新尋找適合的大前提;把大前提比作‘履,小前提比作‘足,那么‘履自‘足來,‘履隨‘足變,應‘修履適足而不是‘削足適履。” 〔7 〕也就是說,過去制定的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則都是針對特定的語境的,如果現在發生的案件的語境與之不同,那么縱使大小前提確實有邏輯上的涵攝關系,但大前提卻不具備賦予小前提以結論的合法性。
參考文獻:
〔1〕聶長建.司法三段論迷局破解〔J〕.學術探索,2010,(2).
〔2〕聶長建.從概念涵攝到類型歸屬——司法三段論適用模式的轉型〔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4).
〔3〕〔德〕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4〕王 路.邏輯的觀念〔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下卷)〔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7〕聶長建.司法三段論的大前提研究——兼論邏輯涵攝與法律涵攝的區別〔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1).
責任編輯 楊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