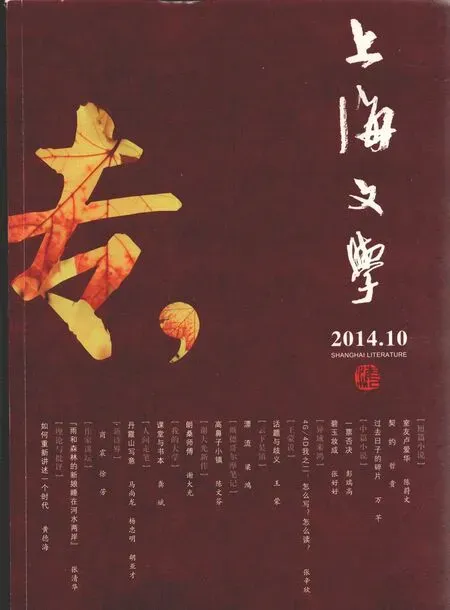話題與歧義
今天我主要是談一些熱點,人們喜歡議論的一些事,從專業(yè)化的角度來看也比較有趣的,它是被人們所關心的一些話題,另外我盡量做到,在我們過去的文章里面多次寫過的、多次發(fā)表過的我就不說了,我在這兒說一些我原來沒有得到機會寫文章的一些東西,因此都是一些不成熟的話,我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在這兒講完了以后也許會引起一些批評,有很大的歧義這是肯定的,我只是希望網(wǎng)絡報道的時候不要太夸張,不能相反。
關于“五四”與傳統(tǒng)文化
第一個問題,談一下“五四”新文學運動和傳統(tǒng)文化。“五四”不多說了,因為北京大學是“五四”的發(fā)源地,我現(xiàn)在談的這個問題是什么原因,就是“五四”時期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很猛烈的批評,這種批評是很刺激,可是現(xiàn)在我們國家又確實面臨著一個挖掘傳統(tǒng)文化、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熱度,我想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然“五四”到現(xiàn)在不止三十年了,快九十年了,是更多的年頭了。
我想這里頭有很多的原因,首先是歷史的一種選擇,在“五四”時期中國正在迎接一場風暴,迎接一場大的變動,而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比較簡單,它的特質在于維護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乃至于和諧,而不是在推動社會大的變革。所以對于“五四”時期的那些呼喚暴風,呼喚改革,呼喚革命,呼喚翻天覆地的仁人志士來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惰性的因素,甚至于是反對的因素,所以不管國民黨還是共產(chǎn)黨,不管是胡適還是魯迅、陳獨秀,也不管是吳稚暉還是李大釗,他們都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在當時令國人大大地感到悲痛的是從傳統(tǒng)文化上找不到通向現(xiàn)代化,通向富國強兵、發(fā)展科學技術的契機。如果說現(xiàn)在認識到了那時候的一些言論比較激烈,態(tài)度也比較情緒化,那么恰恰是因為現(xiàn)在經(jīng)過“五四”的洗禮,我們已經(jīng)吸收了,已經(jīng)接受了大量的推動民主、科學、社會進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還有包括一個有爭議的詞,“五四”價值等等。是在你接受的許許多多東西以后,你回過頭來再看傳統(tǒng)文化,覺得傳統(tǒng)文化有著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有很多美好的東西。尤其是當我們國家面臨著不是一個風暴接著一個風暴,一個顛覆接著一個顛覆,一場大的斗爭接著一場大的斗爭,而是更傾向于在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情況下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和發(fā)展生產(chǎn),發(fā)展文化的這樣一個時候,人們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有些東西合情合理,有利于給社會各個方面一個規(guī)范。
所以,我非常不能贊成一種看法,就是把弘揚傳統(tǒng)文化和繼承“五四”的精神對立起來,甚至一講傳統(tǒng)文化就得罵一頓“五四”,或者一講“五四”就一定不能夠講傳統(tǒng)文化,我覺得那樣就錯了。文化的問題很多時候它不是一個零和的模式,不是說吸收這個文化了就不能吸收那個文化。前不久我參加過一個討論中國民族的節(jié)慶或者節(jié)日活動的一個研討會,我就不接受那種說法,說我們?yōu)槭裁船F(xiàn)在要講中國民族的節(jié)慶,因為現(xiàn)在西方的節(jié)慶已經(jīng)侵入到我們這兒來了,又是情人節(jié),又是圣誕節(jié)。不一定要對立起來。你如果說是情人節(jié)、圣誕節(jié)是舶來品的話,那“五一”也是舶來品,“三八”也是舶來品,“六一”也是舶來品,不一定是對立的。
關于“國學熱”
在這種情況之下又出了一個新的名詞,這個新的名詞更敏感一些,就是“國學熱”,國學熱是媒體起的作用特別的大。這個東西的出現(xiàn)它也符合了社會的上上下下的許多方面人們的心愿,就是被我們撂下得太久了,四書五經(jīng)、孔孟之道、老莊之道一直到易經(jīng)。現(xiàn)在到新華書店一看,什么風水,這個風水連韓國都要申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這就更加緊張,我們得趕緊弄這個風水,不弄風水的話就變成韓國的了。當然,你撂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又拿出來,覺得孔子說得多好啊,是不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和而不同”……越說越好,說得很好聽,很美好,國學熱就出來了,一直發(fā)展到什么份兒上了?今年九月,暑期開學的時候,有好多小學都穿上古代服裝,以念《三字經(jīng)》來參加開學典禮,新華社發(fā)了有紫陽小學,還有南京的夫子廟小學。紫陽小學的穿衣接近清朝,夫子廟小學我沒弄清楚,這整個有一點像天主教。還有成都有的小學,因為成都很熱,九月一號開學,非常熱,有的小學,在大太陽底下,學生們都穿上古代服裝,熱得一身汗,好多家長都心疼得不得了。我有一點糊涂,中國出什么事兒了?大清復辟了?
對不起,《三字經(jīng)》我也發(fā)表一個看法,《三字經(jīng)》的好處是很好普及,很容易記憶,容易背誦,有些話語也都挺好,“教不嚴、師之惰”……有些說法挺好,但是《三字經(jīng)》對于今天走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的國家來說,它的內容相當?shù)膯我弧⑵妫褪撬押⒆佑柧毘梢粋€老老實實、規(guī)規(guī)矩矩,什么都合理,什么都聽話,訓練成這樣一個孩子。
《三字經(jīng)》不講身體健康,不講精神活潑,不講兒童天然的一個游玩的權利,它不講發(fā)揮你的想像,你的個性,它不講創(chuàng)造性,它很少有積極的,就是讓你的精神得到解放,智力得到解放,活力得到解放的東西,而相反都規(guī)范起來。規(guī)范當然是好,我們學校也是有規(guī)范的,任何一個單位都是有規(guī)范的,但是只有這些東西它是不夠的。我一想起我們的小學生穿著清朝的服裝在那大太陽底下曬著,在那兒念《三字經(jīng)》,咱們的“五四”就這么白搞了嗎?至于嗎?
關于國學,《詞源》上只解釋是國家辦的學,這是古代的解釋,《辭海》上有兩個解釋,一個是國家辦的學,一個是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國固有的文化這個說法能不能跟這個國學完全站得住,我也有懷疑。就現(xiàn)在一般講國學都講先秦諸子的,研究《紅樓夢》的人沒有人說他是國學家,研究明清小說的有沒有(國學家)我不知道,研究唐詩的人都沒有人說他是國學家,研究李白、杜甫的都沒有人說他是國學家,馮至先生是研究杜甫的,是寫杜甫傳的,從來沒有人當他是國學家,當然年紀大了他就是國學家了,我也快成國學家了,因為我還講“老子”。
固有文化這種說法我也不太喜歡,什么叫固有的文化?文化能固有嗎?文化都是在不斷的接觸、開創(chuàng)、交流、碰撞、消化、融匯之中得到的。琵琶不是我們固有的,黃瓜不是我們固有的,所以黃瓜叫胡瓜,南瓜是不是我不知道,洋白菜肯定不是我們固有的,要不怎么叫洋白菜?番茄肯定也不是固有的,因為帶番字,土豆在新疆都叫洋芋,肯定也不是固有的,白薯是菲律賓來的,這個固有以哪一年算起?黃帝元年?還是炎帝元年?和那個時候沒有關系,哪個都不是固有的,沒有辦法,許多科學家更不是固有的。所以對這個定義我也不大喜歡,我個人不大愿意用這個定義。
但是很多大學有國學院,這個我沒意見,我贊成,大學里面的事好辦。為什么?大學里面學院多得很,北大有多少個學院,有二十多個嗎?三十多個學院有一個國學院,有國學院的同時還有文學院,還有法學院,還有其他的,可是如果讓社會上,把這個國學變成一個最重大的口號,我就有一點搞不清楚了,我不敢說不對,我也沒有這個膽,但是我搞不清楚了。
和這有關的,現(xiàn)在和“五四”聯(lián)系起來,很多問題現(xiàn)在都出來了,一個是白話文和文言文,爭論越來越多,這本來有道理的,“五四”時期是不是對文言文批評得太過了?我想這個檢討可能是有道理的。有人就給我講,他說白話文不僅僅是一個工具的問題,而且它有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審美的意向。比如說你把老書全部翻譯成白話文,包括《論語》和《孟子》都翻譯成白話文,基本上翻譯出來以后,很多內容都沒有了。我想這些都說的是對的。但是反過來說白話文是從洋文那兒制造出來的,我講,這在二十年前《文藝報》上就曾經(jīng)有朋友這樣寫,說我們民族文化什么都沒有了,我們把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字丟掉了,“五四”以后,是根據(jù)英語創(chuàng)造的白話文,這就跟活在夢里一樣了,白話文首先是我們嘴上說的文,就是我們口語,這個口語的存在是我們固有的,從來沒有消失過的,即使是在幾百年以前,人們見面說話首先不可能全部都是純的文言,里面夾雜一些半文的話肯定也有,但是不可能是純文言。
關于文白之爭與繁簡之爭
前不久我又聽到一種,也是讓我大惑不解的說法,說白話文有兩種,一種是老的白話文,原來在中國有生長的、源遠流長的白話文,說“五四”以后的作家只有三個人會老白話文,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周作人,一個是張愛玲,其他的人都是受英文影響而寫自己的白話文,這純粹是夢話。說中國原來有白話文,難道這是一個新的發(fā)現(xiàn)嗎?幾大才子書基本上都是白話文:《鏡花緣》是白話文;《鏡花緣》里面夾雜一些半文言,很好的;最好的白話文小說尤其是北京話小說是《兒女英雄傳》,雖然它的思想水準相當?shù)年惻f,相當?shù)睦蠚猓撬f的話都是很通順的口語;《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也是白話文。過去很多話本,解放以后也還出版過。解放以后江蘇省有一個揚州評話的專家叫楊少堂,他講武松,我看過他的半部武松,這是四十五萬字,全部都是以口語白話記錄下來的,把武松講得活靈活現(xiàn),非常的詳細、周密,加了很多的創(chuàng)造,這都是白話文。那么老舍的白話文更不用說,魯迅的白話文里面文言文成分比較多,很多是把文言文用在白話文里面,據(jù)說他的文句還頗受日語影響,可以說如今有些朋友對于這個白話文的說法也制造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噱頭。
還有海外鬧得非常厲害,說中國的白話文不好,因為受了“毛文體”的影響。“毛文體”?開玩笑啊,誰受了毛文體的影響?在座的,你們哪位寫的文章像毛澤東,你們舉個手,我把我今天的講演費全部乘五送給你。如果你的文章確實寫得像毛澤東,請舉手!開玩笑啊,學毛澤東寫文章,你沒地位,沒名氣,沒有那個自信,沒有那個居高臨下、所向披靡,是不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尖銳,還帶幾分孫悟空齊天大圣的勁。至于說在政治運動的時代,有些比如說寫文章講道理不夠,這里頭是不是也受某個領導人文風的影響,這是另外一個討論。然后這個愈演愈烈,一直發(fā)展到簡體字,連臺灣的都跟著鬧,說簡體字始作俑者是國民政府,并不是共產(chǎn)黨開始搞的簡體字。現(xiàn)在傳出去說簡體字是共產(chǎn)黨根據(jù)蘇聯(lián)專家的意思搞的,我都不知道這樣的無稽之談從哪兒來。我們的簡體字包括用拼音文字的時候,我們很大的一條,我們拒絕蘇聯(lián)專家的建議,沒有采用斯拉夫字母作漢語拼音符號,而是用的羅馬字母。1922年,錢玄同提出了筆畫方案。在1932年,我負兩歲的時候,出版了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匯》,收入不少簡體字。所以簡體字對我們來講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我上小學的時候我有一個同學,他有三個兄弟,有兩個是孿生,有一個跟他們差一歲半,一個叫聶幫鼎,一個叫聶幫基,一個叫聶幫礎,這個音也很鏗鏘有力,這三個孩子學寫字的時候,整天地哭,因為他的姓很復雜。那時候得連著寫三個耳朵,復雜,簡化以后變成兩個“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處。而且簡體字和繁體字根本不需要對立起來。我相信北大的學文科的人都懂繁體字,請在座的人里面,你們不認識繁體字的請舉手。沒有一個舉手,因為它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然后舊詩新詩,喜歡寫這些詩的都很可愛,都很好,尤其像錢鍾書的詩、徐志摩的詩、艾青的詩、舒婷的詩、聶紺弩的詩,都寫得非常好。現(xiàn)在讓我有時候略感擔憂的就是我們把這種文體上的一些區(qū)別,把這個題材上甚至于風格上的不一樣把它對立化,變成互不相容的東西。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應該相通,也許這個時候我們想一下,盡管它有各種針對性。在《共產(chǎn)黨宣言》里面已經(jīng)提出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也許我們還可以提一下,就是鄧小平給景山學校題的詞,他提出了一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xiàn)代化”的這樣一個主張,我們弘揚傳統(tǒng)文化,我們鉆研“國學”都是好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xiàn)代化,我們的目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是現(xiàn)代化,不是古代化,不是回到明清,更不是回到先秦。
關于文學與革命
然后我談一個很大的問題,文學和革命的關系,革命前的文學和革命后的文學的關系,或者叫“前革命的文學”和“后革命的文學”的關系。從世界歷史中我們發(fā)現(xiàn)一點,就是在有些地方在革命以前或者革命的初期,它會有一個文學的高潮,譬如俄羅斯。俄羅斯它所出現(xiàn)的文學的燦爛,到現(xiàn)在是沒有先例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果戈里……太多太多了,我是講不全的。有時候我產(chǎn)生一個非常荒唐的想法,我說俄羅斯的經(jīng)濟發(fā)展常常走彎路,它非常不順利,中國的農村包產(chǎn)到戶立刻糧食問題就解決了,是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俄羅斯你把集體一解散,糧食生產(chǎn)量還下去了,有時候都無法想像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他們國家文學太發(fā)達了?一個國家文學要太發(fā)達了,還有人好好種糧食嗎?還有人好好地弄醬油弄醋做電池做手電做衣服嗎?文學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點兒伏特加,朗誦一首俄文詩,再唱個俄羅斯民歌,游覽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這個時候還再去計算什么經(jīng)濟效益,多么煞風景。
當然也許這只能算是笑談。
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五四”以后到一九四九,也是非常活躍的,郁達夫、巴金一直到胡適、梁實秋,這也非常的多,不多說,非常的活躍。有時候文學的高潮是和社會的際遇,和歷史風暴的前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是一個事實,當然我們不見得都從政治或者革命歷史的角度來說,中國人也早就發(fā)現(xiàn)了,窮愁之詩易工,而歡娛之詞難寫。我們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視中國的古典文學,越古我們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講過一個理論,這是他的原話,說你們老覺得中國的古典文學了不起,因為你們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話,你看一看英法的那個古代文學,比你中國的古典文學要豐厚得多。就拿最輝煌的唐詩來說,它的題材就用了那么幾種,思鄉(xiāng)、送別、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國是“五四”以后現(xiàn)代文學一下子熱鬧起來了,各式各樣,什么都有。后來夏志清的話我見人就問,見北大的我問,別的學校我也問,香港我問、澳門我也問,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跟我說,他贊成夏志清的話,所以夏志清的話是光桿司令,就他一個人這么說,但是他畢竟是夏志清。
后革命的文學不需要走出一條大路
我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革命的文學。當這個社會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付出了鮮血與生命的代價,終于達到了革命的人民奪取政權這樣的一個目標,宣稱人民已經(jīng)把命運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了。這時候對文學怎么走?這個文學怎么辦?卻沒有特別好的答案。
比如說蘇聯(lián)有法捷耶夫等占主流的作家,還有肖洛霍夫,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蘇聯(lián)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他的代表團成員里面就包括肖洛霍夫,而且走到哪兒都是這種口氣:“這是我們蘇維埃的偉大作家肖洛霍夫。”在蘇聯(lián)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肖洛霍夫發(fā)言,他說西方世界攻擊我們蘇聯(lián)的作家是按照黨的命令來寫作的,這是胡說八道,我們是按照自己的良心來寫作的,但是我們的良心屬于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我一聽這覺悟真高,真會說,真招人疼。但是有的時候人們也會發(fā)出批評、責備,就是認為蘇維埃時期的狀況還趕不上沙皇尼古拉二世那個時期。這個問題也麻煩,蘇維埃如果不是最好的文學的環(huán)境的話,那么現(xiàn)在蘇聯(lián)解體已經(jīng)過去了將近二十年,解體了是不是又該出來托爾斯泰,托爾斯泰二號,也沒見,更沒戲了。這種問題中國也有,尤其是到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們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要全面小康,所以我有一天講話,人家給我提條子,問得我直翻眼,他問我“王蒙先生,您認為文學還能夠存活多久?什么時候將要滅亡?”一些夸張其詞的一些說法,這些比較多。
革命前的那個時候文學發(fā)達,而且有孤注一擲的勇氣,拚了!為了正義,這是最后的斗爭,團結起來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會是怎么樣?怎么發(fā)展?我不但看到了中國會面對革命以后這個問題的一個困惑,而且我還看到比如說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我還見過她,她講話的時候的自信,那種使命感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為黑人的權利和種族主義者作斗爭,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過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監(jiān)獄。種族主義它垮臺了,南非勝利了,她達到了她畢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聲音慢慢小了起來。2006年還出了這么一件事,有幾個搶匪——也是她畢生為之奮斗的人——進了她的家,搶她的東西,讓她把她的結婚戒指扒下來,她拒絕了,結果她挨了打。這確實是個事,就是這些熱情地呼喚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們,在革命勝利以后怎么樣繼續(xù)歌唱?咱們中國還有一些說法,我完全沒有資格,沒有能力對之作出特別明晰的判斷,比如前五六年就曾經(jīng)有人回憶,說是在1950年代,就是1957年的時候,有人問毛主席,說如果魯迅活著,現(xiàn)在會是什么情況?說毛主席回答說,也可能他在監(jiān)獄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寫作了吧!當然也有很多魯迅研究所的所謂魯學的專家,對這種說法深惡痛絕,認為這種說法是完全不負責任,也是不符合史實,這說明在這中間也還需要積累更多的經(jīng)驗。我在兩年多以前曾經(jīng)提出一個議題,就是雄辯的文學與親和的文學,我們的文學不可能僅僅是雄辯,也不可能時時都找一個對立面來進行辯論,有些時候需要更好地表現(xiàn)人性。
關于市場經(jīng)濟和文學
第三個話題談談市場經(jīng)濟和文學。市場經(jīng)濟和文學這是兩回事。我記得當年有記者采訪一位老作家,說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有什么影響?他的回答是我對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無動于衷。你寫你的東西,他對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完全無動于衷,我沒有做到。但是我也并不是因為市場經(jīng)濟來決定我寫作或者不寫作,市場經(jīng)濟當然有動于衷,它影響我的衣食住行、生活需要、子女教育、父母贍養(yǎng)以及消費的水平,從這些方面來考慮,但是它和文學這是兩碼事。但是我們這里一直也有很強烈的反映,就是認為市場經(jīng)濟毀掉了文學,認為市場經(jīng)濟摧毀了文學。有一個非常可愛的老作家,老的革命作家,我不打算提他的名字,我最近聽說,這位大師已經(jīng)去世,他說過去我們是“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我們現(xiàn)在要“冒著敵人的鈔票前進”。這我也不明白,因為過去我舉的例子,就是說在革命成功了以后,有一些歷史人物那種浪漫性就降低了,比如說“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唱起來非常悲壯,但是我提改革你就不能唱,冒著賠錢的危險改革,冒著鬧事的危險下崗,這些都不能唱,可是我沒想到,我所敬愛的一位老作家提出了,說“冒著敵人的鈔票前進”。敵人的鈔票來了,你收回來交給革命不就完了嘛!那鈔票能把人打死嗎?砸在腦袋上一摞,五十萬元捆成一包,從四層樓上往下照人腦袋上砸,那還是有一定的威脅,如果砸昏了以后,一看旁邊有五十萬元,也許臉上會顯出苦笑兼甜笑,這個我不太明白。
有一個地方舉行詩歌節(jié),有一個詩人就講,紅旗都倒了,詩還有什么用?某雜志曾經(jīng)說過,現(xiàn)在文學狀況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壞,比淪陷區(qū)壞,比白區(qū)壞,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現(xiàn)在據(jù)說是為了迎合市場,有了什么下半身寫作或者其他一些涉嫌不雅的一些寫作的內容出現(xiàn)。我們和從前所處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文化革命”前1949年到1966年是十七年,這十七年一共出了兩百本長篇小說,平均一年能出十一二本,現(xiàn)在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七百至一千種,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這一年都出了一些什么長篇小說,哪怕他的專業(yè)比如說在北大當代文學研究中心長篇小說科(好像沒有這么一個科),他也說不清楚,好像就是有了更多的選擇的可能,可以滿足更多的個性化需要,這是一個好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把有些因為有歧義而不能順利出版的一些內容也都出版了,一個東西,一百個人,九十九個人否定,一個人肯定的他也出版了。但是壞處也有,好的作品也淹沒在上千種趣味低級的新書里面。我現(xiàn)在上西單圖書大廈,有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書以后,我就嘆息,再不要寫書了,到處都是書啊,你想到的他也出,你想不到的他也出,現(xiàn)在沒有必要再出書了。
現(xiàn)在建國都六十年了,有些人回憶起來就覺得,從1959年到1966年,尤其是1959年到1962年、1963年,因為后來越來越緊了,那個期間的長篇小說最成功。舉個例子,《保衛(wèi)延安》1959年,“三紅兩創(chuàng)”,文學出版社還出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1960年代還有《野火春風斗古城》、《鐵道游擊隊》、《苦菜花》,等等。有一批現(xiàn)在的人們都還記得,或者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你要是拿兩本書,一本比如說是2008年出版的,還有一本是1968年出版的,1968年就不要說了,1962年出版的,你要放在一塊兒看看,你不能說現(xiàn)在的書越寫越差,反正有不同的文學環(huán)境,在一種不同的文學生態(tài)下面,在一種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和歷史時期下面,人們閱讀文學作品的心態(tài)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北大這樣,但是我讀到了,說余華有一次跟學生們交流,談到當代文學,就不斷地有同學提問,說你看“五四”時期作家寫得多么好,現(xiàn)在作家寫得多么差,把余華說急了。他說我實話告訴你們吧,“五四”時期的那些作家,我不說名字了,要不我說了也沒關系,說什么《河塘月色》什么的,現(xiàn)在是個高中生作文都可以做成那樣,說你們看我的作品比他們寫得好多了,說我唯一的弱點就是我還沒死啊,我要死了以后,你們不說我的作品好才怪。這也是一種說法,一個作品的被接受,被抬高或者說被重視,當然和作品的質量有關,也和許許多多的情況有關。
我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一個社會,文學事業(yè),高潮化是所期望的,但是高潮化是未必能夠持久的,許許多多的高潮都要向正常移動和過渡。老子早說過,颶風刮一早上就不刮了,太陽一出來就不刮了。當然這是老子說的,可能沒有趕上那個大風口,大的雨也不過下一天,八個小時,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就差不多了,即使再下,也要停一會兒。所以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逐漸走向正常的這樣一個社會和文學生活,所以現(xiàn)在我們談不到什么特別激烈的文學運動或者那種文學高潮或者文學口號,寫出什么什么來,談不到這種口號。但是我們更多的是處在一個相對正常的閱讀環(huán)境,那是不是現(xiàn)在的文學就沒有好作品了?我不這樣看,我覺得還需要時間的淘洗,目前就說什么作品就是好,什么作品就是不好,什么作品是不如什么時代好,都為時過早了。
關于諾貝爾文學獎
大家還有一個很關心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水準很低,但是許多人關心它,所以我愿意在這兒談一談,就是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一個文學的大獎,它叫大獎起碼它的獎金大,它是一百多萬歐元,中國的最高的獎項是茅盾文學獎,四五萬人民幣(按:現(xiàn)在獎金數(shù)額已經(jīng)大有增加),這是第一。第二,它由瑞典科學院的十八位院士組成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他們都是終身制,死一個補一個,這里頭只有一個人能懂中文,就是馬悅然教授。諾貝爾文學獎特別喜歡標榜自己的特立獨行,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比較喜歡給具有或者是色彩上沾一點持不同政見的人發(fā)獎,在西方國家它相當喜歡給左翼的文學家發(fā)獎,比如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早期,他們發(fā)過海因里希·伯爾,他當時把西德批得一塌糊涂,西德政府拿他沒有辦法,他的駐華大使曾經(jīng)跟我說,給他發(fā)獎,這真的使我們頭疼,當時法蘭克福一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他說伯爾他的德語相當差,他是以道德家的身份得獎的,因為譴責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下面的許多不公正的現(xiàn)象而獲得的,有過這種說法。它還曾經(jīng)給葡萄牙共產(chǎn)黨人薩拉馬戈發(fā)過獎,給加西亞·馬爾克斯發(fā)過獎。在中國,好多人都可以看出加西亞·馬爾克斯把不發(fā)展的或者發(fā)展中國家的某些迷信、所謂落后的東西把它美化,變成文學的契機,變成文學的才能。另外一位偏西方的秘魯?shù)囊彩侵Z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略薩,他的政治意識還特別強,寫過很多政治論文,還競選過總統(tǒng),當然未能選上,他曾經(jīng)痛罵加西亞·馬爾克斯是卡斯特羅的太監(jiān)。還有意大利的劇作家達里奧·福,那也是令人大吃一驚的,至于對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獎勵一些流亡的作家,那多了,太多了,我這兒就不一一介紹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一點我親歷的事情,1993年在紐約,在華美協(xié)進社(胡適當年創(chuàng)立的,為美國主流社會了解中國文化搞的一個機構),我在那兒講話,講完話了以后,美國的一個筆會的女秘書,但是在中國肯定叫秘書長,她很強悍,這位女士就來問我,說今年北島將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知道嗎?我說我不知道,我說據(jù)我所知,諾貝爾文學獎是封閉的,是不提前公布的。她說我知道,我當然很佩服,是不是?這是“大牛皮”秘書長啊!你知道啊,好好好!她說你什么態(tài)度?我說我祝賀啊,我說誰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都祝賀,我說要你得了我也祝賀。她說中國作家什么態(tài)度?我說有人會高興,有人會不高興,她一聽兩眼發(fā)光,趕緊說為什么有些人高興,有些人不高興?我說你連這都不知道啊,所有的作家都覺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哪有老子天下第二的作家,老子天下第二他就不干了。她說中國政府什么態(tài)度?我說現(xiàn)在這個說得早了點兒,我說現(xiàn)在我不當部長了,代表不了中國政府。這也是一個事實。我有一種印象,這位女士拿著中國政府當公牛,拿諾貝爾獎當紅布,想這么甩一下,這么甩一下,等著缺心眼的人往上沖。
1992年,我接到瑞典科學院院士馬悅然教授的邀請信,說希望你推薦五個中國作家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其中完全可以包括你自己,這份材料不得少于十五頁(中國人講字數(shù),外國人講頁數(shù),我就不懂,這個字號怎么算,是用一號字?)。后來我就寫了,請外文專家黃友義先生給我翻譯,而且我告訴你們,我這里面推薦的有韓少功、張煒、鐵凝、王安憶,還有一個人我還沒寫,我可能想寫我自己,反正也沒成沒關系,如果順利的話,我不會不寫我自己。但是完了以后,因為我擔任過職務,第一步要征求我駐瑞典的機構的意見。當時駐瑞典的機構就說,馬悅然約你,不好,他對中國的態(tài)度不好,你王蒙的身份不應該來,不可以來。第一步就擋住了,我不能去。文化部還特意又寫了一封信,說由于王蒙有很豐富的經(jīng)驗,說可以應對不同的情況,我們建議這次還是讓他去一下,跟瑞典科學院建立聯(lián)系。但是我們駐瑞典機構仍然說不不不,還是不。瑞典方面著急啊,就改由SAS公司的總裁來邀請我。可是咱們這個駐瑞典的機構一看就看出問題來了,那航空公司的總裁邀請你干什么?你又不買飛機(其實當時給我一種感覺,火眼金睛!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這種感覺)。不行,還是不能來。瑞典方面也使勁,瑞典一個女的副首相兼外交部長來中國,見到中國跟她同級別的官員,領導人,她跟這位領導就說,說我們瑞典方面已經(jīng)做好了準備,歡迎王蒙先生訪問瑞典。我們的領導人回去就問,說她說這個干嗎?別人就告訴他,說那就派王蒙去吧。領導人發(fā)了話,說去吧。時間已經(jīng)很緊了,于是有關部門就通知文化部,王蒙可以去了。但是文化部下屬的外聯(lián)局火了,也不是說領導發(fā)了話可以去才可以去,我們一直說可以去,你這兒不讓去,現(xiàn)在我們這都忙起來了,我們不去了,不辦了。這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就沒去成。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跑到中國來問我什么時候去?我說手續(xù)沒辦好。我也不能說別的,我說有可能去不成。他回去就告訴馬悅然,說看來王蒙對訪問瑞典沒有興趣。馬悅然也是性情中人,也是學中文學得太透了,受中國人情緒化的影響,被中國和平演變了,他立刻發(fā)表一個聲明,他說王蒙已經(jīng)表示對瑞典科學院沒有興趣,也不準備和瑞典科學院進行交流,因此今后我們只好放棄跟中國大陸的文學的聯(lián)系。這是哪兒跟哪兒啊,他把我想得也太高了。總而言之,所以說你們看著很偉大的事情,你要知道內情以后,陰差陽錯,也不要以為那么偉大。結果馬悅然的輕率的做法引起了瑞典駐華大使館的不滿,他們的文化專員在香港發(fā)表了一個聲明,說關于邀請王蒙先生訪問瑞典科學院的情況你不完全了解,與王蒙先生個人完全無關,馬悅然的說法是不公正的,不真實的。
現(xiàn)在馬悅然又到中國來了(有一段時間都不許馬悅然入境,都上了黑名單的)。別人催著我問什么時候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法說這個事兒,怎么說?沒處可說,得了就得了,不得就不得,得獎當然很好,一百多萬歐元,存在中國銀行,對國家也有貢獻啊,得不了就得不了,算了,那也沒辦法。但是反過來說,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是國際奧林匹克,沒有競技技巧。比如我們知道的挪威,這是當年的事,挪威跟瑞典是一個國家的時候,挪威最有名的戲劇家易卜生,在最后的關頭,諾貝爾文學獎決定不給他,而給他的一個競爭對手叫比昂松,但是比昂松沒有什么人記住他,而易卜生非常有人氣。
如果我們列舉得獎的人我們會列舉出很出色的作家來,近半個世紀來有海明威、加西亞·馬爾克斯,但是我們列舉那些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也有一大批出色的作家,比如說俄羅斯的那批作家,等等。有人老在那兒分析諾貝爾文學獎,而且在那兒分析,為什么?因為中國作家膽小,因為中國作家沒有成為烈士。還有人分析中國作家自殺的太少,外國作家自殺的數(shù)量很大,我不知道是由于吃得太多,還是由于低血糖造成的這些說法。簡單來說對諾貝爾文學獎我們既不必把它看得那么那么的渴望,也不必把它視為對立面,以公牛的姿態(tài)向它沖去,也不必這樣。現(xiàn)在馬悅然已經(jīng)多次表示過,他最喜歡的是兩位山西作家,一位是李銳,一位是曹乃謙。有一年在重慶書市,馬悅然給曹乃謙站臺,而且說他隨時可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所以有馬悅然這樣的一個許諾,有些熱衷于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有些雖然對諾貝爾文學獎不無興趣,但是一看馬悅然沒提名,也就死了這條心,踏踏實實該干什么干什么,用不著再折騰這事兒了。
中國作家的兩項原罪
我開玩笑啊,我說中國作家有兩項原罪,第一項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第二就是沒有當今的胡適、魯迅。因為有人就說魯迅多么偉大,多么偉大,說中國人的驕傲在于有一個魯迅,中國人的悲哀在于只有一個魯迅。這個作為造句來說是有一定說服力和煽動力的句子,但是這個句子不通,因為所有的作家都只有一個,沒有克隆和復制。中國只有一個魯迅,中國也只有一個李白,中國也只有一個杜甫,中國也只有一個曹雪芹,只有一部《紅樓夢》,而且只有八十回再加后續(xù)四十回,哪個作家都是只有一個,怎么能來倆,照抄也不好看啊。再想,英國只有一個莎士比亞,英國有倆莎士比亞?法國只有一個雨果,只有一個巴爾扎克。魯迅有魯迅的年代,魯迅是作為一個精神的領袖,作為一個社會的良心,作為時代的一個代言人,作為一個青年的導師而出現(xiàn)的,原因就是那個時候這個社會已經(jīng)沒有權威,沒有精神上的權威,他跟現(xiàn)在的情況也不一樣了,我們現(xiàn)在很難設想現(xiàn)在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或者在座的中文系的學生,你們以嗷嗷待哺的心情等待著一位救星的到來,等待著一位精神導師的到來,說高舉起你們的火炬跟著我走吧,有人跟你走嗎?所以不同社會發(fā)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狀況下,人們對文學的期待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中國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把很多東西尤其是把文學道德化,有些人對于文學的期待實際上是在期待著一個圣人,咱們現(xiàn)在還沒有這樣一個圣人。瞅活著的作家,誰的模樣也不像圣人,也不像魯迅,沒有那么悲情,沒有那么嚴肅,沒有那么大的承擔。但是說這話的人忘記了不同的時期,就在文學史上能夠起到魯迅這樣的精神領袖的作用的作家也微乎其微。李白喜歡月,喜歡喝酒,杜甫好一點,叫詩圣,還有好多的也在那兒嘆息。曹雪芹更不是,他絲毫沒有,在他的作品里面并沒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這樣的一種高姿態(tài)。外國的作家也是這樣。
關于魯迅和張愛玲
我再講一個話題,我其實是講我的困惑。在大家懷念魯迅,談魯迅,思念魯迅,閱讀魯迅的同時,不斷地重復當然也會讓人感到厭煩,與此同時也增加了對張愛玲的熱度。張愛玲的寫作有一種生動感,她對顏色的描繪很好,對有些人情世故的描寫,特別是對于女性心理的描寫十分不錯,但是,有那么好嗎?我實在是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希望待會兒有人能夠對我進行一點兒教育(我已經(jīng)下過多少次決心了,我既沒有教條主義,也沒有政審的意識,我也沒在專門部門工作過,說是由于政治上對張愛玲不感興趣,就說她寫得不好)。我找了她的書,我還上國家圖書館借了她的書,但是沒有幾篇我是認真地讀得下來的,因為我需要更多的藝術的想像,我需要更深的對歷史,包括對人生的思索。張愛玲說,要是沒有發(fā)生過的事,我還是寫不了的,我只能寫發(fā)生過的事。這個話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不是天真了一點?再說得尖銳一點,是不是低能了一點?現(xiàn)在張愛玲已經(jīng)快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代表了,我覺得有點悲哀。如果選擇同時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更愿意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我覺得也很有意思。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我們談現(xiàn)當代文學,那個時候唯周楊馬首是瞻,周楊怎么說的看講義,但是現(xiàn)在至少有一半是唯夏志清馬首是瞻,其實我們還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認識。
我在這兒講了半天,介紹了一些情況,談了許多自己的困惑,也是白白地耽誤了大家的時間,非常對不起!
提問:
關于網(wǎng)絡文學與青春文學
網(wǎng)絡作家:您剛才提到人們對文學有道德上的期待,但是對網(wǎng)絡作者來說,幾乎沒有受到來自這一方面的影響,對此您怎么看?
王 蒙:我個人從理論上對網(wǎng)絡文學完全是支持的,我也做過極少量的瀏覽,包括有些人的很尖銳的博客我也都讀過的,里面的某些見解還是好的,是可取的。另外我還給例如安徽的一個網(wǎng)絡寫手叫爾林兔,她寫有關《紅樓夢》的書,她寄給我那個書,我還給她寫過評論和序。還有一些書,我讀著也很有興趣,比如《明朝那些事兒》,但是更多的情況我還不知道。我還參與過一些網(wǎng)絡的評獎,或者發(fā)獎什么的,所以從總的態(tài)度我是支持的,我也是喜歡的,但是太具體的我也說不出來。我不覺得寫了以后你是先在網(wǎng)絡上發(fā)也好還是在出版印書也好有特別大的矛盾,連寫新詩、舊詩我也不覺得有多么大的矛盾,我覺得就是根據(jù)自己的題材自己的作品的情況先上網(wǎng)也行先出書也行,愿意用文言文寫的我也不反對,你愿意用英文寫,我更不反對,因為我一直就是,老想學好英文,老學不好,你要用英文寫的,那我看著我更羨慕,更有奮進,你好好用英文寫。
SO大展學生評委:我看到PPT以后,看到王蒙先生第一部作品是十九歲寫出來的,按照這樣來算的話是青春文學,青春文學每代都有,可能在我們這一代成了一個事,我想聽聽王蒙先生的意見?
王 蒙:我覺得跟媒體的炒作也有關,年輕人低齡寫作,現(xiàn)在不是十九歲的問題,現(xiàn)在好像還有,最低齡的六歲也出詩集了,當然這比較少,特例。但是我不贊成不同的年齡的人在那兒互相嘲笑,互相攻擊。青年人肯定有青年人的銳氣,他的體力,老年人有老年人的優(yōu)勢。我特別喜歡老舍《茶館》里面的一句臺詞:年輕的時候有牙沒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沒牙。這個牙你怎么解釋都行,“80后”渾身都長著牙,想咬一口就能咬一口,而且能咬得起來,但是花生仁少了一點,就是讀過的書,走過的路,吃過的鹽,經(jīng)歷的挫折少一些。老年人是花生仁越來越多了,但牙已經(jīng)不行了,銳氣沒了,硬東西也不敢嚼了。尤其是作家,你要是寫好了,你總是會寫好的,用不著貶低別人,如果寫得差勁的話,就算全國的作家被你罵死,你還是寫得比較差勁。如果寫得特別好的話,別人更好,大家一塊兒好,咱們變成黃金時代,黃金集團,一個實力集團,更是夢寐以求的事,所以不要造成一個氣氛,按年齡分。我是“30后”,離“80后”差五十年了,但是我在沒有得到“召喚”前,沒有完全癡呆以前,我這不是,我也寫,該說笑我也說笑……
2009年9月27日·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