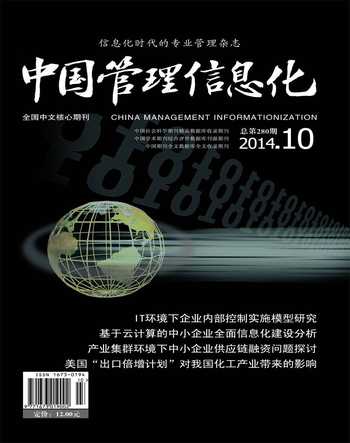網絡公共輿論危機的形成與應對策略研究
李晶 謝金林
[摘 要] 從新意見階層的興起、政治信任的流失和網絡輿論倍增機制3個方面分析當下網絡公共輿論危機形成的原因,并為政府部分應對危機提出了議程重置、話語權重構和政府—公眾對話程序建構3項應對策略,以提高政府新聞執政能力。
[關鍵詞] 網絡;公共輿論;危機;策略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0. 062
[中圖分類號] C912.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4)10- 0088- 03
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5.13億,全年新增網民5 580萬;互聯網普及率較上年底提升4個百分點,達到38.3%。中國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同比增長17.5%,與前幾年相比,中國的整體網民規模增長進入平臺期。[1 ]互聯網成為中國人生產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是不爭的事實。從BBS/論壇到博客,從SNS(社交網站)到微博,“新媒介的出現和逐步擴大,深刻影響著轉型行中國社會的結構,網絡公共輿論成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建制變革的重要推動力。”[2]2003年被稱為“網絡輿論元年”網民開始主動參與到寶馬車撞人案、孫志剛事件、非典等一系列重要社會事件。其后數年,三鹿“毒奶粉”“躲貓貓”事件、鄧玉嬌案、宜黃強拆自焚事件、李剛之子案,通過網絡、手機等新媒介與傳統媒體互動形成的網絡媒介事件,促發著公共輿論危機的持續升溫。2011年“7·23”動車追尾事故和郭美美事件更是引發網上網下人聲鼎沸。
網絡作為中國公眾言論表達的重要載體蓄積著巨大的輿論能量,網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政府、行政部門的管理環境,促使政府、行政部門要以新的理念和姿態來應對和化解網絡公共輿論危機,進而提升新聞執政能力。
1 網絡媒介事件與公共輿論危機
近年來,國內學界、業界對與網絡有關的媒介事件研究中比較常用的是“網絡群體性事件”,這是我國政府管理部門對網絡上熱議的媒介事件的官方稱為,自2008年期大眾媒體開始廣泛使用。然而學者師曾志(2010)指出,群體性事件在政治意涵上更強調的是單一身份的暴力甚至暴亂,而網絡媒介事件實質上最深刻影響到的是公共輿論。在與群體性事件概念的比較中,該學者強調網絡社會群體事件的新社會運動性質,從文化的視角呈現集體認同的建構功能。在此也認同并使用網絡媒介事件這一概念,即“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互動生發的公眾輿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討論、爭議等,對人們的思想、觀念乃至行動會產生深刻影響的媒體聯動效益甚至行動,其具有突發性、分層性、即逝性、媒體聯動性等特點。”[2]
“公共輿論”在此僅指政治輿論,是公眾“對特殊政策和問題的反應”, “是有關政治和社會事務散亂的理念和態度”[3]。“輿論危機就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中,各類媒體對某人、某單位、某政治集團或國家片面、偏激或敵對的輿論占據主導地位、并使絕大多數受眾的情緒、思維和行為等產生共鳴的一種輿論傳播現象。”[4]據此,網絡公共輿論危機是指由政府成員或組織的不恰當行政行為引發的,通過網絡傳播的眾多負面輿論聚合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使被輿論對象處于極大輿論壓力之下。
2 網絡媒介事件促發公共輿論危機的原因
2.1 政治信任的流失
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公眾知情權意識不斷提升。在突發事件中,網民渴求真相,但是正如祝新華等人在《2011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指出的: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不公開依然是常態,公開是例外。網絡時代下的“全民偵探”,與一些政府部門試圖掩蓋真相的拉鋸戰繼續上演。例如,近年來“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隨著網絡傳播而相繼曝光,嚴重影響了公安機關的公信力。“自‘躲貓貓事件進入公共議程之初,網友就表現出對作為官方機構代表的云南晉寧縣警方的強烈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不僅停留在質疑其所傳達的信息的層面,還上升到了質疑其行為的層面。” [5]在溫州錢云會非正常死亡案中,盡管目前完整的證據鏈支持這是一場集中了太多巧合的交通事故,但多數網民就是不相信。在目前官民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躲貓貓”事件和錢云會案被網民“合理想象”和無限放大。由于長期的信息封閉給公眾造成官民對立的思維定式,也由于公安部門自身公信力的不足,從而形成了公眾和政府對信息的對立解讀,使得政府與公眾之間非但不能互相對話,并達成共識,更不能彌合兩者之間的信任鴻溝。
正如網絡上流行的“塔西佗陷阱”,即“一旦失去公信力,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不論這是否是“西方政治學的著名定律”,還是網友們的杜撰,修復和提振政府的公信力,是應對輿論危機的關鍵,更是政府形象樹立的根基。
2.2 轉型時期新意見階層對網絡輿論的主導
在我國傳統媒體受到嚴格管理,并被賦予“輿論導向”的責任。網絡技術普及使用深刻影響著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結構,互聯網成為個人、民間組織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力量,改變著傳統的“強政府弱社會”格局。網絡成為人們言論的重要載體,“尤其是日益發展的微博,已經成為倒逼政府轉型的最大社會推手”[6]。多年從事網絡輿情研究的學者感嘆道:“中國網絡輿論場的強度,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家”[6]。強大的網絡輿論場孕育的是新意見階層的崛起和壯大。2008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中把關注新聞時事、在網上直抒胸臆的網民成為“新意見階層”,并引有關部門的調查結果描述了“新意見階層”的特征:“常在網上發表言論的網民,35歲以下的占78.8%,大專以上學歷的占79.2%,月收入2500元以下的占68.6%,在企業工作的占36.9%”[7]。時隔3年,社會各階層都習慣于上網“喊話”了。弱勢群體、“公共知識分子”是網上最早的發言者。2011年“動車追尾事故成為一個契機,推動中等收入階層集體登上網絡輿論平臺”[6],而高收入階層卻成為很多公共議題的熱心參與者,其微博粉絲大多上百萬。新意見階層的不斷壯大正是網絡虛擬社會“去中心化”特征的呈現。電腦、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的集成,SNS、微博客等Web2.0應用的快速發展,促進了互聯網信息承載量的急劇增長,信息資源前所未有的豐富。但同時,海量級、碎片化的信息增加了人們獲取有效信息的時間和成本,而“新意見階層”在網絡傳播中擔負起前所未有的意見領袖的中介功能。
①諸如“躲貓貓”這樣荒誕離奇,疑點重重的案件,“郭美美Baby”以“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微博炫富,都在第一時間觸動了“新意見階層”敏銳的感知,他們在論壇、微博上轉發、評論,引發了公眾對公安及司法機關的不信任,也引爆了公眾對官辦慈善組織的質疑和深深失望,甚至將矛頭指向整個國家的“公權力”。②與傳統意見領袖接收信息進行加工、解釋而后以微型傳播(如面對面的交談)的方式傳達給其他受眾或追隨者不同的是:“新意見階層”以新媒介為平臺的二次傳播是疾速的社會網傳播,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③微博、SNS、論壇等具有很強的黏性,參與者會持續關注、轉載事件的發展,加之網絡環境的匿名性特點,為公眾了解信息、表達意見、參與社會進程提供了更為廣泛的空間。“新意見階層或新意見領袖的出現,影響著公眾輿論的生成和發展,網絡等媒介和傳統媒體互動所形成的網絡媒介事件,成為公眾輿論的非常重要的生發源,進而構成了組織和溝通社會的重要力量,在當下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2]
2.3 網絡公共輿論倍增機制
當前互聯網進入微博、社交網(SNS)、即時通訊(IM)等為主導的Web2.0時代,公眾成為網絡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消費者,互動、共享的網絡傳播理念及其相關技術的使用,為網絡輿論提供了充分的技術條件。借助移動互聯網終端,隨時、隨地、隨人的“公民報道”成為可能,正在深刻改變社會輿論的生成機制。3.18億中國手機網民人,可以隨時隨地上網發布和瀏覽信息、發表和分享意見。在任何的突發公共事件中,任何一個在場的人都可能上網發送文字、圖片、視頻點燃輿論的火種。以“7·23”動車事故為例,2011年7月23日20時34分發生追尾,21時01分D3115次動車乘客發出第一條微博:“童鞋們快救救偶吧!!!偶所乘坐的D3115次動車出軌叻!!!偶被困在近溫州南的半路上叻!!”自媒體的出現,讓每一人都可以實施“現場報道”。超過5億網民面對虛擬和匿名的網絡環境,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達空間和話語權,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探討問題、形成觀點、引導并放大輿論,成為參與輿論的主體。更加之無線網絡的便捷,公眾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參與輿情討論;另外還將數量龐大的城鎮低收入人群以及農民工納入到了網絡輿論場中。網絡媒介事件促發的公共輿論中,媒體文本在以幾何級數增長,意義則呈現多元化,所蓄積的輿論力量是傳統媒體下無法比擬的。正如約翰·菲斯克認為的,媒體文本總是處于持續生產的狀態中,它由源源不斷的材料組成,所產生的也是源源不斷的意義。[8]尤其在公眾長期感到缺乏社會協商的機會和公共言論空間時,網絡成為“信息自由”的另類釋放通道和公眾輿論的放大器。任何的官民沖突、警民沖突、城管與攤販沖突、交通事故乃至群體性事件在新媒介和統媒體互動中,從單一網民的抗爭,到公眾、媒體、社會精英和政府共同參與,以網絡聚集方式引發的巨大輿論壓力。
3 網絡公共輿論危機的應對理念與策略
面對危機人們慣常的思維和行動模式更多地拘泥于一時一地,從組織自身目標出發解決問題。網絡社會“去中心化”和“去主體化”的特征,一方面使得現實中的等級制度一步一瓦解,個體可以自由選擇信息、發表信息,決定和誰進行自由交流;另一反面網絡交流沒有主客之分,上線者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的發出者,始終處于一種主體與客體交互的不確定狀態之中,這與傳統世界中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交互模式截然不同。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不同社會階層有著各異的利益訴求,并都借助網絡激烈而大聲地“喊出”,各級政府和行政部門必須擺脫過去的以我為主的思維和行動模式,更多地考慮組織面臨的問題所涉及的相關公眾、組織,在與各方利益博弈中取得平衡,才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和危機的應對。
師曾志(2009)以汶川地震災后救援重建研究中國公民社會發展時,提出了公共傳播的概念,即任何組織在處理和化解危機中所應有的一種思維和行為模式,這種模式強調的是以組織所面向的現實的、潛在的公眾為考慮問題的思路和出發點,在與這些公眾利益的博弈過程中達到組織利益的最大化[9]。在當下社會變遷中公共傳播理念的確立,正是轉變社會管理思想與思維方式,推動社會關系、社會建制變革的一種全新視角。在處理和化解危機的利益博弈中,需要“重構組織合理化運行的機制,而這種重構的機制是以改變組織以往運行的方式為代價的”,“這種改變的特點是在構成中完成的”。[9]
3.1 議程重置
“以往的傳播形式主要是國家、政府或組織勸服和影響受眾的工具,這便是權力話語,而網絡傳播的出現,則改變了這種格局……網絡世界中沒有統一的‘主義,沒有絕對的權威”[10]網絡獨特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傳播的話語權分配,打破了政府對議程設置的壟斷權。轉型時期社會輿論的特點與網絡傳播規律決定了網絡空間政府輿論危機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 政府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不是如何運用行政權力對網絡輿論進行封殺或是沉默, 而是要考慮如何在危機爆發之時, 通過何種辦法盡早爭取輿論議題設置權力。從而引導輿論方向, 降低危機帶來的負面后果。
網絡公共輿論危機爆發時, 負面輿論大多具有非理性的特點, 而且媒體的報道有時也只是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而對事件進行片面的放大。事實上整個輿論就被設定了方向, 快速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如果政府只是對其作出回應, 而不能重新設置議題, 化解危機的所有工作都會處于被動之中。化被動為主動的唯一辦法就是積極爭奪輿論的話語權, 重新設置議題。“輿論議程設置權實質是虛擬環境主動創建權。”[11]議程重置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①健全政府網絡新聞發言人機制,使其常態化。建立網絡新聞發言人制度,旨在通過網絡即時、主動、準確地發布權威信息, 盡快澄清虛假、不完整信息, 消除誤解, 化解矛盾。設立網絡輿論發言人制度就是要壓縮炒作空間。如何防止過分的炒作擾亂社會秩序, 唯一的辦法就是政府在第一時間將權威的消息公之于眾,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網絡發言人制度不應該是危機事發時的應急機制,而應該成為政府進行輿論引導的常態機制。要建立完備的輿情預警體現,同時做到敏感事件信息及時公開,熱點事件及時回應。②以求真務實的態度增進政府與媒介的合作。民主政治時代新聞自由是最基本的權利,政府不能運用行政權力剝奪新聞機構的自由。政府與媒體如何合作,政府傳播與媒體傳播如何良性互動,直接影響到危機的解決。政府必須以求真務實、信任、公開、寬容的態度對待社會媒體,通過制度化的信息傳遞機制,引導社會媒體輿論報道的方向。否則,政府與媒體之間相互猜疑必然導致政府權威話語與社會媒體報道互相矛盾,使事件陷入“××門”的困惑之中,增大炒作空間,進而也散失了議程重置的主動權。
3.2 話語權力重構
圍繞著熱點事件,各種爭議是難免的。在政府、媒體、公眾就事件引發的話語權博弈中,政府作為擁有行政權力和輿論矛盾指向的一方,需要主動促進“政府—媒體—公眾”之間良性互動,并在互動中積極爭取話語權,引領輿論的方向、促進事件的解決,那肯定有助于維護良好的“政府—媒體—公眾”平衡關系,有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與提升。
網絡時代由于信息傳播模式的轉變,傳統意義的政府話語權被平面化非中心的網絡結構解構了,政府與公眾必須在網絡媒介中重新分配并爭奪話語權。如果政府的話語能夠被公眾所接受,并能夠彼此就有關公共事件進行平等對話與協商,“政府—媒體—公眾”關系才有可能良性互動,“政府—公眾”共治的良好平臺才有可能建立起來,從而使得社會問題在理性的商談中達到共識并獲得良好的治理。但是,在自由的、平民化的網絡媒介之中,政府如果不能獲得話語權,不能有效地引導公共輿論,事件就會不斷地惡化。隨著傳統的源自等級制的話語權的解構,政府如何爭取話語權確實是新媒體下必須思考的問題。誠實是公關的首要原則,也是獲得公眾認可并在事件傳播過程中主導話語權的首要原則。
在自由化的網絡世界里, 誰有話語權, 誰可以引起網民的共鳴, 誰就主導網絡輿論的方向。相比公眾而言, 政府在網絡資源的占有上具有絕對的優勢, 積極利用主流網絡爭奪話語權, 就有能力在危機爆發之時, 通過第一時間的公開信息掌握話語權, 將公眾對事情的泄憤轉變為對事件的本質及其解決之道的理性思考。這樣, 一邊倒的輿論才可以得到適當的平衡, 輿論方向才可以朝積極的一面發展。如果政府對熱點問題不能及時作出回應, 權威聲音在熱點問題上失語、妄語, 就不能滿足網民的知情權的要求, 網民則會從別的渠道獲知有關事件的信息, 甚至從各自的角度對事件作出不同的解讀, 從而使一個事件有眾多的不同的版本, 使事件處于一種不可控制的態勢之中。正如俗語所言, 真理還沒有來得及穿鞋, 謠言已行了千里 , 對于熱點事件, 政府不僅必須作出回應, 而且必須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
3.3 政府—公眾對話程序建構
抗爭是網絡群體事件的精神內核,也是網絡群體事件產生的目的。[12]近年諸多網絡媒介事件表現出的都是網民為代表的公眾對政府進行話語抵制。有學者指出這種政治色彩的言行有可能滑向民粹式的民主狂熱。政府在應對網絡輿論危機時,最好辦法就主動打破“官民對抗”的僵局,建構起政府—公眾平等對話的程序,促進政府與公眾之間的相互理解, 推進共識的形成, 從而引導網絡輿論向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面發展。信息傳播過程本質是通過信息分享達到相互對話、相互理解的過程。 網絡世界里,等級制權威被消解,自主性原則發揮得淋漓盡至,信息的接受者同時又是信息的傳播者。某個事情只要能夠激起公眾的關注,就產生出燃燒效應,每一個有著自己意識、情感、目的和動機的個人都可以運用多種方式即時參與到事件的討論中,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并且通過對話相互影響,最終形成網絡輿論。當然,等級制權威的消解并不意味著每個結點的能量是相同的,網絡中的每一個主體表達能力與表達欲望肯定有著差別,因而對共識的最后形成所起的作用也會不同。但是,輿論的方向并不由某一個人所決定而是所有參與者合力的結果。網絡輿論是網民共識的體現,是網民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
輿論是不可能強制的,如果不能抓住網民的心理,不能引起網民共鳴,思想灌輸所能起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要在政府與網民之間建構起平等的對話, 就必須加強以下4方面的工作:①真誠對待網民。如果政府不能以真誠的態度面對公眾, 或者文過飾非,或不及時滿足公眾知情權, 那么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任就無法建立起來, 就無法就公共事務進行理性的協商與對話, 更不用說達成共識并對輿論進行引導。② 政府話語必須體現公共利益的要求。政府作為公眾的信托機構, 必須以公共利益作為出發點, 站在公眾的立場上, 維護公共利益的實現。相反, 如果政府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 或者想法開脫責任, 把政府與公眾對立起來, 勢必激起公眾的反感, 成為輿論的譴責對象, 使批評性輿論更加尖銳, 也就喪失了引領對話的能力。③ 政府必須以平等的態度與網民進行溝通。在以對話為基礎的交往行動中, 必須堅持主體間的平等交互性而不能主客體二分, 把別的參與者當作操縱的客體, 通過言語操縱( 威脅或者引誘) 別人按照自己的意見行動,而是要通過平等的討論, 達成對共同生活的理解。權力話語只會造成主體間的彼此隔閡。在權力分散化、去中心化的平面網絡之中, 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獨白無論怎么樣都不可能獲得網民的認同與支持, 反而會使政府與網民之間的對立情緒加劇。④堅持開放的對話原則。如果要有助于共識的形成, 政府就要對不同的觀點進行開放, 而且對話內容也必須保持開放性, 除少數因法律規定之外, 都必須公開討論, 不能隨意以國家機密作為借口, 拒絕討論, 否則會加深公眾與政府之間的隔閡。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調查統計報告[EB/OL].http://www.cnnic.cn/research/bgxz/tjbg/201201/P0201201
18512855484817.pdf,2012-01-16.
[2]師曾志.網絡媒介事件及其近年來的研究現狀與特點[J].國際新聞界,2010(6):86-90.
[3][美]邁克爾·羅斯金.政治科學[M].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2:150.
[4]傅開強,張占勝.全球化時代輿論危機的現實探析[J].軍事記者,2007(7):24-26.
[5] 杜俊飛.沸騰的冰點:2009中國網絡輿情報告[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337.
[6]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2011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EB/OL].http://yuqing.people.com.cn/GB/16698341.html,2011-12-23.
[7]祝華新,單學剛,胡江春.2008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EB/OL].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zgshxs/content_171009
22_5.htm,2009-01-13.
[8]陸道夫.試論約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論[J].南京社會科學,2008(12):40-47.
[9]師曾志.公共傳播視野下的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媒體的角色——以汶川地震災后救援重建為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343.
[10]張品良.網絡傳播的后現代性分析[J].當代傳播,2004(5):53-56.
[11]謝金林.網絡輿論危機下政府形象傳播的困境及對策[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10(5):16-21.
[12]杜俊飛.網絡群體事件的類型辨析[J].國際新聞界,2009(7):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