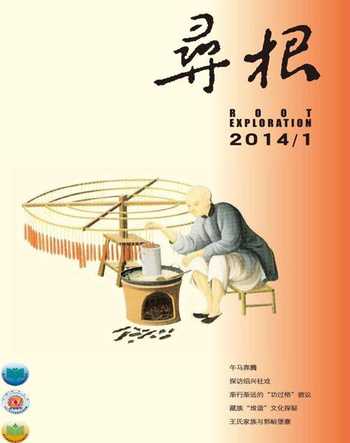閩臺福德文化之淵源
湯漳平
福德正神俗稱土地神或土地公,究其淵源,應來自我國先民的自然神崇拜,而傳人閩南地區的土地公崇拜,很可能是來源于先秦的楚文化。
從近數十年出土文獻資料發現,在多座楚墓的祭祀竹簡中,有相當數量是祭祀各種名號的土地神。閩南人多稱其由河南固始移民而來。固始本為楚相孫叔敖的封地,其周邊之申、息、羅、蓼、蔣、江、黃等國,均在春秋時期被楚國所滅,此后該地區即成為楚國向中原發展的重要基地。楚國著名的“申息之師”,也出于此,因而豫南地區是楚文化的重要區域。后楚國雖為秦所滅,但楚文化在這一地區有很深厚的積淀。
唐代,這一地區民眾移民閩南,就將其對土地神的信仰帶到閩南。農耕時代土地和民眾生活密不可分,對土地的依賴而產生出的敬畏,使得“土地公”成了民間最不可忽略的神祇。因此在開拓閩南和墾殖臺灣時,這一信仰自然得到進一步的傳承與弘揚。
一
福德正神,俗稱土地神或土地公,是閩臺地區共有的一種十分廣泛的民間信仰。雖然在中國,無論南方或北方,都有許多種類的民間信仰存在,但在神靈的數量和祭祀的范圍上,南方尤其是閩南地區和北方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北方祭祀的神祇,無論其宮廟數量還是神祇的種類,都比南方要少得多。筆者雖是南方人,但曾在上海郊區和河南工作長達四十年之久,對當地城市鄉村也都廣有接觸,這些地方的民間信仰所涉及的神祇、宮廟寥寥可數。而閩南雖然同樣經過多次所謂“破四舊”的政治運動,但民間信仰的興盛依舊不改。街頭巷尾,各種名目的宮廟時時出現,吸引著世人的目光。同時,這些宮廟頻繁舉辦的各類娛神活動,也成為閩南地區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種情況,頗能引起北方來的民眾好奇。
我從閩南到臺灣,沿途發現,臺灣不僅宮廟眾多,而且其規模之大與裝飾之富麗堂皇,較閩南有過之而無不及。臺灣的民間信仰之盛,恰與閩南相同,究其原因,則都認為臺灣既多為閩南移民之后裔,因而這種多神信仰的風俗,應當是來自原鄉的閩南。考察臺灣祭祀的神靈和閩南共有的四大民間信仰——媽祖、關帝、保生大帝與開漳圣王,除關帝信仰是來源于中原外,其余則皆為產生于閩南的民間神祇。從閩南傳入臺灣的神祇也正是分為兩類:一類是從中原地區傳入的神靈,例如天公、玄天上帝、東岳大帝、關帝、趙公元帥等。另一類是產生于閩南本土的神祇,是閩南人在開發過程中,因為客觀需要而逐漸形成的信仰,如媽祖為海神,佑護閩南人在萬頃波濤中保得平安;保生大帝是庇佑民眾免除疾病折磨的醫神;開漳圣王為安邦守土之神,保護本族群不受外來強寇的侵犯。
那么,福德正神的信仰來源于何處?是本地產生的,還是源自北方中原?如果是源于中原,那么應當南北方祭祀比較一致,但為什么北方少而南方多?這些問題確實值得進一步思考與探究。
土地神的起源應當很早,它是中華民族祖先遠古時代自然崇拜的產物,不可能晚至西周時期。古代先民在其生存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嚴酷的自然環境的考驗,同時也感受到大自然給予人的種種恩惠,于是產生對天、地、日、月、星辰、山川等自然物的崇拜與感恩,由此催生了內容豐富的古代神話,并形成對自然神的崇拜。土地崇拜即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禮記·郊特牲》載:“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這個解釋頗有道理。而為了表示感恩,便有了對神祇的祭祀,古人認為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把祭神列為和打仗一樣,是國家頭等重要的事,這是今人所難以想象的。
對于神祇的祭祀,古人是按照“天神地祇人鬼”形成系列,天神和地袱屬于自然神,是自然崇拜的產物,由是而有玉皇大帝、日、月、云、雨、雷、電、司命、司禍等天神。而地祇則有后土(與皇天相對應的),各山川之神(如五岳、四瀆及各名山、大川、大湖之神)。至于人鬼,則有歷史上為族群的繁榮昌盛作出各種貢獻的名人、英雄,同時也有失敗的英雄,如共工,甚至還有惡人,如“過澆”。過澆是夏初的一個惡人,為幫寒浞篡位,殺害了夏后相,還曾亂倫,與他的嫂嫂女歧茍合,結果被少康所殺。可是他力大無比,能夠“釋舟陸行”(《楚辭·天問》),即把船放在陸地上推著走,所以他死后被民間供奉為水仙神。還有那些不得善終的殤鬼,也往往是在祭祀的行列中,如《楚辭·九歌》中祭祀的人鬼是“國殤”,即死于國事的那些將士,這當然是應當祭祀的。但漢代祭祀天神、地祇之后,要祭祀的人鬼卻是秦二世胡亥。因胡亥也是“殤鬼”,漢朝怕他出來作祟,影響大漢江山的穩定,因此將他列入祭神的系列。
有記載的地祇祭祀,最早是后土。關于后土的來源,有多種說法,早期記載中多認為后土是共工的兒子。《禮記·祭法》載:“共工氏之霸九州島也,其子日后土,能平九州島,故祀以為社。”《左傳》中也載:“共工氏有子日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山海經》中的《大荒西經》《大荒北經》《海內經》等均有相同記載。但至今保存歷史最早的后土祠——古代位于汾陰(今山西萬榮)祭祀的卻是女媧。而且從漢代起,歷代帝王曾多次前往祭祀。這種情況應當與傳統的陰陽觀念有關。天為陽、地為陰,《易經》中已作了這樣的表述,既然如此,地祇后土以女媧這位能“摶泥土作人”的女神充任,自然最適合不過了。
《史記·封禪書》引《尚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可知地祇之祭,自堯舜時代已有。
《史記·封禪書》引《周官》也載:“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I,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
二
閩臺之民既為中原移民之后裔,其土地神祭祀,是否源自北方中原?應當說既是,又不是。
所謂是,指地祇祭祀確為上古之祭典,有文獻可證。所謂不是,是因為如果遵守的是上古祭禮,那就有嚴格的限制,不是人人都可以隨時隨地致祭的。隨時隨地祭拜不列入國家祭典的神祇,被稱為“淫祀”,即不遵守禮法的祭祀。閩臺之民眾對土地神的祭拜是不分時候的,只要有問題祈求土地神幫忙解決,就立即可以去廟里祭拜,這種風氣,我認為就與楚、越等南方民俗影響有關。
可能有人會問,不是說閩南人都來自河南中原地區,怎么會和楚、越有關呢?這應從歷史源頭說起。今日不僅閩南人,所有福建人,都說自己的祖地在河南固始。可是,對于固始這個地方的歷史情況如何,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很多。
我們一般講中原文化,發端于河洛文化,即今黃河與洛水交匯的一片區域,并以此為核心,向西擴展至陜西,向北延伸至山西。上古三代的夏、商、周,其國都雖然不斷遷徙,如夏都六遷,商都七遷,但都沒有離開這一區域。而其周邊甘肅一帶為西戎,內蒙古一帶為北狄,山東一帶為東夷,長江以南則為南蠻。河南固始其地理位置在湖北、安徽與河南交界的三角地帶,已屬淮河流域,這里在商代是淮夷文化區,自古至今,受安徽一帶淮夷文化影響最大。到春秋戰國時期,吳楚間多次在這里交鋒。20世紀70年代,這里還發現了吳國最后一位國君夫差的妻子句吳夫人的墓地。后來越滅吳,楚滅越,當然就不再有這種爭執了。春秋時期,楚國在盡滅漢陽諸姬姓國后,揮戈北上,直取淮河流域廣大地區。今河南信陽一帶的古代諸侯國如樊、羅、申、江、黃、息、蔣、蓼均于這一時期為楚所滅,而往北及往東的沈、不羹、葉、陳、蔡、應、六等也接連并于楚,所謂“傷心莫過息夫人”的故事便發生于楚文王時期(公元前689~公元前675年)。這時還是春秋早期,楚文王先后滅了息、蔡、黃諸國,并在這些地方建立了郡縣,將楚國的勢力抵達淮河流域,從而建立了北上中原的橋頭堡。特別重要的是,他在這里建立了一支強悍的軍隊——“申息之師”。這支“申息之師”在楚國歷史上曾多次承擔重要的軍事任務,為其興盛立下了不朽之功。息國就在固始的北面,與之土地緊密相連,自然很快為楚所滅,如固始的蔣國,在公元前617年即被楚兼并。楚莊王時(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著名楚相孫叔敖的家鄉便在這里。此后,直至楚國滅亡(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在400多年的時間里,固始一直是楚國的屬地,可以說完全受到楚文化的浸潤與影響。孫叔敖為官清廉,死后其家無恒產,十分困難,楚王就將固始封給他的后代。直到唐代,固始仍屬淮南西道管轄,而不屬中原道。
楚國的習俗和中原地區不同,崇尚鬼神,流行巫歌,被稱為“巫風”,楚著名詩人屈原留下的楚辭詩篇,被日本學者藤野巖友稱為“巫系文學”,《楚辭·九歌》是典型描寫楚人祭祀內容的作品。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九歌序》中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結,托之以諷諫。”
《九歌》十一篇,除最后一首《禮魂》是送神曲外,其余十篇分別祭祀了十位神祇,它們是東皇太一、東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國殤。這十位神祗中,東皇太一、東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為天神;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為地祇;最后配之以國殤,即為國犧牲的將士之魂,符合于天神地袱人鬼的祭禮。筆者認為它是楚王室的祭典,自然是比較正規的祭典。
但是,楚國還盛行“淫祀”之風,也就是超越祭禮的祭祀。大概這種祭祀的音樂很動聽,叫“巫音”,因此在楚地流行,稱為“巫風”。這種“巫風”,據《國語·楚語》載,它其實最早是盛行于上古時期:“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而且自九黎傳至三苗,又傳至商朝。《禮記·表記》引孔子的話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商書·伊訓》中也記述當時的情況是:“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周取代商之后,在北方,由周公制禮作樂,加以規范,然而在南方,這種“巫風”并未停止。一方面是所謂“南蠻”的九黎三苗被趕到南方后并未改變它的習俗,依然保存下這種“巫風”盛行的風氣。其次,按照郭沫若的考證,楚人從北方遷到南方時,把商人原有的淫祀之風也帶到南方。三苗的傳統和商人的遺風相結合,形成楚國“巫風”的興盛。“巫風”,其實是一種原始的宗教,也可稱為巫教。其后,楚在其發展壯大過程中,吞并了吳、越、陳等地,這些地方也是“巫風”盛行地域,所以“巫音”之風靡全楚,就是理所當然的。陳國雖與宋、鄭等國相鄰,卻也是“巫風”興盛的地方。《詩經·陳風》中首篇《宛丘》,就是描寫巫舞的詩篇: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翱。
《陳風》第二篇的《東門之柑》亦是如此,那位在“東門之柑,宛丘之栩”,婆娑其下的“子仲之子”,其實也是位巫風的舞者。《詩集傳》引《詩序》云:
陳,國名,太難伏犧氏之墟
……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后,以其女大姬妻其子。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
這是講陳國也是巫風盛行之所,而陳國就在固始北面。就是說,這一大片地方,風氣大致相同。
“巫風”盛行,其結果并不美妙,有的人還把楚國的衰亡同其喜好“巫風”聯系在一起。如《呂氏春秋·侈樂篇》載:“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千鐘、大呂是用青銅制作的大型鐘鼓樂器,形制巨大,耗費大量人力物力,所以宋、齊因此而衰。而“巫音”則是祭祀時的樂舞,《呂氏春秋》認為楚人沉湎于此,影響了國家的發展,導致衰敗。當然,是否如此,另當別論,但“巫風”在楚漫延,則應是事實。
也許有人會問,從楚國滅亡到中原移民入閩,其間經歷了數百年之久,難道社會風氣和習俗不會發生變化嗎?那么我們不妨看看《漢書·地理志》中的相關記載。
《漢書·地理志》在分別記載了漢代各郡的戶口、土地、領縣之后,又記載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在記陳國時,有這樣一段話:
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舜后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日:“東門之檸,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這段話雖與《詩序》陳風前之語略同,而時則已過三百年矣。又楚地,《漢書·地理志》(下)載: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氳贏蛤,食物常足……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在談到吳越的民風時,則說:
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略同。
班固在寫作《地理志》時,既有對歷史的回顧,又有對當時狀況的敘寫,可知至東漢時風氣依然如此。《地理志》在眾多郡縣中,獨對陳、楚、吳、越之域書以“信巫鬼,重淫祀”“其俗巫鬼”,可知當時南北異俗已形成,非獨今日如此。
作為昔日楚地的固始,其承傳的風氣也可想而知。
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蓬勃發展,地下出土的一批批文物大量涌現,為今日學人提供了第一手數據,得以探知古人生活時代的真實狀況。簡帛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已出現在當代學人的面前。運用最新出土的簡帛文獻數據,可以讓我們解讀許多過去難以破解的問題。我很感興趣的是這些年來,在出土文獻中有了多批有關楚人祭祀內容的竹簡,通過對這些竹簡內容的研究,也許我們能更好地知曉今日民間信仰與古代信仰之間的接續關系。
特別有意思的是迄今為止,出土的先秦竹簡都是楚簡。其中祭祀類竹簡最重要的有四批,即湖北江陵望山一號墓簡、天星觀一號墓簡和包山二號墓簡,還有河南新蔡葛陵墓簡。現將這四座墓葬基本情況概述如下:
(一)墓葬時間:四座墓葬時間均為戰國時代,其中最早的是天星觀一號墓,入葬時間應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楚威王時期;最晚的包山楚墓為公元前316年。前后集中在不足50年時間內。
(二)墓葬地點:湖北三座墓葬,均在楚國故都江陵周圍,荊門包山二號墓在江陵北邊不遠,為楚都的北大門。河南新蔡葛陵墓為古代蔡國所在地,和陳國相鄰,過去常以“陳蔡”連稱。
(三)墓主人身份:四座墓主人,兩位是楚國的封君,兩位是大夫級官員。其中江陵天星觀一號墓主人邸煬君和新蔡葛陵墓主人平夜君是楚之封君,按照楚國的爵位等級,楚之封君地位相當于楚國上卿,身份等級僅次于楚王而高于大夫,有食邑。江陵望山一號墓主人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孫,楚王的侍者,位為大夫。荊門包山楚墓主邵((方+它))是楚昭王后裔,生前是主管楚國司法的左尹,為令尹的重要助手。
(四)上述四批祭祀竹簡,其內容記載大體相同,都是墓主人生前讓巫職人員為其進行占卜、祭祀的情況的記錄,如邸煬君番勅的祭祀竹簡:“卜筮的具體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墓主貞問‘侍王是否順利;一類是貞問憂患、疾病的吉兇;一類是貞問遷居新室是否‘長居之,前途如何,等等。”(湖北荊州博物館:《江陵天星觀一號楚墓》)其余幾座墓的祭祀竹簡記載內容也大體相同。
祭祀竹簡中尤其引起我們關注的是有關祭祀神祇的記錄。祭祀簡所載的祭祀神祇,如同《周禮》所載,可分為天神、地祇、人鬼,形成完整的系列。其中地祇有社、芒社、后土、地主、山川、丘、大水、二天子、四方神、灶等44種。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楚人祭祀的廣泛性。如果說在江陵周邊的三座墓葬距淮河流域的河南固始還比較遠的話,那么新蔡葛陵墓葬就在固始西北,同屬淮河流域,正如研究者普遍認為的,葛陵簡的出土,為研究楚國腹地和東部疆土之間在卜筮、祭禱等禮制風俗方面的異同提供了寶貴的材料。況且,自公元前278年秦國將軍白起拔郢,楚頃襄王倉皇逃出郢都,東北保于陳城之后,今河南的東南一帶地區直到楚滅亡的數十年間,成為楚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影響之深是可以想見的。
四
閩南民眾自中原南遷入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首先是西晉八王之亂后,有中原士族南遷,但人數不多,主要到達閩南的地點是晉江一帶,當時民間信仰情況不甚可知;第二次比較大規模的中原移民為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從固始帶去的府兵3700余人及其后中原58姓移民共約萬人。目前有許多閩南民間信仰被認為是那個時期從中原帶入的。如謝安的廟,《漳浦縣志》卷二《方域》載:“東山廟,浦鄉里屯處皆有之,相傳陳將軍自光州攜香火來浦,五十八姓同崇奉焉,故今皆祀于民間。”第三次是唐朝末年的“三王入閩”,但“三王”入閩后主要活動中心在閩東福州。
閩南人對自然山川之神崇拜,應多數傳自中原,如天公崇拜,始于古代太陽神崇拜,鄭鏞在《閩南民間諸神探尋》中認為:“閩南人對太陽神崇拜應深受楚文化的影響。”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而玄天上帝、東岳大帝、炎黃二帝、關帝等,都應是從中原傳承而來。
土地神作為重要的自然山川之神,其傳人閩南雖無明載,但當與中原的祭祀風俗密切相關。在四座楚墓祭祀竹簡中,雖都有祭社的記載,但記載最多的恰恰是和固始相鄰的新蔡葛陵楚簡,其中不僅有許多里社的祭祀記錄,還有一些在里社進行相關活動的情況。記錄中以“某里人禱于其社”,例如:
梠里人禱于其社□(乙四88)
□里人禱于其社一□(零88)
□里人禱于其祉□(零168)
□堵里人禱于其[社](零116)
由于簡文過于殘泐,有些簡文只看得出是某里人祭禱的記錄,根據上列諸簡,可以知道它們應當也是該里之人禱于其社的記錄。例如:
(禾+者)室之里人禱口(乙三54)
楊里人禱□(零72)
大榗里人禱□(零11)
中楊里人□(零30)
□里人禱□(零524)
這說明該地區的祭社活動確實十分廣泛。閩臺兩地如此廣泛的土地信仰,其源自中原淮河流域也就可以理解了。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福德文化起源于遠古時期中華民族先人的自然崇拜,而不是產生于西周初年。出土的戰國時代楚地祭祀竹簡雖然有眾多祭祀地祇的記錄,卻沒有“福德正神”的記錄,說明在當時尚未有“福德正神”之名。“福德”,從字義探討具有美好的意義,“福”,幸福而美滿;而“德者,得也”,人們盼望“土地神”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幸福安樂,能夠歲歲豐收。因此“福德”代表著民眾對幸福生活的一種期盼。
(二)閩臺福德文化是閩南移民南遷時從中原固始傳承而來的,然固始在春秋戰國時期已為楚地,是楚文化東部的核心區。閩臺濃烈的“信鬼而好祀”之風,應當是受到楚文化的影響,閩南人自中原遷入閩南(主要是唐代)后,將早期的這種信俗保存到了今天,因此說閩南文化比較完整地保存了古代漢族文化的特色是很有道理的。福德文化的傳人和得到弘揚,也根源于此。農耕時代土地和民眾生活密不可分,對土地的依賴而產生出的敬畏,使得“土地公”成了民間最不可忽略的神祇。因此在開拓閩南和墾殖臺灣時,這一信仰自然得到進一步的傳承與弘揚。
(三)楚墓祭祀竹簡為我們認識相關的問題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它是最新也是最前沿的研究,希望有更多學者關注這一領域的研究,相信一定能夠有更多的發現和收獲。
當然,由于年代的久遠,史料的不足,有些傳承過程的中間環節也不甚明了,因此尚有待于大家作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