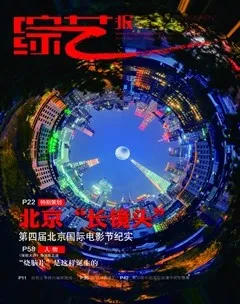關于北京,關于電影


評委會主席訪談
《綜藝》:吳宇森導演,擔任“天壇獎”國際評委會主席,有何感受?
吳宇森:我是經過很多考量才決定接受這個任務的。第一,我拍戲非常忙,《太平輪》還沒有拍完;第二,怕自己能力不夠。后來想想,能夠參與其中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因為我最喜歡看電影了,這次擔任評委,也讓我有機會看到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電影,還可以和來自不同國家的評委交朋友、分享經驗。尤其是印度導演拉庫馬·希拉尼,他的《三傻大鬧寶萊塢》我很喜歡。
《綜藝》:對于入圍本屆“天壇獎”的影片,有何評價?
吳宇森:從我們目前已看過的片子來看,質素非常高。
《綜藝》:評委會評選有無設定標準?評委內部意見不一致時,最終的評判標準會如何做出?
吳宇森:世界級影展,每個主席都會給評委一個導向,或者概念,也就是所謂選片的標準——當然并不是強制性的。譬如有一年我參加一個國際影展,那年剛好全球電影業都不景氣,主席就說應該關注電影的市場方面,希望打動更多觀眾。但是這次我跟各位評委溝通過,我們沒有主題,完全是憑評委自己的專業標準去判斷,通過民主投票來選擇。目前,我們對看過的電影都有不同的觀感。最后,如果大家意見無法統一,將用投票的方式選擇當選影片,我不會一人說了算。
《綜藝》:你心目中的好電影是什么樣子的?
吳宇森:能夠打動人心的才是真正的好電影。我最注重的是電影里的人性價值和人文精神。有時候我們的電影拍得很華麗,但欠缺感動人的力量。所以這次“天壇獎”,我和其他評委都非常注重電影傳達出來的情懷。
《綜藝》:作為少數在好萊塢獲得成功的華裔電影人,對于“如何讓外國人看懂中國電影”,你有何經驗可以分享?
吳宇森:在國際傳播方面,我們到現在還處在“想辦法讓外國人接受中國人的電影”這個階段。如何突破?我的師父張徹早就說過,“用西方的技巧注入東方的精神”。我們在香港時就很擅長用西方技巧來表達東方精神的電影,比如讓我進入好萊塢的《喋血雙雄》,它的內容很東方,但它的拍攝方式和剪輯技巧在法國一整年都被拿來做教材,美國的學校也用過它來講課。西方影評人說,看這部電影,不需要懂得中國的文字和語言,但他們會為這部電影憂傷、興奮,里面的幽默不需要懂對白也能讓人發笑。所以,一部電影要讓外國人看懂,剪輯技巧、演員的表演功底等都很重要。
《綜藝》:對于入圍的兩部華語影片,你如何評價?
吳宇森:《中國合伙人》我還沒有看,《一代宗師》看了,蠻喜歡。我很欣賞王家衛,當然我更欣賞章子怡,她在這部電影里的表現非常出色,很感人,動作戲也很漂亮。
《綜藝》:你拍攝的動作片別具特色,最近幾年為什么不再拍了?
吳宇森:拍動作片,好題材比較難找。想要拍出更好的動作片,唯一的辦法只有和徐克再合作,所以拍完《太平輪》后,我會拍一部像《英雄本色》那種類型的武俠片。我一直希望找到另一種境界,《太平輪》是一種新境界。接下來和徐克的合作希望找到另一種境界。我很懷念和徐克他們拍電影的歲月,我和徐克可能會合作兩部電影,比如一部他監制我導演,另一部我監制他來導。
評委訪談
《綜藝》:陸川導演,作為青年導演的代表,你認為市場應該給予青年導演怎樣的成長空間?作為“天壇獎”評委,你的選片標準是什么?
陸川:這幾年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令全球矚目,年輕導演有了更多拍電影的機會,比我當年出道時機會更多。但我比較幸運的是,以前我的制片人基本上都給了我自由創作的機會。不過現在很難,市場對年輕導演越來越嚴酷。前兩年,大家還會談談《鋼的琴》這一類型的藝術化電影,但現在幾乎都在談票房。電影美學、人文關懷、藝術性等都不看了,只有票房,只有數字。我曾和寧浩聊起,似乎現在年輕導演不拿一億票房都不好意思出來見人。所以,希望能給青年導演更多空間。
說到評片標準,我比較看重影片的電影技巧,不希望電影拍得像電視劇一樣。
《綜藝》:寧浩導演,你拍了不少口碑票房俱佳的喜劇。你認為中國喜劇片和國外喜劇片相比有什么優勢?
寧浩:客觀來說,中國喜劇電影沒有優勢,但我們的市場有優勢。我們可以先有一個好市場,然后有更多高端人才投入電影事業,優勢估計會在后面。中國電影門檻不高,外國人不是看不懂,只是因為有文化隔閡,主觀上他不愿意看。但中國人這一百多年來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和西式生活習慣的影響,接受他們比較容易。所以,中國電影需要有一段漫長的積累文化自信的過程,我們可以先獨善其身,再談文化輸出。
《綜藝》:古欣娜塔女士,此次來中國擔任“天壇獎”評委,感受如何?
瑪莉亞·嘉西亞·古欣娜塔:我很喜歡電影節,因為有機會看到很多電影,可以發現一些年輕的電影人,還可以看到一些在我自己國家看不到的電影。而且,參加電影節也能找到些商機,可以找到一些合作伙伴,做一些合拍項目。我非常希望和中國的電影人合作,已經接拍了一部中意兩國聯合制作的電影,是和中國演員黃海波、王麗坤合作的。這部片子的后期制作剛剛完成,拍完時我喜極而泣,更堅定要繼續與中國合作。這期間,我還學會了做中國菜。
《綜藝》:戈麥斯先生,你如何評價中國電影及中國電影市場?
安德魯斯·文森特·戈麥斯:我不太熟悉中國電影,是第一次來到中國。對我而言,印象深刻的華語片仍停留在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三大電影節入圍電影的范圍,比如《霸王別姬》。但我注意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導演在電影中植入中國元素,不少西方電影甚至加入“中國話的對白”。但是,在西班牙公映的中國電影比較少,我只能通過戛納電影節等了解中國電影,非常期待與中國的導演進行交流探討。
《綜藝》:希拉尼先生,你認為中國電影走向國際市場需要克服哪些困難?可否分享一些“寶萊塢”這方面的經驗?
拉庫馬·希拉尼:我認為主要還是語言問題。因為寶萊塢的制作很多是和英美掛鉤的,有很多印度人分布在英美國家,再加上寶萊塢的市場營銷做得也不錯,所以目前成績比華語片好一些。現在電影市場正受到全球化影響,我相信未來中國和國際互相借鑒、交流的形式一定會越來越多。我非常喜歡中國電影,中國的電影市場很廣闊,我這次離開中國時要帶25部中國最值得看的電影回去細細品味。
《綜藝》:彌勒先生,你如何看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前景?
費利普·彌勒:中國吸引了很多國家的電影人,大家都相信三五年之內,中國市場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影市場。所以,非常多的制片人都在琢磨如何做中國電影,如何加入中國元素。但我認為要拍中國電影,必須來中國,否則無法展現真實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