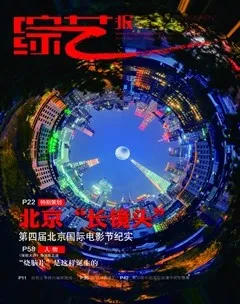“燒腦片”是這樣誕生的


徐崢主演的電影《催眠大師》于4月29日在全國上映,至5月8日上映9天票房收入1.63億元。影片由中國臺灣導演陳正道執導,其上一部影片《101次求婚》票房過2億元,讓市場見識到他的商業潛力。
類型的突破
《催眠大師》是一部怎樣的電影?
徐崢說:“這是一部非常酷的電影,看劇本就讓人欲罷不能。”
莫文蔚說:“劇情懸念性很強,看了開頭絕對不會想到結尾。”
《催眠大師》講的是徐崢扮演的心理治療師徐瑞寧,擅長催眠術,驕傲自大。一天出現了一個神秘病人——莫文蔚扮演的任小妍,她告訴徐瑞寧,自己可以看到已經死去的人。徐瑞寧在治療過程中發現任小妍來治療別有目的……
有影評認為,《催眠大師》是國內少有的高智商影片,開創了國產電影的新類型。
《催眠大師》是一部懸疑推理片,劇本寫了兩到三年時間,具體是7稿還是9稿,陳正道說自己也記不清了。
《101次求婚》還沒上映時,陳正道就想拍一個心理醫生和精神病患者的故事。為此,他去香港跟一位很有名的催眠師聊天。催眠師介紹的情況令他著迷,隨后劇本方向調整為以催眠為主題。
陳正道對催眠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有人認為催眠是心理學,有人認為是一種表演,還有人認為是幻術。《催眠大師》借由醫學上催眠療法的概念,構建了一個新世界。《催眠大師》中的催眠術落足于“一個人內心有死結,怎么想都想不通,要靠外人給一些暗示,幫忙解開心結”。“一個人不管多聰明,也只能有自己一方的觀點,多一個人可以多個不一樣的角度。”陳正道如此理解催眠術。
戲中的催眠有三層,各種人物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催眠連環套”,結構上有點像《盜夢空間》。陳正道和徐崢聊劇本時,需要畫圖才能把故事講清楚。
美術細節也處處呼應著電影中催眠一層套一層的概念。心理研究所的每一塊地板,墻上的每一幅畫,桌上的每一個道具,都有深意。每一個東西都有更里層:畫框里面有圖案,圖案里面有格子,格子里面有人。地板也是一圈又一圈,每個地板里面還有小紋路。甚至徐崢的袖扣,也是照著波普藝術設計的……
影片中的催眠用了兩種方式:恍惚催眠和清醒催眠。恍惚狀態下人沒有意識,做的事情在醒來后會忘記;清醒催眠則是長期暗示,在日常生活中被催眠。陳正道舉例,經常在電影中看到的——心理醫生說“閉上眼睛,你現在覺得很舒服,前方有一個海灘,你開始跑,覺得很開心……”這種催眠是恍惚催眠。《催眠大師》中出現的廢墟、墳場、湖上的小橋都是恍惚催眠后出現的幻想。而清醒催眠是,比如一個人想減肥,醫生長期暗示說,當你打開冰箱時,肚子就會痛,雖然人是清醒的,但只要一打開冰箱就會覺得肚子痛。《催眠大師》中真正關鍵的劇情不是恍惚催眠,而是清醒催眠。
說服徐崢擔綱監制
《催眠大師》主要的戲份圍繞徐崢和莫文蔚展開。
陳正道初次接觸徐崢,正是后者《泰囧》票房狂飆之時。制片人把劇本送過去,陳沒抱太大希望徐崢會接演。確定演出前,兩人只見了一次面。“他第一次跟我聊劇本,我就覺得他好像要演,因為他問的都是為什么這個人物是這樣,我要怎么詮釋或者你覺得他應該是怎樣的。” 陳正道說,正式開拍后的一次閑聊中,徐崢才告訴他,接受邀約的原因是“劇本很好”。
徐崢對這部電影的信心隨著拍攝進行越來越飽滿。最初請邀演時,制片方就曾提出請徐崢兼任監制,他當時以“專心當演員”回絕了,“拍到一半時他覺得可以試試,看完初剪他就說這個我來監制。” 陳正道說。
徐崢對影片提了很多建議,比如電影中徐瑞寧最后跟任小妍說:“你一直覺得你自己看得到死去的人,是因為你太想念你的未婚夫,人死了就是死了,沒有別的可能了。”這段對白在劇本中是以心理學的方式寫的,很難懂。拍攝當天,徐崢提早一個小時到場,他覺得這段臺詞怎么讀都不順。他把陳正道、莫文蔚和另一位編劇叫到一起,四人重新順了遍臺詞。那段臺詞是徐崢重寫的,陳正道在鏡頭外聽完那段對話,感動得快要掉眼淚。“這段戲這樣改真好,我一點不關心為什么要改我的戲,惟一的感覺是我的戲被改得更好了。”
影片最后,莫文蔚唱歌的戲,陳正道在剪輯時也紅了眼眶。這讓他相信這部看上去更受男性觀眾喜歡的推理電影,也能打動女性觀眾。莫文蔚在《墮落天使》里的“瘋”讓陳正道印象深刻,《催眠大師》中,任小妍是一個瘋狂的角色,陳正道寫劇本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莫文蔚。
戲里瘋狂,戲外的拍攝卻非常冷靜。有一天拍到一半休息,徐崢突然對陳正道說:“這戲拍得挺寂寞。”在徐崢的微信朋友圈里,陳正道看到徐崢跟黃渤、寧浩喝啤酒、吃火鍋、唱歌……“原來他平常拍電影是這么開心的,但我們是用很‘冷’的方式把片子拍完的。”
再見,“小清新”
《101次求婚》上映后,陳正道一下子收到了五六十個愛情片的劇本,但他一心想轉換“跑道”,在萬達的幫助下,他“改道”成功,拍攝了《催眠大師》這樣一個類型獨特的影片。該片能當選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閉幕片,“跟類型上的創新有很大關系。” 陳正道說。
“《催眠大師》之后,大家就不會再說臺灣來的導演這次又拍什么小清新電影了,誰又愛上誰了之類的。”陳正道說,“男孩子,人生中不只有愛情,心里還是有一個蝙蝠俠的夢、星球大戰的夢……”
這次“轉型”并非“硬著陸”,其實陳正道23歲時拍的處女作《宅變》就是驚悚片,該片當時在臺灣票房不錯,但口碑不行。現今33歲的陳正道拍《催眠大師》可謂重拾舊愛,“我愛這個類型愛了十年了,也許中間‘變心’拍了幾個愛情片,但這個才是我真正喜歡的東西。”
《催眠大師》的特效以討巧為主,沒有像《盜夢空間》中城市折疊那樣的大動作,更多的像“影像戲法”的特效。比如,莫文蔚在第一次進入催眠世界后,在房間撿起懷表,背后突然出現了別的空間。觀眾看到這一幕或許會以為是用特效做成的,但其實是實景拍攝——拍法非常折騰人,道具組把背景房間一部分的景拉到廢墟景上重新搭建,然后把外墻挖開,打回原來室內的光。打光很復雜,拍攝難度更大。
因為《盛夏光年》,陳正道曾被貼上“小清新”標簽,在他看來自己其實從沒有拍過“小清新”,“我一直都偏好比較重的情感。”《盛夏光年》講的是身體的成長,在香港和日本都是禁止未成年人觀看的。《催眠大師》中,陳正道借催眠概念講了一個復雜的故事,想表達的是 “無論犯了什么錯,哪里做得不好,自己找到一個方法治療自己、原諒自己最重要。”
今年下半年,陳正道計劃拍一部青春奇幻片,講述一個老奶奶重返24歲的故事,而明年,計劃推出“大師系列”的第二部《記憶大師》。《記憶大師》在規劃中是一個科幻推理片,“是一個比《催眠大師》再大一點的夢”。“如果觀眾接納了《催眠大師》,從而開啟中國電影更多類型的可能,我會努力寫一個更精致更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