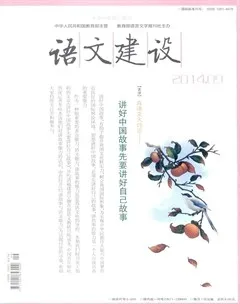語文教學的“舌尖滋味”
一部《舌尖上的中國》,展現了具有民族烹飪底蘊的“味”之精妙。烹飪大師與“味”相交,“悉味”“玩味”,對“味境”苦心孤詣的追求,似乎與我們在教學中對語文“味”的追求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言烹飪大師造美味之道,絕非心血來潮,一蹴而就,僅其“施烹”肇始之前那止于“躁動”的“力度”及“心境”而言,也絕非尋常人所能具備,需秉“心”養“術”。語文課的味醇之道,也在于教師苦心孤詣的“課外”修煉。如我在臺灣聽張輝誠老師的《國文課——孟子思想核心》,就為其孜孜不倦的修煉經歷所嘆服。他之所以把國學講得深入淺出,鞭辟入里,在于其對自己嚴格的“十八般武藝”的要求,在于其永不懈怠的學養追求,在于其身體力行傳承著國學文化精神。張老師在課堂上傳遞孔孟思想中“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學以致用”的部分,把“生命自覺”的意識啟蒙不著痕跡地滲透于經典的講授中,以他獨有的幽默方式講活了經典,巧妙地讓國學的精神與智慧,振撥年輕的生命,啟發懵瞳的心靈,如大易之道,生生不息……正是他課外之深厚功力,才烹出了國學至美至醇之味。
有言烹飪大師對“味”的演繹,必須對“味”做出“主題烹飪個性特色”的特殊考量。個性化“味”的演繹,在于烹飪高手能否依據食材特性因勢利導,通過多元組合來使食材“保性守真”,把味演繹得圓滿理想。“味之甘美”完全憑著烹飪者深厚的積淀與靈活高超、隨機應變的“和味”功夫。我從曹國慶執教的《紅狐》一課中,體會到了課堂上的“和味”之妙。教和學完全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教師憑著充分的備課,在課堂教學中相時相機而動,針對學生現拋出來的疑問,汲取、選擇需要的信息,不斷重組自己導學發展的思維軌線。當然,這一思維軌線是以語言文字的學習與運用為主干的。例如,教師拋出三個看似簡單的“咬文嚼字”問題:為什么是“叨”而不是“偷”,為什么是“懷念”而不是“故事”,“懷念”這兩個字是否多余,引導學生最終實現的卻是“突破語言的表層意義,抵達語言的深度思維”的文本核心價值。教師本著“語文教學的一切問題,都應該用語言的方式去解決”的態度,從語文視角出發,立足文本語言,開展語文教學。設問、討論、讀寫活動緊扣文本,貫穿著對學生概括、理解、分析、鑒賞能力的指導,學生隨著教師的指導,穿越文本語言,品悟作者情意,情感與素養在師生語言交鋒中得以自然提升,充分體現了語文至真至切之味。
有言中國味道很一般又特別不一般。語文“家常課”亦如此。如果說語文課是三年而順,五年而聰,八年而美,十年而莊,十五年而強,二十年而醇,二十五年而厚,三十年則應為“淡”了。從黃厚江老師執教《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這一課中,我悟到了語文課的真味——淡。教學開篇,教師只是讓三個學生上黑板默寫,寫完后讀,讀完后糾錯、正音、釋義,期間有教師對默寫后板書的評點:對寫字書法的要求、布局的要求、標點的要求、如何釋義的要求、重點字正確讀音的要求。聽來似乎寡淡得很,但我體會到了“詩書滋味長”,師生對話中的點點滴滴都滲透著教師對學生語文素養的關注和培養。教學始終在師生談笑打趣中進行,師生始終在用聊的方式探討問題,似乎很隨意,沒有章法,但對話是“以活激活”,共生智慧。在教學中,教師有幾個看似散淡的提問其實步步匠心,閑聊中暗藏的教學思路是清晰的,即整體把握一具體揣摩一品味鑒賞一掌握讀詩的方法規律。整堂課教師總是力圖用語文的方法去教語文,以語言為核心,以語文活動為載體,以提高語文素養為根本追求,重積累、重過程,用一種樸實的心態和實用的態度建設課堂。這樣的“淡”是寡淡中的深刻扎實,閑淡中的言近意遠,散淡中的疏朗開闊,平淡中的不凡境界。這正如烹飪大師能將大味若淡與拙中見巧相融無悖,做出返璞歸真的通常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