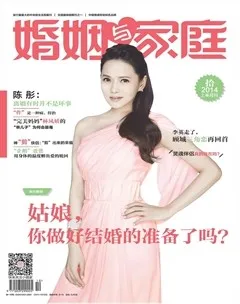張云逸家訓:記住你是普通人
已經退休的張光東少將,如今和夫人曹莉冬住在北京一個普通又陳舊的大雜院里,里面一共4戶人家。而張光東的家,除了客廳里一整面墻的書,在很多人看來甚是“寒酸”。
這位曾任石家莊陸軍指揮學院副院長、官至少將的老人卻說:“我就是一個普通人,住在這里我覺得舒服又自然。”他說,幾十年前曾照顧父親的阿姨,如今也住在這里。張光東說,一是因為父親向來就把警衛員、廚師和保姆都當成自己家人一樣平等相待,早年就住在一起;二是因為父親交代過,要幫忙照顧曾經陪伴照顧過他的工作人員。
無論是居所環境,還是言談舉止,你都無法把張光東當成特殊的“紅二代”,對此,他的解釋是:“因為父親一直是個普通人,我打記事起就沒覺得自己有什么特殊。”因為戰爭,張云逸和妻子長期分居兩地,直到54歲時,他才有了二兒子張光東(兩個兒子相差20歲)。
盡管老年得子,張云逸卻從不寵溺張光東。兒子從小學到高中,履歷表“社會關系”一欄,“父親”都是空著的。剛開始張光東沒在意,后來覺得詫異,他才問父親:“其他同學都寫父親的名字,您為啥不讓我寫?老師問我父親去哪兒了,我要怎么說?”張云逸說:“你就說,父親經常不在家,管不了你。”
張光東所在的小學有個豆腐坊,張云逸就讓兒子把沒用的豆腐渣拿回來。后來,家里的飯桌上就多了道白蘿卜拌豆腐渣的菜,一滴油都沒放,特別寡淡無味。張云逸說:“破布可以納鞋底,麥麩能喂豬,豆腐渣能做菜。我們都是普通人,一定要勤儉節約。”張光東說,在餐廳的墻上,貼著父親用毛筆字寫的“有時需作無時想,莫待無時想有時”的名句。
張光東小學畢業后考上了北京四中,那時很流行學俄語,所有干部子弟的孩子都被分在了俄語班。但“父親”一欄總是空著的張光東,卻被分在了英語班。“當時英語課剛開,連個老師都沒有。”張光東對父親抱怨,父親告訴他:“那些百姓家的孩子不都在英語班嗎?記住你是普通人!記住,和普通人在一起的生活是最有意義的!”張光東沒再要求分到俄語班。英語課空了幾個月后,有個在英國待過多年的海歸成了他們的英語老師。老師的英語說得非常地道,思想也非常先進。張光東很慶幸自己選擇了英語。
張光東說:“當我漸漸長大懂事后,開始覺得‘普通人’的身份讓我更快樂和自由。這讓我一生都受益匪淺。”
當張光東接到哈爾濱軍工大學錄取的通知書時,父親張云逸非常高興。隨“錄取通知書”下來的,還有一套軍人的行裝。張光東的母親發現行裝里沒有枕頭,于是就做了個枕頭,準備給兒子帶上。張云逸卻把枕頭拿掉了,用一張包袱皮(白粗布)把張光東的衣服包在里面,然后說:“軍人都是用這個當枕頭的。”
張云逸有專車,但是張光東從來都不能坐。母親送他去車站,也是來回坐公汽。他大學畢業后,只要說出父親是誰,完全可以分到北京,但張云逸卻不讓兒子這么做。后來張光東被分到四川什邡的大山里,而領導幾乎都是父親曾經的手下。但他知道自己是普通人,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父親是張云逸。
也許有人認為,張云逸對兒子太嚴苛了。但張光東卻說,父親對他的愛無處不在。整個學生時代,父親每次都會親自給他包書。用牛皮信封做書皮,然后再用繁體毛筆字,在封皮上寫上科目、班級和姓名。書皮內頁,張云逸會給兒子寫一句鼓勵的話。張光東還說,父親對他的關愛,還體現在他上大學后,父親給他寫的一封信里,告訴他,野營時容易把被子踢散,所以要用背包帶把被子的一頭系死,這樣睡著才暖和;每次從外地回到家,父親都催促母親,趕緊給兒子燒他最愛吃的魚……
1973年,病重的張云逸問張光東:“你什么時候能回來?”張光東和妻子才從四川調回北京陪伴、照顧父親。一年后,張云逸離世。張光東說,從1965年離開北京上大學,到1974年回到北京,在父親生命中的最后10年時光,他陪在身旁的時間卻不足一年。“我這一生最大的遺憾,是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了。但父親臨終前卻說,他一點都不遺憾,因為我越是不在他身旁,就越能做個普通人!”當張光東這樣說時,你能從這個“普通人”身上看到非同一般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