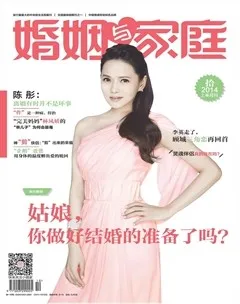用涂鴉打開孩子關閉的心門
她像嬰兒一樣滿地亂爬
跟著媽媽走進咨詢室后,10歲的菲菲一直沉默不語。為了引起她的興趣,我遞給她一盒彩筆。菲菲沒接住,彩筆散落在地上。接著,令人驚詫的一幕發生了:菲菲突然趴在地上,像個嬰兒似的,滿地亂爬地撿水彩筆。看著女兒這樣,菲菲媽瞬間崩潰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都怪我,都是我的錯!”
我讓助手陪菲菲玩水彩筆,自己則帶著媽媽走進另一間咨詢室。她斷斷續續地講述了女兒的經歷:菲菲是個留守兒童,父母都在北京打工。去年暑假,菲菲同12歲的表哥一起來北京探親。剛進入青春期的表哥,借著“玩游戲”的名義,偷偷侵犯了菲菲。
“回到老家后,原本名列前茅的她,成績下滑得厲害,也不愛搭理人。快開學時,我陪妹妹到醫院做子宮肌瘤手術,菲菲忽然抱著我說:‘媽媽,你帶我也檢查一下吧,我怕肚子里有寶寶。’我嚇壞了,才知道發生了這種事!從醫院回來后,菲菲拒絕上學,而且行為變得很怪異。每天鉆到床底下睡覺,說那樣安全。我經常晚上陪她在床底下睡,給她唱兒歌。一不順心,她就會跟動物似的,滿地亂爬……”
我理解了菲菲在咨詢室里幼稚的行為。這是一種退行,是一個人遇到重大創傷時的本能自我保護。因為菲菲不肯說話,我決定用涂鴉的方法,和菲菲交流。
媽媽“縮小”,爸爸“沒了”
接下來的日子,菲菲每隔兩天就來咨詢室里畫畫,我們的關系越來越親密,雖然彼此的言語交流很少。
一次,我們采用“交互繪畫”的方式,在同一張紙上輪流畫一部分,直到完成整幅繪畫。畫的主題是“我的家庭”,它可以展現孩子心中的家庭關系。我只畫家具,人物部分都留給孩子。
“我的床單是黃色的。”菲菲提醒我。“是檸檬黃嗎?”我問。菲菲點頭。在繪畫的過程中,她和我的對話越來越多。
我畫完床,菲菲接著畫人。菲菲把媽媽畫得像指甲那么小,卻把自己畫得像拳頭那么大。我注意到這個細節,問:“這是媽媽嗎,怎么這么小?” 菲菲不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又給媽媽的衣服涂上難看的顏色。這是一種心理投射:發生創傷事件后,孩子對父母的信任感降低,所以媽媽的形象“縮小”了。而難看的顏色,代表她對媽媽的憤怒。
“這個家看起來真好!可是,爸爸在哪兒呢?”我發現孩子沒有畫爸爸。菲菲果然被觸動了,黯然說:“蘭老師,我好怕爸爸和媽媽吵架。我做了一件錯事,他們總因為我的事情吵架……我是個壞孩子……他們是不是要離婚了?”她無聲地流下了眼淚,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菲菲哭泣。
第二天,菲菲的父母來見我,我和他們談了菲菲的感受。了解到原來事情發生后,菲菲的父母都非常痛苦,他們互相埋怨對方,天天吵架。吵到后來,菲菲爸爸干脆搬到工廠里住。而他們的爭吵讓菲菲更加恐懼和自責,認定自己是個壞孩子。
通過認知疏導,我幫助菲菲的父母修正想法,讓他們把整件事情歸結為“意外”,沒有人愿意看見這件事發生,也不需要為這件事負責。我給他們看了菲菲的畫,轉達了孩子的擔憂和恐懼,并告訴他們,現在給孩子一個安穩的環境才是最重要的。當晚,菲菲爸爸就搬回了家。自從爸爸和媽媽不再爭吵后,菲菲“爬行”的頻率大大減少,但仍然躲在床底下睡覺。
經過8次咨詢后,菲菲第一次用語言表達了她的感受:“蘭老師,我好害怕!一想起那件事,我就怕得渾身發抖!”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問題進入意識層面就解決一半了,我們可以就創傷進行對話。
要想撫平創傷,就不能回避那段經歷。因為,回避不等于遺忘,那些經歷仍然會閃回到她的腦中,一次次地侵害她的生活。只有在記憶中重現創傷的經歷,并且尋求到安慰自己的方式,才能夠擺脫創傷對她的控制。
“老師有個不讓你害怕的方法,要不要試試呢?”菲菲猶豫了一下,點了點頭。
接著,我和菲菲運用繪畫還原了事件發生時的場景。然后,我讓菲菲靠在沙發上,閉起眼睛回憶當時的感受。
“在你的眼前,有一臺電視,正在播放那天的情景。你感受到什么?”
“我……好害怕……”菲菲顫抖地說。
“你聽到什么?”
菲菲一下子睜開眼睛,攥住我的手說:“表哥說,要是我不同意,就把這件事告訴媽媽……他,他還狠狠地掐我!”菲菲的眼中充滿了恐懼。
“你看,你做這件事,是因為被表哥威脅的!你是個好女孩,沒有必要為此自責!”聽了這句話,菲菲的身體慢慢放松了,放下了一大半的心理包袱。有時候,只有孩子愿意聽時,你的話才能走到他們的心里。菲菲聽父母說過太多次“不是你的錯”,但卻始終不敢相信。直到自己在記憶中搜尋到了“證據”,她才終于確信了這一點。隨后,菲菲記起了很多細節:當時的天氣,他們穿的衣服,表哥說的話,事后如何威脅自己……把這些細節說出來,它們就不會再在菲菲的記憶中繼續傷害她。這次咨詢后,菲菲不再恐懼黑暗,開始練習獨自睡覺。
然而,我們只是解決了她最表層的恐懼—就像被狗咬了一口后,她最初怕的是被咬的痛;當表層恐懼解決后,深層恐懼凸顯出來—她怕所有的“狗”,開始恐懼異性,恐懼婚姻。
在新娘旁邊,畫一個新郎
咨詢半年后,已經復學的菲菲突然畫了這樣一幅畫:一個穿著漂亮婚紗的女孩站在最前面,幾個小人散落在新娘背后。我指著新娘身旁的大片空白,問:“新娘真漂亮!可是,為什么沒有畫新郎呢?”
菲菲堅定地回答:“沒有新郎,也不會有婚禮。”
菲菲媽媽告訴我,女兒在學校的表現很好,但是不肯和男孩接觸。只要老師給她安排男生同桌,她就不肯上學,還揚言自己“一輩子都不結婚”。
顯然,菲菲對異性和婚姻的恐懼,是源于自我保護,以防自己再度受傷。我決定從她最熟悉的男同學入手,消除她對異性的恐懼。我請菲菲畫他們的班級,她非常認真地畫了6個小人,拉著手一起做游戲。小人是簡筆畫,看不出性別。我問:“你們班有多少個同學?”“36個。”菲菲說。
“那咱們把他們全都畫在圖上,女生畫長發,男孩畫平頭,好嗎?”我有意識地引導菲菲改寫她的“圖畫”。菲菲拿著筆,又加了30個簡筆小人,并且為每個小人畫了頭發。然后,我和菲菲為每一個小人涂色,涂一個小人,我就請她講講這個同學的事。講到女生時,菲菲說得很流暢;講到男生時,她顯得很遲疑。剛開始,她指著幾個男生,說他們“粗魯、可惡、霸道、調皮”,都是負面詞。慢慢的,她指著一個臉上有雀斑的小人說:“這是李勇,他拿著班級的鑰匙,從沒遲到過。”我點點頭:“哦,這么說,李勇很有責任感啊!”“嗯,是吧!”接著,菲菲又指著一個高個子小人說:“這是小華,他曾經背著中暑的女生去醫務室,累得夠嗆!”“這樣啊,小華真有愛心!”我用這種方式,幫助修正菲菲對男生的認知,強化對男生的好感。陸續說出幾個男生的優點后,菲菲若有所思地說:“咦,蘭老師,好像不是所有男生都喜歡欺負女生!”我欣慰地點頭:“是呀!女生中有好女生和壞女生,男生中也有好男生和壞男生。你可以先認真地觀察他們,然后再和好女生、好男生做朋友!”
“嗯,那我試試看吧!”菲菲又看了一眼自己畫的畫,對著36個拉著手的小人,害羞地笑了。
兩個月后,菲菲媽媽打來電話:“孩子已經敢和男生交往了,而且她很受同學歡迎,打算在下學期競選班干部!”
“菲菲還畫畫嗎?”我問。
“嗯!她可喜歡畫畫了!對了,前兩天,她在那個‘新娘’旁邊,畫了一個‘新郎’,還挺帥的!”菲菲媽激動地說。
在咨詢8個月后,菲菲受創的心終于修復了。
給家長的建議:
1.營造一個溫暖、安全的環境,是父母給孩子最有力的支持。建議父母盡量把孩子當成正常的孩子看待,這樣能減少她的情緒波動,加速恢復的周期。當孩子情緒波動大時,爸爸和媽媽要一再對她做出有力的保證:“孩子,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再發生!爸爸媽媽保證!”另外,父母不要當孩子的面爭吵,多陪伴孩子。菲菲媽鉆到床底下陪女兒睡覺的做法就很好。
2.放下內疚,不要無限度補償孩子。經歷過創傷的孩子,總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經常用物質來填補自己的擔心。過度彌補會讓孩子心中的黑洞越來越大,父母也會承受不必要的經濟壓力。關鍵是要讓孩子意識到,她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在咨詢初期,菲菲把過去10年里渴望而沒得到的東西,通通買了個遍,800多元的名牌文具買了兩套。因為內疚,菲菲父母對女兒的愿望全部滿足。
當菲菲又讓媽媽給她買一套72色的畫筆時,我問菲菲:“想象一下,有了最漂亮的畫筆,你有多開心?”菲菲回答說:“我不知道,可我就是想要!”我讓菲菲把自己渴望的東西都畫出來。然后,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擁有了它,要怎么使用,她的生活會發生什么改變?這種繪畫的樂趣,分散了她一部分欲望。“畫餅充饑”的方法對孩子非常有效,比起直接擁有物品,孩子更喜歡別人能夠理解他們的渴望。利用孩子的想象空間,就可以完成很多現實中不曾實現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