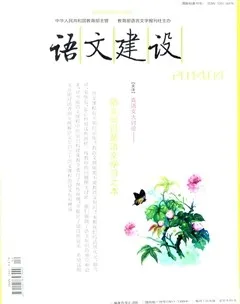教給學生新的言語方式
課程知識既來自課程標準的統一規定,也來自師生在具體教學過程中的創造性生成。正如美國著名課程論專家拉爾夫·泰勒在《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中指出的:“設計學習經驗(此處可視為與課程內容同義)的過程,并不是用一種機械的方法為每一個特定目標制定明確規定的學習經驗。相反,它是一種比較富有創造性的過程。”[1]
語文課程知識,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十分寬泛的概念;“言語—思維”方式,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能夠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創生豐富意義和價值。其實,語文教學前輩早就注意到了從范文中教給學生新的言語方式。例如,何仲英先生于1920年在《教育雜志》第十二期第二號上發表過一篇題為《白話文教授問題》的論文[2],其中有一段文字生動地講述了他是如何講授《武松打虎》這段選文的。他寫道:
從“武松在路上行上幾日”起,到“一步步捱下崗子來”,分段寫,用新式句讀,然后考查《水滸傳》的來歷(見商務印書館《小說叢考》),然后研究《水滸傳》的內容(學生有看過的,談起來津津有味),然后詢問字義,“怎地”“恁地”怎么講?“端的好酒”的“端”字何以做“真”字解?“休得胡鳥說”的“鳥”字何以指“男子的生殖器”?不但要明其當然,還要明其所以然,那就不可不研究聲音學了。全篇意思既然明白,段落也早分清楚,然后就要問怎樣吃下十八碗酒?怎樣拿哨棒做個線索?是組織上應該研究的;然后再問“原來那大蟲拿人……”“原來打急了……”“原來使盡了氣力……”那幾句話,為什么要用“原來”字眼?又有讀廟門榜文后欲轉身回來一段,風過虎來叫聲“啊呀”翻下青石來一段,被驚出冷汗一段,……皆故作驚人之筆,如何樣描寫傳神?如何樣措詞琢句?是修辭上應當研究的。我研究到這些問題,學生沒有不歡喜推敲,沒有不入神注意,我真敢相信,學生有了這種研究的興趣,將來有少數的人研究古文,定能“勢如破竹”。
這一段文字告訴后人:教師在小說的敘述語言中選取若干節點,從漢字的構形與聲音,漢語詞匯的意義,篇章組織的線索與伏筆,動詞的選用,重復和夸飾辭格等方面,對選文實施多光源聚焦觀照;于是,這一段選文就呈現出了諸多側面和紛繁色彩;學生就以“歡喜推敲”“入神注意”“研究興趣”做出了強烈回應。
這一段教學筆記發表的時間,距離今天已經快一百年了;從范文中教學生學習言語方式作為一個優良傳統,也一直綿延至今。我們這里不妨繼續選用當今語文課教學古典白話小說的課例。例如,教學《林教頭風雪山神廟》,教師把兩課時分解為三個階段[3]:
第一階段學習陳述性鑒賞知識。教師向學生介紹了金圣嘆的小說評點鑒賞方法,主要介紹了“先事而起波”和“事過而作波”兩種推求小說情節內在關聯的方法。金圣嘆認為“夫文章之法,有事先而起波者,有事過而作波者”。所謂“事先而起波”是指事先埋下一筆,先因后果,如小說開頭寫酒生兒李小二夫妻,并不單是寫林沖在牢城營里有一個舊相識,而是“意自在閣子背后聽說話一段絕妙奇文,則不得不先在此作一個地步”。所謂“事過而作波”是指事后補敘原因,先果后因,如寫火燒草料場,先見草料場大火,但起火原因事前并沒有交代,后來通過陸虞候三人在山神廟前的對話補出原因。金圣嘆對情節內在關聯的這兩種推求,均從小說細部描寫入手。因此,鑒賞者也要循此而推求出這些細部的因果關系來。
第二階段學習程序性鑒賞知識。教師讓學生仿照金圣嘆的方法,從小說情節細部入手推求“內在關聯”。教師先讓學生通讀全文,在把握基本情節的基礎上各自尋找鑒賞點,然后把學生找到的鑒賞點歸納為“事先而起波”和“事過而作波”兩大類;再交給學生討論。學生興趣很濃,討論很熱烈。學生的鑒賞點主要集中在小說對“風雪”“火”“刀”“花槍”,以及對陸虞候三人的語言描寫等方面。
第三階段學習策略性知識。這個階段的重點是組織學生反省自己的學習過程,談鑒賞體會。概括起來,學生的主要體會是:通過這種鑒賞方式,明白了文學作品中也存在著因果關系,以后讀小說不能光看大概的故事情節,而要仔細看小說細節背后的因果關系;通過學習這一篇課文,學會了鑒賞小說的方法,以后讀小說也要盡量用這種方法去讀;透過細節和語言描寫,更加了解了林沖的性格發展,明白了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是怎樣被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又如,教學《林黛玉進賈府》[4],教師以“語文教學的根本是學習語言”為宗旨,在學生確認了林黛玉寄人籬下的身份和不得不“步步留心,時時在意”的心態之后,教師提出了“那么,她進入賈府以后該怎樣和賈府的人說話呢”這樣一個總問題,并要求學生勾畫出“林黛玉進賈府后和哪些人說了些什么話”,而后引導學生重點推敲了林黛玉回答大舅母邢夫人和二舅母王夫人的兩處話語,體驗她答話的得體性;還推敲了王熙鳳出場話語的乖巧。最后得出結論:說話得體,要審視不同的場合和對象,要注意說話雙方的身份和地位,要根據不同目的采用不同的說話方式。
與100年前白話語體文剛剛進入語文課程的形勢相比,與當年何仲英前輩執教《武松打虎》相比,當代語文教師已經對教學古典白話小說的課程內容進行了大膽解構和自主重構。這不僅是因為百余年來,諸如語言學、修辭學、文章學、文藝學、教育心理學等這些與語文課程和教學緊密相關的學科理論,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而且,還因為當代越來越多的語文教師已經清醒地意識到,語文新課程的目標與任務急需新鮮的課程和教學內容來支撐。
這種歷史演變和現實狀況,至少告訴我們以下幾點經驗。
早有研究者指出:“學習語言一般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從語言綜合運用的范例學習,一個是從語言分析研究得出的規律學習。”“從語言的綜合運用中學習語言的時候,必然要對許多語言現象,語音的、詞匯的、語法的,加以比較、概括,探索某些規律性的東西,以備模仿、比照、類推來指導語言實踐。”“從語言的綜合運用來學習語言,是一個自然的方法,傳統的方法,現在還普遍采用的方法。”[5]換言之,學習語言,既需要學習范例中運用語言的種種現象(語料),也需要探索這些語料所依據的語言知識規律(語理)。在中小學語文課程教科書中,大量文質兼美的范文就是綜合運用語言的范例,語言知識規律就依附這些范文而存在。因此,如何認識和對待這兩種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方法,歷來是影響語文課程與教學質量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中小學語文課程中,教師在什么時間、教哪些語文規律,應視學生的學情而定。早在1949年,郭繩武先生已在《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草案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指出:“任何一篇文章都包含無數的規律,在教學上,絕不能一下子全面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根據學生的學習規律,逐步地適當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從教學的觀點上看,語文規律是活的,不是死的,它是語文規律與學生的學習規律相結合的產物,它不是單純的說明‘是什么’,解釋‘為什么’,而必須能夠指出‘怎么樣’來,這樣對于學生的語文實踐,才能起指導作用。”[6]換言之,經由范文教學語言知識規律,不能停留在讓學生僅僅認知上,而應重在引導學生模仿和應用。因此,教師既要考慮從小學到中學各個學段不同年級的安排,又要考慮各種規律之間的配合,還要考慮學生認識規律與運用規律的協調,即學習語言過程中“知”與“行”的關系。
在語文課程中教學語言知識規律,既需要隨文學習、及時積累,也需要適時整理,集零為整。有效積累,需要訓練學生養成朗讀、復述、背誦、抄寫、默寫等學習語文的良好習慣。有效整理,是因為隱含于范文的活的語文規律,需要適度的明確化(概念、命題或規則),需要適度的類型化(分類)和系統化(編序)。只有這樣,才能有益于學生自主組建有結構的知識。否則,模糊的、個別的、散漫的知識既不利于學生必要的理解和記憶,也不利于他們有效的模仿和遷移。這種整理,既應是教師教學工作的組成部分,也應成為學生學習活動的必要環節和良好習慣。也就是說,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學會建構自己的知識結構。“因為理解某一事物就是意味著給某一事物在知識、動機、信念、系統中找到位置,意味著了解某一事物在我們活動中或他人的活動中可能發生什么樣的作用。”[7]
參考文獻
[1][美]拉爾夫·泰勒著,施良方等譯.課程與教學的基本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64.
[2]何仲英.白話文教授問題[A].顧黃初,李杏保主編.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44.
[3]陳隆升.推求“小說細部關聯”重組“鑒賞教學內容”——以《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的鑒賞教學為例[J].語文學習,2005(10).
[4]蔣祖慰.語文教學的根本是學習語言——《林黛玉進賈府》教學案例[J].語文建設,2007(7-8).
[5]蔣仲仁.語言規律與語文教學[A].顧黃初,李杏保主編.二十世紀后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453-454.
[6]郭繩武.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草案中的幾個問題[A].顧黃初,李杏保主編.二十世紀前期中國語文教育論集[C].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956-957.
[7][蘇]彼得羅夫斯基主編,朱志賢等譯.普通心理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