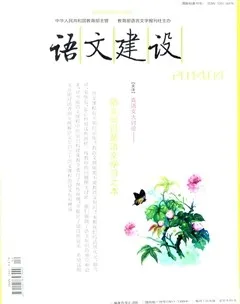也談國(guó)學(xué)進(jìn)課堂
最近讀到幾篇關(guān)于國(guó)學(xué)教育的文章,因?yàn)檫@是熱點(diǎn)問題,遂頗多好奇;可是從讀者角度看,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的討論還需要深入下去。
“國(guó)學(xué)”一詞,古已有之。《周禮·春官宗伯·樂師》言:“樂師掌國(guó)學(xué)之政,以教國(guó)子小舞。”《禮記·學(xué)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shù)有序,國(guó)有學(xué)。”孫詒讓在其所著《周禮正義》中指出:“國(guó)學(xué)者,在國(guó)城中王宮左之小學(xué)也。”由此可見,“國(guó)學(xué)”在中國(guó)古代,指的是國(guó)家一級(jí)的學(xué)校,與漢代的“太學(xué)”相當(dāng)。20世紀(jì)初,西風(fēng)東漸時(shí)期,與西學(xué)(即西方文化、經(jīng)濟(jì)、科學(xué)、政治、思想等總稱)相對(duì),提出“國(guó)學(xué)”,側(cè)重在兩者的差異性,以文化和思想為主要比較方面。中國(guó)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在文化發(fā)育中已經(jīng)形成被廣泛認(rèn)可的價(jià)值體系,當(dāng)西方文化思想潮流來襲時(shí),勢(shì)必引發(fā)與本土文化的沖突。國(guó)學(xué),這個(gè)時(shí)候自然成為一批本土意識(shí)非常強(qiáng)烈的文化人樹立起來的旗幟。
我們也知道,與梁?jiǎn)⒊㈥惇?dú)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一批新文化名人并峙的還有一個(gè)名人群,如章太炎、陳寅恪、梁漱溟等。有意思的是,這個(gè)時(shí)期的文化名人,有不少都秉持國(guó)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他們之間的文化論爭(zhēng)或許非常激烈,可是在文化養(yǎng)成上,他們大多不排斥中西兼修。
文化之變多與社會(huì)形態(tài)之變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新中國(guó)成立,宣告與封建文化決裂;20世紀(jì)80年代執(zhí)行改革開放政策,推進(jìn)了中國(guó)社會(huì)的工業(yè)化進(jìn)程,我國(guó)從農(nóng)業(yè)主體人口社會(huì)演變?yōu)楣I(yè)人口和城市人口占多數(shù)的社會(huì),這也勢(shì)必重新構(gòu)建所謂現(xiàn)代新文化。在整個(gè)歷史長(zhǎng)河中,這一段社會(huì)巨變的時(shí)間并不是很長(zhǎng),文化修復(fù)和整合的時(shí)間比較短促,而且當(dāng)下很多人正在經(jīng)歷這場(chǎng)文化的撕裂,普遍對(duì)文化生活不適應(yīng)。于是國(guó)學(xué)熱潮風(fēng)生水起。
國(guó)學(xué)教育產(chǎn)生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與西學(xué)的抗?fàn)幹校瑖?guó)學(xué)被當(dāng)作社會(huì)改造的一個(gè)抓手。在這場(chǎng)論爭(zhēng)中,我們需要明確這樣幾個(gè)結(jié)論:
其一,社會(huì)的發(fā)展與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尤其是全球化的高度融合,客觀上決定了傳統(tǒng)意義的國(guó)學(xué)已經(jīng)不可能成為未來中國(guó)社會(huì)的主流文化和主導(dǎo)文化。文化的變革與融合是趨勢(shì)。
其二,西學(xué)永遠(yuǎn)不可能湮沒中國(guó)文化,因此以西學(xué)移植來改造中國(guó)社會(huì)這條路子也走不通。我們的思維、思想具有中國(guó)特色,這決定了中國(guó)文化一定是循著一條脈絡(luò)發(fā)展的。就如西方文化發(fā)展到今天,無論說它怎么現(xiàn)代、魔幻、荒誕,可我們還是能夠從古希臘文化那里找到它形成的基因。
其三,傳承國(guó)學(xué)的人越來越少了,現(xiàn)在的所謂國(guó)學(xué)大師,或許可以專修國(guó)學(xué)的某一點(diǎn),不可能與當(dāng)前國(guó)學(xué)潮流中我們所賦予國(guó)學(xué)的宏大所般配。以國(guó)學(xué)大師為文化旗號(hào)聚集大眾,成為他們的信徒,這有些荒謬。
其四,國(guó)學(xué)在思想上有一定的駁雜性,如諸子百家,很多都是有沖突的。我們學(xué)習(xí)國(guó)學(xué)思想,怎樣兼容這些不同的東西,也是一個(gè)問題。在封建時(shí)代,統(tǒng)治階級(jí)解決這個(gè)問題,采取的是獨(dú)尊儒術(shù)。今天的國(guó)學(xué)教育中,我們應(yīng)該怎么辦?是否要考慮選擇性?
其五,國(guó)學(xué)有一批文化典籍,目前倡導(dǎo)國(guó)學(xué)的人,采取的基本方法是注疏或宣講這些典籍。謀求貼近典籍本義的努力,或者照搬照抄、死記硬背,這樣的路數(shù)并不適合今天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而一些文化學(xué)者,希望在今天的語境里賦予國(guó)學(xué)典籍以新解,這樣的路數(shù)也被批評(píng),因?yàn)樾陆庖呀?jīng)不是國(guó)學(xué)了。我們學(xué)習(xí)國(guó)學(xué),應(yīng)該走一條什么路子?這是值得思考的。
我是語文老師。出于職業(yè)角色需要,有意識(shí)接觸了一批我國(guó)古代文化典籍,就我的知識(shí)儲(chǔ)備來說,這樣的閱讀實(shí)踐是比較艱難的。據(jù)此來看,在我國(guó)大眾中推及古典閱讀,在我國(guó)中小學(xué)普及國(guó)學(xué)教育,用這樣粗疏的食古不化的辦法主導(dǎo)學(xué)習(xí),必將更難。基礎(chǔ)教育是大眾化普及教育,若國(guó)學(xué)教育納入學(xué)校課程體系,自然需要有識(shí)之士做幾件事:
第一,從國(guó)學(xué)的若干考察維度和領(lǐng)域上,做出閱讀的精選,明確到底要讀什么,哪些可以打下文化底子和思想修養(yǎng)底子。思維要開闊一些,要多維度選擇,不要局限在某些被歷史教育窄化、固化的東西上。過去是儒家第一,以為國(guó)學(xué)就是儒學(xué),這顯然是狹隘的文化視野。國(guó)學(xué)是雜學(xué),存在多種思想的沖突,要把這些原生的東西呈現(xiàn)出來。由此奠定的文化新人,一定要區(qū)別于封建社會(huì)里服務(wù)封建文化統(tǒng)治的儒生。
第二,要在傳承的同時(shí),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識(shí),或文化自覺。中國(guó)文化是多民族在不同時(shí)代,經(jīng)過多次劇烈碰撞融合發(fā)展而來的。國(guó)學(xué)不是一時(shí)的文化,也不是一世的文化、一朝的文化、一族的文化。因此,它不可避免帶有時(shí)代的局限性,力求解決的是特定時(shí)代人們的生活需求和精神危機(jī)問題。目前什么人做什么事,都打著國(guó)粹的旗號(hào),這是需要警惕的。
第三,對(duì)于普及性的中小學(xué)國(guó)學(xué)教育,一定要用學(xué)生喜聞樂見的方式,結(jié)合現(xiàn)代生活問題的解決,闡釋古人的智慧。也就是說,在中小學(xué)教育中的國(guó)學(xué),一定不能走學(xué)術(shù)的高精尖的路子。
第四,不要迷信西學(xué)可以救世,同樣也不要神化我們的文化。中國(guó)的文化典籍和文化名人,在封建教育文化環(huán)境里已經(jīng)被神圣化,在民間傳播中帶有迷信和崇拜的意味。學(xué)習(xí)國(guó)學(xué)反對(duì)薄古厚今,同樣也不能薄今厚古。
(作者單位:天津市教育教學(xué)研究室)
推薦理由
當(dāng)前,學(xué)習(xí)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已成大勢(shì)所趨,與此相應(yīng)的國(guó)學(xué)教育亦在各地風(fēng)生水起。博主從一名語文教師的視角,結(jié)合自己對(duì)于國(guó)學(xué)的認(rèn)識(shí)和體悟,對(duì)如何將國(guó)學(xué)教育納入中小學(xué)課程體系做了冷靜的思考,并提出了頗具理性的實(shí)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