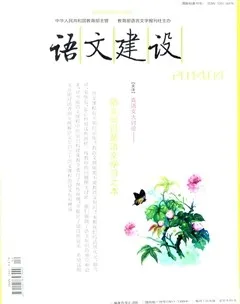建設真語文的語用知識基礎
關于真語文的討論,有一個普遍忽視的方面就是:語文課程知識問題。課程的問題,“本質上是知識的選擇問題”[1]。盡管語文不是知識型學科,而是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實踐性學科,但語文實踐離不開知識的指引,否則,就會墮入傳統語文教育那種“暗里摸索”(葉圣陶語)的盲目低效境地。
真語文“真”在哪里?真語文是要培養學生能夠應付現實生活、工作、學習真正實用的語文能力。這個語文能力的培養,要靠一套“語用型”的語文課程知識體系。
當今我國語文教育問題的根源,幾乎都能找到其知識基礎上的癥結。
一是語文課程知識內容陳舊。現有的語文課程知識主要產生于20世紀前期,是當時語言學、修辭學、文章學、文藝學等所謂“新學問”的移植,此后雖略有修正,但整體面貌并沒有大的改觀。我們過去常用的“字、詞、句、段,語、修、邏、文”的基礎知識,“主題、材料、結構、語言”等文章知識,“議論文三要素”“小說三要素”等文體知識,“重點突出、中心明確、情景交融、鋪墊照應、對比映襯、先抑后揚、開篇點題、收束全文”等寫作知識,現在看來不免陳舊。這些“語文基礎知識”在語文教育發展歷程中,或許曾經有效,而今隨著語用學、語篇學、語境學、文藝學、傳播學、閱讀學、交際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許多新的更有效的語文課程知識理論已經涌現,如語境、語體、語篇、過程寫作、言語交際、媒介語言等知識,應引起我國語文教育界應有的重視。
二是語文課程知識觀念落后。從當代知識觀去看現存的語文課程知識就會發現:長久以來我們所固守的那套知識系統,大致與認知心理學中的陳述性知識相當,沒有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我們對這些知識的認識還停留在客觀的、靜態的、普泛的原理知識層面,沒有考慮到當代知識的發展性、情境性、動態性、生成性、多樣化的特點。把知識當作可以記憶、儲存、可灌輸傳授的東西,這種狹隘的知識觀不但難以實現從知識到能力的轉化,而且還造成了語文教育與生活世界的隔離,與個體語言生命的疏離,與人的精神世界的分離。更為關鍵的是基于傳統語言學、文章學的知識體系,與基于當今語用學的知識體系,幾乎是兩套本質不同的語言知識體系。前者研究的是靜態的、抽象的、有固定意義的語言符號,指向語符和語義教學,以認知并運用符合固定語法規則的正確的句子為重心;后者則是以言語為研究對象,指向具體情境中的語言運用,培養的是符合語境的真實靈活的語言交際能力,這更接近語文教育的本質。
三是語文課程知識概念與認識的分歧。百年來,現代語文教育一方面表現出一種知識化的總體趨勢,另一方面又存在對知識教學的質疑。我國語文教育經歷了由“追求知識”到“淡化知識”再到“重建知識”的發展歷程。其實質并非“要不要”知識的簡單回歸,而是“要什么樣”的知識的命題轉換,是對“什么知識最有價值”的永恒追尋。傳統的語言學知識源于結構語言學,是靜態的語文知識體系,而今要基于功能語言學、語用學的發展,進行語文課程知識體系的更新和重建。
2011年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指出:“語文課程作為一門實踐課程,必須要求學生在閱讀、表達的實踐上下功夫,避免圍繞知識條文、概念定義耗費精力。”[2]還認為:“語文課程目標不是落在關于語言、文字的知識系統和學科規律的理論知識上,課程內容不是語音學、詞匯學、語法學、語用學、文字學、文章學、文學的知識拼盤,而是要讓學生學會‘運用’或者說‘駕馭’語言文字這種工具,是要通過運用語言文字的范例和實踐,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在本課程和其他課程的學習中,在將來不同工作領域運用好語言文字。”[3]
我們認同這些說法,但對此有不同的認識理解。一是關于語文課程知識的概念。課標組說的是“狹義知識”,我們用的是“廣義知識”,即包括事實(范例、課文)、概念、技能、策略、態度等。可見,“語言文字的范例和實踐”本身就是案例知識和實踐性知識。二是要達成“讓學生學會運用或者駕馭語言文字工具”的能力離不開相應的語文課程知識體系。“案例和實踐”是不可窮盡的,需要抽象與概括。這種抽象與概括的語言實踐知識主要就是“語用知識”。語用學是研究語言運用規律的學科,是語文教學的原理學科。我們說的語文課程知識主要指語言運用知識,即“語用知識”。
基于語用的語文課程知識理念和體系,有如下特點。
第一,以“語用知能”為核心。
傳統的語文教育主要是基于靜態語言學的語言符號形式和客觀意義的教育。它容易墮落為行為主義的死記硬背與機械模仿,難以培養出靈活應付各種生活、工作、學習情境中的語言應用能力。當今社會,語言的實際運用能力和交際能力日益重要。比如,禮貌得體地打電話,在各種場合與人交流溝通,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訴求,通過媒介與人協商溝通達成協議等,都需要真的語言能力,需要語用型的語文教育。
韓雪屏認為,由于當代語文課程與教學缺乏“語用”這個上位概念,因此,就不可能自覺地衍生出諸如話語、文體、語體、得體、語境、語篇、語用原則、語用失誤等一系列下位概念和知識體系,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研制和轉化出相應的、用以指導學生言語實踐的動態性知識。[4]雖然語用學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西方學者創立和發展起來的語言學的一門獨立的新學科,但至今,“語用”概念還沒有正式進入我國中學語文課程與教學領域。這種狀況,主要源于語文課程知識理論建設上認識的誤區和行動上對相關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的隔膜與拒斥。
第二,“以交流能力”為取向。
語文能力是以“閱讀理解”為主,還是以“表達交際”為主?這也是當今語文教育目標取向基點的分歧所在。傳統的語文教育以“閱讀理解”為中心,以閱讀理解能力培養為主要任務目標,說寫處于附庸地位。這種以理解吸收為主的語文學習,是一種被動的、內向型的語文能力的教育,它與傳統封閉保守的社會需求基本一致,而現代社會是一種外向、交往型的社會環境,更需要人的表達交流與溝通合作能力。當今的文學理論已由文本中心、作者中心轉向“讀者中心”,國外的寫作教學理論也實現了由“文章(結果)中心”向“交流(讀者)中心”的轉型,這是現代社會對人的交往技能及相關學科理論“向外轉”的結果。
在一個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不同民族之間利用互聯網等現代通訊工具廣泛合作交流的時代,過去靠一己之力完成的工作,現在須靠團隊、集體的力量甚至跨地區、文化、國家去完成。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如何運用語言進行溝通、交流、合作變得日益重要。人們的語言交際能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成為生活、工作、學習所必需。
第三,以“語境、語篇、語用”知識為重點。
一個具有合格語文能力的人應該是一個必須能夠靈活自如地應付各種人、事以及各種情境需要的人。說出合乎情境的話語,寫出合乎情境的文章,閱讀時能夠還原語境的豐富內涵,聽話時能夠聽出話外之音,這是語文教育中的語境感知、還原與構建能力。目前的語文能力是一種“去語境”的通用語文能力,不考慮對象、場合、目的、情境,文字限于其字典意義,表達限于其語法形式,意義的褒貶似乎都是固定不變的。我們且看一個例子。
一個小學二年級學生在《我的理想》的作文中寫道:
阿爹還沒走的時候,他對我說,你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長大做個科學家;阿媽卻要我長大后做個公安,說這樣啥都不怕。我不想當科學家,也不想當公安。我的理想是變成一只狗,天天夜里守在家門口。因為阿媽膽小,怕鬼,我也怕。但阿媽說,狗不怕鬼,所以我要做一只狗,這樣阿媽和我就都不怕了……
如果用傳統語言學知識和通行標準來評判這篇學生作文,當然有點“不登大雅之堂”。可是回到作文的語篇語境去解讀,這篇習作卻又是多么情真意切、真摯感人啊!然而教師卻在學生的作文本上畫了個大大的“×”,并寫道:“這也叫理想?”我們認為這名教師犯了兩個錯誤:一是用偽圣的道德評判誤讀了孩子純真的心靈,二是缺乏語境、語用知識的常識。我們的語文課程知識是一套與現實生活、工作、學習需要的真實的書面表達能力不發生聯系的假知識,這些假知識甚至可以將學生原本在生活和課文中獲得的正確的語感戕害殆盡,導致我們的語言教育扭曲變形。
第四,吸收并開發當今社會急需的語用知識。
隨著當代電子信息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有關電腦讀寫、屏幕閱讀、網頁瀏覽以及信息的搜索、識別、鑒賞、傳播等媒介語言教育已經成為各國語文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內容。然而由于我們的語文教育觀念落后,這些新的語文能力需求并沒有進入語文主流教育的視野。
我們不去培養學生鑒別信息的真假優劣、獨立思考以及自由表達的能力,不去培養學生閱讀說明書或海報、瀏覽網頁、發布信息的能力,將很難培養出適合當代信息科技發展,參與國際間激烈競爭的有創造力、批判力的高素質公民。
總之,我們的語文教育觀、能力觀、知識觀、教學觀、評價觀等方面都面臨著知識和理論的更新和重建。語用學及其知識,則很可能是我國未來偉大的語文教育重建工程的知識基礎與理論來源。
參考文獻
[1]王榮生.簡論制約語文課程與教學目標的知識狀況[J].學科教育,2002(10).
[2]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組.關于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的修訂[J].基礎教育課程,2011(36).
[3]巢宗祺.關于語文課程性質、基本理念和設計思路的對話[J].語文建設,2012(3).
[4]韓雪屏.審理我國百年語文課程的語用知識[J].課程·教材·教法,2010(10).
【本文系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新修訂課程標準的實施研究”相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