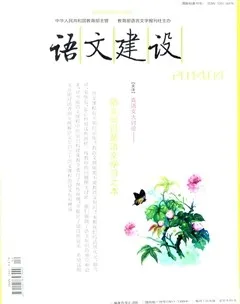語文課程須立足語言形式
《語文建設》正在開展真語文大討論。這是一件好事。人們也許會問:什么是真語文?其實,真語文就是語文。在一般語義層面上,真語文與語文這兩個語詞含義相同,語文是什么,真語文就是什么。真語文與語文的區別在于語用層面:真語文是針對假語文而言的。正如真假美猴王,真美猴王就是美猴王,之所以要叫真美猴王,是因為出現了假美猴王。真語文大討論,其價值就在于引導人們思考并把握語文課程的本質,反思并拒絕那些假語文,從而提高語文教學質量,并推動語文課程改革健康發展。
語文的本質是什么?
語文的本質在于培養和提高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這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目標,或者是語文學科設科的基本出發點。因此,課文的語言形式應當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課文或文章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但語文教學中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與社會上一般人讀文章時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是不一樣的。一般人讀文章,重在文章的內容。比如地方日報上一則停水的通知,人們關心的是什么時候開始停水,什么時候恢復供水,而不太在意文章的形式。甚至讀一部小說,一般人關心的是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而不太在意小說的文學特色或語言形式,但在語文教學中情況發生了變化。要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就必須重視課文的語言形式,課文的語言形式成了教學的主要內容。這就是語文課程中形式與內容的辯證法。正如書法:一首唐詩,可以用柳體寫,也可以用歐體寫,唐詩是內容,柳體或歐體是形式;但當我們研究書法藝術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當我們研究柳體書法藝術時,柳體書法藝術就成了研究的內容,柳體書法藝術既可以通過一首唐詩來表現,也可以通過一首宋詞來表現,而唐詩或宋詞成了柳體書法藝術賴以存在的形式。語文課程中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系也正如此。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語文教學應當引導學生認真學習課文的語言形式,在課文的語言形式中汲取作者的言語智慧,讀出課文的思想內容。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什么是假語文。游離了課文的語言形式,沒完沒了討論文本內容或文化內涵的語文課背離了語文課程的本質,那樣的語文課其實已經不是語文課,而是科技常識課、政治思想課或泛文化課。一名語文教師教學《中國石拱橋》,不教說明文的知識,不培養說明文的閱讀和寫作能力,而是講二十八道拱圈的力學原理,留的作業是“為家鄉設計一座石拱橋”。這哪里是語文課?這就是科技常識課,簡直是橋梁建筑的專業課。一名語文教師教學鄒韜奮《我的母親》,不引導學生學習作者是怎樣表達親情的,而是不厭其煩地進行母愛教育,課前還不辭辛苦地寫了《我的父親》印發給學生,因為他覺得,不如此親情教育就不充分。一名教師教學《武松打虎》,讓學生討論老虎該不該打,有的學生說不該打,因為老虎是國家保護動物,有的學生說該打,因為它會吃人。這名教師不知道,《武松打虎》的價值至少在于讓學生懂得文似看山不喜平的道理,學會把事情寫得曲折,有波瀾。
當我們強調課文語言形式的時候,有人會問:那還要不要課文的思想內容?還要不要情感態度價值觀?回答是:當然要。任何課文都有思想內容,任何課文都有情感態度價值觀,因此,語文課程必然具有并且必須重視其倫理功能或思想教育功能。人才學家的統計資料表明,對于人的成長和發展,智商的作用約占30%,而情商的作用約占70%。重視情商,重視情感態度價值觀,是教育的進步,是當代教育重要的價值取向,也是課程改革的正確方向。情感態度價值觀是語文素養建構不可或缺的要素,對于語言能力的形成和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制約。一個思想貧乏的人不可能有豐富的語言,一個情感淡漠的人不可能寫出感人至深的文章,一個不夠誠摯的人不可能說出可信度高的俗語,一個價值觀念淺薄的人不可能有深刻的表達。正因為如此,我們同樣反對離開課文的語境,孤立地講授語言知識和貼標簽式的機械練習。閱讀教學必須在明白“寫了什么”的基礎上思考“怎樣寫的”也是這個道理,因為離開了一定的思想內容,文章語言形式的成敗得失和高雅俚俗也就說不清。語文教學有兩個主要的錯誤傾向:一是游離文本進行泛文化討論,一是孤立地講授語言知識。前者的錯誤在于忘記了語文課程的根本任務在于建構學生的語言世界;后者的錯誤在于不明白語言世界必須通過語言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系才能建構起來,離開了語言世界與生活世界的關系,即使表面上建構起來的語言世界也必然是蒼白的、空洞的。
我們肯定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意義,是建立在以下幾項內容基礎之上的。第一,情感態度價值觀對于任何一個學科都不是最本質的東西。語文課程的人文性是附著于工具性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說語文是表情達意的人文工具。第二,情感態度價值觀不是與知識能力相并列的內容。正如課標所說,知識和能力、過程和方法、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是三個維度,三者構成了一個立體。教學設計中將情感目標與知識能力目標分立的做法是不恰當的。第三,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應當是潛移默化的,應當滲透到聽說讀寫的語文活動中去。第四,游離課文的語言形式而討論文化內涵,是喧賓奪主,是當下阻礙語文課程改革健康發展的主要弊端。第五,課文的思想內容必須引導學生從字里行間讀出來,而不應當由教師告訴學生,這是語文教學的底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明確提出“語文課程是一門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綜合性、實踐性課程”,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是近十年來中國語文教育最了不起的進步。
既然語文課程的基本目標在于培養和提高學生應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既然課文的語言形式應當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那么語文教材就應當堅持文體組元的優良傳統。課程改革語文實驗教材多采用文化主題組元的體例,這是一個誤區。主題組元存在著無法克服的矛盾和弊端:第一,選擇哪些主題?文化主題是非常豐富的,而一冊教材六七個單元,一套教材三四十個單元,要哪些主題,不要哪些主題,理由何在,誰說得清?第二,主題之間的序列如何安排,理由何在,誰說得清?之所以說不清,就是因為文化主題并非出于語文的本質,不能體現語文的本質。第三,表面上是重視了文化主題,其實卻局限了文化主題,因為一個單元四五篇課文只能是一個主題。放開這種局限,每篇課文有不同的文化主題,豈不更加豐富多彩?第四,一個單元中的幾篇選文,原本不是為這個主題寫的,各有其特定的思想情感,現在籠統地確定一個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對學生產生誤導,使其養成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的壞習慣。第五,與自主學習的理念背道而馳。按照自主學習的理念,課文的主題,課文的思想情感,應當引導學生從課文的語言形式中讀出來。可主題組元的教材,在學生閱讀課文之前就已經把主題告訴他們了,這是以編者的閱讀代替學生的閱讀。香港教材研究專家何文勝先生曾批評大陸課程改革實驗教材“在單元教學的組元上,沒有承傳20世紀八九十年代比較合理的以能力組元的經驗”。
文體組元的合理性就在于體現了語文課程的本質,遵循了學生學習語文的規律,把握了課文語言形式這一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因為,文體正是文章最大的語言形式或曰語篇樣式。文體正是課文語言形式的主導因素。課文語言形式的其他因素都受到文體這一主導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例如句式的長短,記敘文多短句,議論文多長句,因為記敘文要呈現事情的進展,要有鮮明的節奏和生動的狀態,句子不宜太拖沓;而議論文要表達嚴密的思想,就要有許多定語、狀語,甚至以句子形式作為句子成分,要用復句,甚至多重復句。再如修辭格,記敘文多用比喻、擬人、夸張等,這是出于生動形象的需要;議論文多用對比、排比、設問、反問等,這是出于思想鮮明、深刻、流暢的需要。把握了文體,就把握了課文語言形式的主導因素,其他因素就可以迎刃而解。文體組元正可以以簡馭繁,因而也就便于教學。在課程改革之初,那些在開發許多體現時代精神和先進價值觀念的優秀選文的同時能夠堅持文體組元的語文教材,表現了難能可貴的學術信念和學術勇氣。
既然語文課程的基本目標在于培養、提高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既然課文的語言形式應當是語文教學的主要內容,那么,語文教師解讀文本的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語文教師應當善于發現字里行間的妙處,善于把握文本的語文教育價值。語文教師只有自己會讀書,才能教會學生讀書;只有自己會寫文章,才能教會學生寫文章。遺憾的是,時下,文本解讀能力低下正在成為語文課程改革健康發展和語文教師專業發展的瓶頸。我們曾經做過這方面的調查:在沒有任何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作為骨干教師的國培班學員,近半數不能恰如其分地分析文本的立意,對于文本的語言表達,更是缺少應有的專業敏感,多數不能絲絲入扣地具體分析,而只能干巴巴地概括幾個所謂的寫作特點。對《列子·湯問》中的《兩小兒辯日》,他們說不清兩小兒的爭辯勝負如何;對朱自清的《春》,他們看不出第2自然段的妙處;對《呂氏春秋·察傳》第1自然段,他們說不清句與句之間的關系。把語文課上成泛文化課,既有語文教學思想的誤區,也有文本解讀能力薄弱的制約,且兩者很可能互為因果。重思想內容輕語言形式的語文教學誤區遮蔽了文本解讀能力的重要性,而文本解讀能力的薄弱也使得許多語文教師更喜歡討論課文的文化內涵。
課程改革的一個重要成就是,教師參與教學研討和學術討論的熱情空前高漲,但十年來在通識主義教師培訓的影響下,語文教師學習和研究的興奮點往往在于怎樣教,而不在于教什么。課程與教學論研究生入學考試,不分具體課程的統考也在強化只研究怎樣教而不研究教什么的誤區。其實,內容決定形式是基本的哲學常識,教什么遠比怎樣教重要得多。語文教師應當首先是一個語文人。一個具有良好文字功底,對語言文字有獨特敏感并有深厚語言學理論修養的人,才能從容地成為一名優秀的語文教師。這樣的語文教師才能充分展示語文的魅力,激發學生學習語文的巨大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