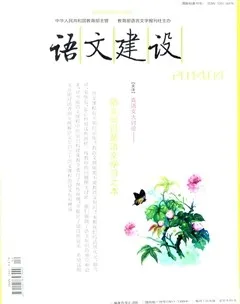艾偉和他的國文教學心理學之研究
在母語教育上,漢語有至少幾千年歷史,一點也不落后于國外,但是國產的語文教學法講經驗,講描述性的總結,而西方現代教育心理學往往講實證,讓數據說話。例如,多讀多寫是提高語文水平不二法門、背書默書有助于記憶、勞于讀書逸于作文等經驗在我們看來似乎是不言而明的道理,但國外心理學研究就需要用事實來證明。德國維茨堡學派心理學就通過實驗證明:“同樣記憶一段學習材料,帶有記憶目的的背誦比反復朗讀更節省時間。”
“五四”以來,隨著西方先進教育思想、教學方法、教育心理學理論知識的引進,國內也有學者開始借鑒國外教育科學實驗的方法來研究教育。這些人大多是帶有“教育救國”理想學成歸國的大學者,我們比較熟悉的有陶行知、廖世承、陳鶴琴。這里面也有些值得一提的而過去常常被我們有意無意忽略的學者,其中艾偉就是一個典型,他可以說是民國時期利用教育心理學科學實驗方法研究漢字漢語規律以及國文教學的“第一人”。
一、艾偉行狀簡介
艾偉,字險舟,原籍湖北江陵,1890年8月12日生于湖北沙市,1955年9月27日病逝于臺灣新竹,享年僅66歲。艾偉早年為錢莊學徒,因鑒于清廷腐敗而參加了孫中山所創的“同盟會”,后又參加辛亥革命。先后求學于武昌美華書院、安慶圣保羅高等學堂、上海圣約翰大學,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后獲學士學位。1921年秋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心理學,次年獲碩士學位。繼入華盛頓大學攻讀教育心理學,1925年獲博士學位后歸國任東南大學心理學教授。后任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兼任上海大夏大學高等師范科主任教授。1931年6月發起成立“中國測驗學會”。當時參加的有張士一、陳鶴琴、廖世承、陸志韋等名家。1933年秋教育部聘其為首屆“部聘教授”。1934年和夫人范冰心在南京寓所開辦萬青試驗小學,1937年發起成立中國心理學學會,被推選為該會理事。他首創我國“教育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長,招碩士學位研究生。抗戰期間在重慶開辦心理學實驗班,研究初中生的國語、英語、算術三門課業的學習過程和心理機制問題,致力于編制各類智力測驗量表。1949年直至病逝,一直居住在臺灣。
艾偉主要著作有《高級統計學》《初級統計學》《初級教育心理學》《師范科教育心理學(上下冊)》《教育心理學(上下冊)》《教育心理學大觀(上中下三冊)》。關于國文教學的有《閱讀心理:漢字問題》《中學國文教學心理學》以及相關的論文。
二、艾偉著作《閱讀心理:漢字問題》述評
艾偉在國文教學科研中的代表作是《閱讀心理:漢字問題》,該書于194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艾偉領導的科研團隊為這個實驗整整工作了二十五年。他在這本書的“鳴謝”一節里說:“關于書中已載各種實驗之進行,昉于民紀十二年,距今已二十五年矣。”從1923年到1947年,跨越年頭正好二十五年。他說在這二十五年間,實驗得到“美京華盛頓、佐治城西大學之在校學生近一百五十人”的幫助,還有他的同學、朋友、學生參與。其中有的負責“漢字橫排直列之比較研究”,即直排橫排究竟哪種讀起來容易;有的負責“漢字測驗之編輯并統計”;有的負責“詞匯分析”;有的負責“書法實驗”;有的負責“字量方面統計”。
二十五年過去了,等到書出版時,有五位參與者已經去世,而“參與實驗和測驗的數千個學子在此二十五年中諸君固已長大成人,而服務于社會為其中堅矣”。艾偉和他的團隊為什么要研究漢字問題呢?他在這本書的“自序”里說:因為四十年來(指清以后)“關于漢字問題之討論殊費學人之苦心,披荊斬棘成就自多,然而有時不免筑室道旁,謀多行少,似學人所見或仁或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其結果也,政府既忌憚于采擇施行,社會亦艱于勇往推進,長此濡滯,影響甚巨。心理學家有鑒于此對漢字作科學之整理,所謂科學之整理不外乎實事求是,蓋初學者對于漢字之感覺有難有易。何種字易于學習?從教學經驗中故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管窺全豹必須用實驗方法作大量初學者之心理觀察,并須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學習歷程,如是則癥結所在不難查出,改進之道方能求得。”本書總的指導思想是研究漢字規律以幫助提高教學效率,因為任何語言學習閱讀的主要障礙就是難讀的詞匯,詞匯積累多了閱讀就會順暢,故本書名為《閱讀心理:漢字問題》。全書一共九章七十五節,分別是:字形研究,字量問題,識字測量,詞匯研究,音義分析,簡化問題,排列(橫排豎排對閱讀的影響),書法研究,全書總結。全書共附錄的各種實驗數據圖表達78張之多,各種插圖16幅。
由于艾偉是受過嚴格的科學訓練的教育心理學家,又精通統計,所以對每一個問題研究都取嚴謹的科學態度。每一章不單單有實驗數據及其分析、結論,而且對本研究中各家成果詳細介紹,例如,第一章“字形研究”后面幾節概述了另一些歸國的心理學家劉廷芳、蔡樂生等人的同類研究,第四章“詞匯研究”介紹了王文新、王顯思、周其辰等人的相關研究。因為母語教學范圍很廣,漢字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所以第二章“字量問題”的研究涉及漢字的歷史,通用字典、普通書報雜志常用字匯、語體文的字匯、小學的分級字匯、兒童民眾盲人字匯、大眾實用字匯、市民常用字匯、農民常用字匯、店號常用字匯等。在國外,如美國考“托福”每年出“字匯總表”,也對每年全世界各大報刊常用詞匯進行統計,以確定考核的范圍。本書出版時已在40年代末。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社會及文化教育家常有“漢字太難”“廢除漢字”“以拉丁文拼音化代替漢字”等宣傳鼓動聲甚囂塵上,認為可以為中國老百姓創設出一套“多快好省”掃除文盲的工具來。艾偉等學者則默默無聞地研究分析,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漢字,力圖找出更快更省力地教好漢字學好漢語的辦法。比起簡單地憑感情贊美或批評漢字,這種科學研究實事求是的態度更是我們需要的。
在此書出版之前的1928年,艾偉就曾在當時的《教育雜志》第20卷第4、5期上發表了十幾萬字的《漢字之心理研究》的實驗報告。他在這一長篇報告的“緒論”里談到研究漢字學習問題。針對社會上多種不同主張(如取消漢字,用西方字母代替漢字,或保存國粹反對簡化或是拉丁化字母道路),他說:“吾人茍具科學之眼光對于各派之主張,不存入主出奴之見;故問題如能解決用急進派之主張可,用保守派之主張亦可,而創造注音字母以化現有文字,亦未嘗不可。”同時,他強調必須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注音字母是否絕對注音,同時能否通行全國?二是中文字業有數千年之歷史,行用注音字母后,此種‘社會遺傳’宜如何保存?三是中國文字艱深,致多不識字之人固也;然若用科學方法從事去教授改良艱深之處可以減至何種程度?”
正是本著這三點,他們進行了二十五年的實驗研究。可以說艾偉的漢字研究代表了民國期間漢字認讀研究的最高水平。
三、艾偉關于文言文白話文閱讀的研究
艾偉的研究可以說已經涉及了現代語文教育中的幾個核心問題。其中影響最大的除“漢字問題”外,就是關于“文言白話”。1929年到30年代初,上海、北京等地文化教育界“文白之爭”“漢字拉丁化之爭”“大眾語運動”“讀經問題”等討論十分熱烈,一些文化教育界、演藝界的頭面人物紛紛撰文表達意見,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說的:“無論贊成或反對,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因為宣傳的口氣越多,科學的態度就越不夠。凡是宣傳,就不免對于不利的事實有所掩飾,同時對于有利的事實有所夸張。掩飾和夸張,就會失了科學的真理。”(《漢字改革》1940年)與宣傳相反,采取科學研究態度的一批人,如艾偉、廖世承、陳鶴琴、龔啟昌、張九如等卻在做扎扎實實的科學實驗,而艾偉尤為其中杰出的人物。
早在20年代前期,“艾偉就通過在江蘇、浙江等省中小學的實地調查和實驗研究,指出中學白話與文言應該兼教,初中以語體為主,高中全部采用文言。初一到初三,語體與文言最恰當的比例應該是7:3、6:4、5:5。這一研究成果獲得教育界的廣泛認同。1929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國文課程暫行標準》就采用了這一結論,從而確立了白話文在國文教育中的地位。”(顧黃初主編《中國現代語文教育百年事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這里談到的在江浙二省的實驗研究,指的是艾偉在1927年發表的《初中國文成績之實驗研究》及其“續”(載《教育雜志》卷24第4、5期)。兩篇報告有十余萬字,是利用國外測驗學科最新理論研究“教學評價”的實驗,已經包括了初中生學習的白話文和文言文的不同速率結果的比較。艾偉為確定白話文在國文教學中的地位做出了科學研究,但是后來形勢發生了變化,30年代初文白之爭又起,“大眾語運動”走得更遠,一度有“打倒文言”的趨勢。教育家總是以科學研究結果說話。艾偉在1934年發表的《關于語體文言的幾種比較實驗》(載《教育雜志》卷24第4期)報告里,又重申了前一次報告(指《初中國文成績之實驗研究》)里的一些話,指出:小學到初中白話文學習的曲線已經到了“中間或后面的一段”,并強調這一結果是由一千人參與實驗得出的,而不是偶然的。據此,他在當時提出:“文言文是否被打倒,白話文能否取而代之,在文學家方面,爭論已甚囂塵上,不容科學家置喙于其間。科學家也豈敢妄參末議,本節第二條(主張文理分量由初一以上至初三應逐步加多)稍涉袒護文言之嫌疑,將來難免主張白話之質問。然吾輩之客觀研究,事實俱在。固非信口雌黃者可比也。夫閱書用白話文為一種工具,用文言文亦為一種工具。二年級之白話文程度既幾相等于三年級,且有過之者,而文言文程度則尚加高。是一種工具已漸完整、他種工具尚需磨冶,假使文言文不能完全推翻之時,中學畢業時兩種工具俱懂,可以運用無窮,較之只有白話文一種工具者,其生活之豐富不可同日而語也。”
然后,他在1934年的這一份有數萬字的實驗報告內,又用高中測驗結果證實了兩種文體學習的結果。其中一張張數據分析限于篇幅這里無法引述。艾偉在結論部分說:“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在現在我覺得對于七年前的第一次報告中的結論尚有維持必要,這結論是:若語體文言兩種同為吾人表達意思之工具,則在求學時代應當磨冶此種工具。此種工具若有分期磨冶之必要,則在小學應當為語體文,在中學應為文言文。”因為他的實驗報告顯示:高中生在語體文(白話文)上的測驗成績與初中生沒有什么差別,也就是高中生讀現代文的理解程度并不比初中生高。
不但這些,艾偉還有更進一步的實驗。1939年,他在重慶沙坪壩創辦了我國教育史上第一個學習心理實驗班。他在這個班上做了多種項目的實驗,實驗結果都記錄在《教學報告》內,其中關于初中文言文誦讀的問題,具體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展開研究。
一是篇幅長短和誦讀速率的關系。他取文言文書籍一本,其中有長短不一的篇目,最短的為64字,最長的為302字。每天由受試學生誦讀一篇,讀之前先由教師串講內容。實驗時,主試者的秒表計算學生每誦讀一遍所需時間,直到背誦為止。以181字數為例,一個被試學生需讀34遍才能背熟,費時1881秒。初讀第一遍需70秒,第二遍65秒以下,依此降至背誦。實驗發現了學生智力之間的差異。
二是文章內容在背誦與默寫上的影響。他以七篇文言文做實驗,要求每篇背誦,過一學期再要求逐篇默寫。這七篇文言文是《陋室銘》《六月十四日曾氏家書》《不死之藥》《孔子世家贊》《春夜宴桃李園序》《七月十七日曾氏家書》《馬說》。實驗結果是:每百字需要秒數最多的是《孔子世家贊》,次多的是“曾氏家書”兩篇,這說明內容枯燥難解會影響到學生誦讀的速率。《陋室銘》《馬說》背書后一學期記住了大半,而“曾氏家書”強記背熟了,但一學期后全忘記,沒有人能默出一字。(艾偉《戰后中國之教育實驗》,載《教育雜志》卷32第1期)這里也無形中證實了德國維茨堡學派關于記憶的一個實驗結論:“1907年維塔澤克發現,僅僅被動的朗讀再朗讀絕對不如讀后跟著主動背誦更加奏效。在主動背誦中受試者強制自己回想他所讀過的材料。這一論述由蓋茨簡化為清楚的數量形式,他不僅肯定了維塔澤克的結論,而且證明不論是學習效率的提高,還是記憶總量的增加,兩者都是由于把不斷增加的學習時間百分比用于背誦促成的;甚至把百分之八十的時間用來背誦也仍然比之較小的百分比更為有效。”([美]加德納·墨菲、約瑟夫·柯瓦奇《近代心理學歷史導引》,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18頁)因為同樣一篇文章需要誦讀34遍后才能背誦,而如果帶著背誦默寫的目的去記憶,顯然從總時間上少于“朗讀再朗讀”。艾偉曾經自豪地說:“在學習心理實驗班里近八年來所作類似的研究非常之多。其所獲得的材料并由此而擬定的原則,足夠我們編輯一部分合乎兒童學習心理的初中國文讀本。”(艾偉《戰后中國之教育實驗》,載《教育雜志》卷32第1期)可惜由于戰爭動亂,1946年以后艾偉所創實驗班中途夭折,而他的研究也沒能很好地運用到國文教學上來。盡管如此,他自己卻寫成了一本二十多萬字的《中學國文教學心理學》。限于篇幅這里無法詳細介紹。
四、幾點啟示
鉤沉索隱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從中獲得對于當下的啟示。
一是看看我們的前輩已經做了些什么。因為近年來常常聽到一些討論語文教育的專家會發一些宏論,好像現代語文教育是沒有什么科學研究的,有的只是一些經驗性的總結。在他們眼中,包括葉圣陶、夏丏尊、黎錦熙諸位老先生的著述也不過是一些缺乏現代課程論教學論意識的經驗性描述,只有外國人的東西才可靠。他們有一種“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氣概;豈知孔子以前,天早就有了。現代語文教育的研究也不是近二十年來才有的。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或因無知或因偏見,有意無意忽略了前人的成果,自己陷于“盲瞽”而不自知,反而以此欺世盜名,這是殊為可笑的。
二是看看前輩們是怎樣扎扎實實搞科研的。他們沒有參與意氣之爭,不發空泛的宏論,不提似是而非的口號。實事求是的作風,正可以用來治治時下的燥熱風氣。
三是通過學習可以了解他們的一些結論。這些結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例如文白兩種文體在中學里的比例究竟怎樣才合適,語文學習方法怎樣才有效率等。珠玉在前,盡可讓我們去分析研究,去繼承和發展。因為像艾偉這一批人可稱得上學貫中西,既讀線裝書,又懂“洋裝書”。不像現在的有些人在中國學英文,到外國去學一點東西然后拿回來嚇唬國人。國文既未通,教育理論也一知半解,以此態度豈能研究好語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