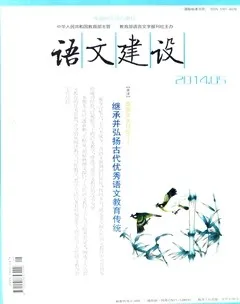小議說明文閱讀教學的起點
《死海不死》作為一篇收入中學語文教材的說明文雖不算經典,但錢夢龍老師十多年前執教這篇文章的教學實錄,已成了體現其教學理念的代表作之一。[1]研讀這篇實錄,對于深刻理解其教學理念,特別是如何活用其思想來執教知識性說明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
初讀該教學實錄的人,一個共有的印象是,錢老師以組織學生討論什么內容不用教為教學起點,然后要求學生根據課文后面的練習題想一想:練習題要求我們掌握的知識哪些可以不教?
就這篇課文而言,把一堂課的教學討論分為“什么可以不教”和“什么需要教”兩部分,是基于這樣一些考慮:首先,關于死海不死的知識,學生在中學地理課或者更早些的小學自然常識課上比較系統地學習過,再學習已經變得沒有必要;其次,說明文是初中階段語文課上著重學習地文體之一,一些基本說明方法如列數字、舉例子等,也被學生所熟知,教師再來教,不易引起學生的求知欲。因此,提出哪些知識可以不教的問題,猶如一開始讓學生猜測有趣的課文標題一樣,同樣是為了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一種策略。
興趣的激發在這篇課文的教學中當然非常重要,因為課文是知識小品,趣味性是其重要特性。如果趣味性并沒有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得到落實,讓枯燥、沉悶的氣氛主導了課堂教學的展開,就會導致教學效果與教學對象間發生邏輯斷裂。事實上,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也許對錢老師來說,更具挑戰性的是,類似的知識性說明文選入語文教材后,其知識性內容對學生大多已失去了吸引力。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找到什么樣的語文教學的邏輯起點呢?當然,我這里提知識性說明文這一種文體,并不意味其他文體的內容對學生來說必然是陌生的、有吸引力的;而是認為,因為其他文體如小說、詩歌等固有的深度使得重讀帶來的內容上的二度開發,要比知識性說明文更容易找到教學的抓手。就知識性說明文來說,當知識本身成為吸引讀者的基本特性但又被他們廣泛了解時,教學會面臨怎樣大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不過,錢老師教學的高明,就在于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點,并通過自覺提出這一困難來克服它,以顯示其教學的特色。
在什么可以不教的討論之前,錢老師從知識遷移的角度,組織學生回憶地理課上學過的知識,包括地理位置、得名原因、海水趣事等,其目的是為語文課上要教什么提供不同學科的連接點和區分邊界。當他開始組織討論什么可以不教時,也是從語文課的意義上來說的。這樣,學生提出了列數字的說明方法和詞語的理解問題,其實是著眼于說明文怎么寫的問題。這一思路似乎暗示我們,同樣的內容,在地理課上學的是寫什么,到了語文課上就要討論怎么寫。既然怎么寫是以寫什么為依托,不存在一個沒有對象的寫作方法,這樣,引入地理課所學的知識內容,一方面說明了語文作為一門工具對其他學科的普適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研究怎樣寫正是語文學科自身的個性所在。
二
當然,不是有關《死海不死》所有的怎樣寫的問題,都構成這堂語文課的起點。錢老師提出的可以不教,既指向地理課,也指向了此前的語文課乃至課外自學,所以學生才會把列數字這樣一種怎樣寫以及個別詞語的理解問題,都放進了不用教的范圍。
對學生提出的意見,錢老師做了區分。一方面,他認同了個別詞語理解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查閱相關工具書來解決,不必再放到課堂來討論;另一方面,他只是部分認同了學生所謂不用教列數字的說明方法,而是根據課后練習,提出了需要理解列數字中“約數”和“確數”的使用語境問題。應該說,這一提示是有道理的。因為從有些學生的回答看,他們簡單認為“約數和確數相比,當然不夠精確”,所以,通過錢老師的引導,其他學生對不同語境中使用約數和確數的方法有了充分認識,這就使他們深入地學習了列數字說明方法。有些學生則根據約數和確數的關系質疑了課文的表述有自相矛盾處,更是討論不用教的環節中出彩的部分。
不過,也是在這一環節中,學生在舉證說明不用教的列數字方法時,他們的舉證本身連同其表述都是粗疏的,不夠精確的。這里的關鍵是,他們說課文用數字來說明死海的海水鹽含量高時,把兩類數據混淆了。一位學生說:“135.46億噸氯化鈉、63.07億噸氯化鈣、各種鹽占死海全部海水的23%-25%等等,這種說明方法一看就知道,完全可以不教。”還有一位學生補充說“用了很多數據”,但就是沒有把“很多數據”更細致地區分出兩類來。人在死海不下沉,是因為浮力大,浮力大的直接原因是液體的比重大于人體的比重,這是文章中明確指出的。課文中列出了死海中含有各種鹽的總數量,還列出了鹽與海水的比值關系,而這后一組數據,是說明人在死海不下沉的關鍵數據。對此,錢老師卻沒有加以強調。在他總結學生的回答中,只提了總的含鹽量,竟沒有把百分比舉出來,未免有些遺憾。如果說,列數字的說明方法確實是這堂語文課上不用教的內容,那么列怎樣的數字、怎樣在說明不同的對象時,列出更有針對性的數字,也許是這一堂語文課需要確立的一個具體化的起點。這一起點和區分“約數”“確數”的使用問題有學理上的一致性,即怎樣恰當地使用一種說明方法,都涉及說明的具體語境、具體對象問題。
三
在進入哪些知識需要教師教的討論環節,錢老師是從文體角度切入的,這是語文課不同于地理課的又一個特色。文體是語文教學切入文本的重要抓手,此問題復雜,這里不便展開討論,我只分析一個具體的教學例子,以說明另一個教學邏輯的起點問題。
課堂上,錢老師就《死海不死》的文體特點與一位學生展開往復多次的問答,曾引起語文界不少人的關注,鄭桂華老師曾從提問的有效性角度加以剖析。[2]這里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說明文教學邏輯的起點問題做簡要闡述。課堂實錄中師生有關文體特點的一段問答是這樣的(略有刪節):
師:說明文是個大類,包括各種產品說明書、書籍的出版說明和內容提要、詞典的釋文、影劇內容介紹、除語文以外的各科教科書及講義、知識小品,等等。凡是以說明事物或事理為主要表達方式的文本都是說明文。(指一學生)你說說看,這篇課文是說明文中的哪一種?
生(1):是知識小品。
師:(問全班)他說得對不對?同意的請舉手。(多數學生舉手)你說對了,但什么是知識小品,你知道嗎?
生(1):不知道。
師:知識小品有什么特點,知道嗎?
生(1):不知道。
師:你都不知道?(生點頭)那你怎么知道這篇課文是知識小品呢?
生(1):我是瞎蒙的。(笑聲)
師:不,你肯定不是瞎蒙的,你心里肯定有一個關于知識小品應有的“樣子”,而這篇課文正好符合你心里的這個“樣子”。是這樣嗎?
生(1):我心里沒有樣子。(笑聲)
……
師:好好想想,你在各種文體中選定知識小品,當時是怎樣想的?
生(1):因為它是介紹關于死海知識的,文章很短小……所以是知識小品。
師:說得對呀!知識小品就是介紹科學知識的;文章篇幅又很短小,所以叫“小品”。你看你說出了知識小品的一些重要特點,你明明知道,怎么說不知道呢?
生(1):這是我看了課文后臨時想出來的。
師:這更了不起,說明你的思維很敏捷,很有判斷力。我早說過你不是瞎蒙的嘛!(笑聲)下面請大家再來看看知識小品除了篇幅短小、具有知識性以外(板書:“知識性”),還有些什么特點。
在這一師生問答過程中,錢老師對學生的信心和耐心,以及他隨時調整提問方式的智慧,都曾引起不少語文教師的贊嘆。一邊是學生對自己思維能力的竭力否認,另一邊是教師對學生的充分肯定。由此形成的教學張力和活力,似乎把教師對學生思維的推進和發展,充分顯示了出來,但細細品讀這段對話,我仍感到了一些意猶未盡的遺憾。
盡管錢老師和這位學生的對話往復了八九次,但學生得出的關于知識小品的兩個特點,作為其判斷知識小品的理由,缺乏內在的關聯性。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學生對自己的思維究竟是怎樣展開的,內在邏輯又是怎樣的,其實并不清楚。學生最終說出知識小品的兩個特點,其實歸因于錢老師的提問本身(雖然提問也是針對課文而來的)。
第一次提問,錢老師說“說明文是個大類”,如果要從大類中進一步找出《死海不死》所屬的小類,那它該是什么文體呢?學生馬上得出“知識小品”,反應確實敏捷,但如果回看錢老師提問的整個句子,學生其實是在他舉出的說明文下屬各個類別中做了一次不太困難的選擇。拿《死海不死》課文一對照,也只有這一篇能跟知識小品對得上號。
第二次提問,錢老師再次凸顯了“知識小品”的概念:“你在各種文體中選定知識小品,當時是怎樣想的?”學生的回答是:“介紹死海知識的,文章很短小。”這一結論的得出,很難說是表明了學生對這一文體的固有理解,很有可能是從“知識小品”字面上的“知識”和“小品”解析出來的(篇幅短小本來就是古代小品文的重要特征),雖然他本人未必意識到這一點。這樣,學生否認自己的判斷是根據心里樣子而來,也許真說了一句大實話。因為兩個答案,其實都包含在錢老師提問的概念中。錢老師說學生的答案不是瞎蒙的當然正確,但如果理由只從學生的內心找,不把它跟自己的提問內容和課文結合起來分析,恐怕難以探及學生思維運行的軌跡。恰恰在這關鍵點上,錢老師停止了深究轉而提問說明文的其他特點了。
正是在錢老師提問中止的地方,我們發現了說明文教學的另一個起點,那就是,不但要善于揭示學生的思維品質是什么,還要探究其是怎么思維的,其思維的邏輯是怎樣展開的。雖然探究學生怎樣思維的問題也許比探究說明文怎么寫的問題要曲折一些、困難一些,但這也正是現代語境的課堂教學中,我們每一個語文教師需要面對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鄭桂華,王榮生主編.語文教育研究大系·中學教學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鄭桂華.課堂教學中教師提問策略的探討[J].中學語文教學,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