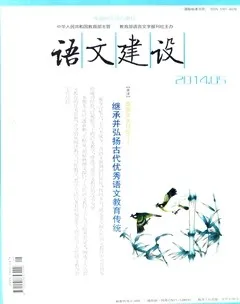民國教科書中《賣火柴的小女孩》概說
《賣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于1846年發表的一篇童話。1919年,周作人首次將其譯為白話,并發表于當年第6卷第1期的《新青年》上。這也是中國人用白話翻譯的第一篇童話。[1]“當一個尊崇個性解放并著力從西方吸取思想資源的時代真正到來,當原始的、淳樸的、生動的生命狀態真正受到推崇,安徒生童話對于精神解放的意義和兒童閱讀的意義很快得到文化界的認可”[2],也受到了教育界的關注。1923年,《賣火柴的小女孩》即入選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自此,這篇童話被許多教材選用。其影響范圍越來越廣,以至于一提起安徒生,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想到《賣火柴的小女孩》。
一、《賣火柴的小女孩》在民國教材中的收錄情況
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館藏的民國時期中小學國文教材中,這篇童話5次被小學教材收入,13次被中學教材收入。
在小學教材中,它主要是供高級小學階段使用的,其具體分布情況如下:

在中學教材中,它主要是供初中階段學生使用的,其具體分布情況如下:

安徒生最初傳入中國時,周作人即贊美“其所著童話,即以小兒之目觀察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真前無古人,后亦無來者也”[3]。他認為安徒生童話“天真爛漫”“合于童心”[4],“有其異常的天性,能夠造出‘兒童的世界’或‘融合成人與兒童的世界’”[5]。民國時期,周作人、趙景深等人致力于安徒生童話的翻譯、傳播與研究工作,他們用白話文翻譯了大量的安徒生童話,并力求在語言上保持原作者創作童話的原本狀態,力求符合兒童心理,體現兒童成長的心理規律。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在“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旗幟下,眾多文人投入到白話文教材的編寫與白話作品的創作、翻譯之中。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國民政府加大了對教育的資金投入,并先后頒布了6個課程標準,對每個學段的識字、閱讀、寫作都做出了明確要求,各項教育制度逐漸完善,“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是民國教育穩步發展、趨于定型的時期”[6]。兒童文學的概念也逐漸形成并發展起來。在以兒童為本位,為兒童創作的文學作品中,童話因其文本內容符合兒童心理、語言形式便于兒童理解,尤其受到當時教材編選者的青睞。因此在中國的原創兒童文學剛剛起步,尚未成熟之時,像《賣火柴的小女孩》這樣優秀的童話便成為教科書中兒童文學的首選。
二、教材收錄《賣火柴的小女孩》時的改動情況
教材中所收錄的都是周作人翻譯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但是在選入教材時,都有不同程度的改編。
高小階段的5套教材中,除《實驗國語教科書》外,其余4套都刪除了小女孩5次劃著火柴,看見虛幻美景的情節,只是簡單地敘述小女孩在大年夜凄涼地死去的故事,并將題目據此改為“可憐的女兒”。童話失去了原有的美好想象的空間。只有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實驗國語教科書》加入了這一場景描寫,既保持了童話的原貌,又忠實于原著,將課文的題目譯為“賣火柴的小女兒”。教材在課文的最后還注明了本篇課文“選自周作人《空大鼓》譯安徒生原作”[7],并補充了安徒生創作這篇童話的緣由和背景知識。這些既便于學生從作者的角度理解這篇童話,又豐富了學生對童話和安徒生的認識,利于學生在學習課文的基礎上拓展閱讀領域。
在13套中學教材中,選文與《實驗國語教科書》基本一致,沒有太大的改動。各版本都增添了對課文出處的說明,并在介紹安徒生時把他稱為“童話之王”[8],還推薦學生閱讀《安徒生傳》《童話論集》等。這些介紹和推薦閱讀既讓學生了解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其童話作品,又擴大了學生的閱讀范圍,增加了學生的文學積淀,有利于提高學生的文學涵養。
三、民國教材對《賣火柴的小女孩》主題的解讀
小學教材中對“賣火柴的小女孩”多是從人文主義角度出發,以悲憫的情懷表達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其目的是教會學生擁有一顆善良的心,尚未涉及對社會的批判與抨擊。如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的《北新國語教本教授書》(《北新國語教科書》的配套教學參考書)在“整理”中指出“要旨同情窮人”[9];《實驗國語教科書》在“說明”中也指出,“這篇寫死寫得并不可怕,而只寫得可憐,使我們讀了永遠忘不了這幅值得人類同情的圖畫”[10]。
在本時期的中學教材中,對《賣火柴的小女孩》則更多的是從社會批判的角度出發,認為小女孩的死是逃離了黑暗社會,奔向光明、幸福生活的解脫。如《初中國文指導書》在“作品研究”中談道:“要旨饑寒交迫的小女兒,雖至凍死而絕無人憐憫,那就只有離開這黑暗的世界,而到光明的天之國了……她脫離了這黑暗世界反能得到歡樂的所在了。”[11]
在小學階段將其解讀為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努力培養學生的同情心,使學生心存美好;到了中學階段,學生已有了一定的思維能力與判斷是非的能力,對于這篇童話的主題,學生可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因此將其解讀為對黑暗社會的抨擊更加突出了學生身心發展的進程。
這一主題解讀的深入,與當時社會的變動也是密切相關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文壇的各個流派重新組合,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左翼運動逐步發展壯大,中國的兒童文學也參與到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激進洪流中。這一時期,“像丹麥安徒生那樣的童話創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來娛樂兒童感情的童話,是不需要的。因為處于苦難的中國,我們不能讓孩子們忘記現實,一味飄飄然地鉆向神仙貴族的世界里。尤其是兒童小說的寫作,應當把血淋淋的現實帶還給孩子們,應當跟政治和社會密切地聯系起來。”[12]人們認為兒童文學一定“要能給兒童認識人生”[13],應“給少年以階級的認識,并且鼓動他們,使他們了解、并參加斗爭之必要,組織之必要”[14],不然,“他們會驚異橫在眼前的世界,他們會懷疑他們的老師,會咒罵安徒生是一個住在花園里寫作的老糊涂”[15]。因此,安徒生童話不再像先前周作人等學者贊賞的那樣,符合兒童的心性,而是被看作反映現實生活的現實主義力作,接受教材的選編者大多夸大、重視或努力渲染其階級性。《賣火柴的小女孩》因此被看作是最能反映下層人民疾苦、暴露社會黑暗的兒童文學作品,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被多套教材收錄,并強化其思想教化的功能和主題。如《基本教科書國文》指導書談到關于這篇童話的寓意時說:
這篇的意義,如用直接陳述法說出,便是:富人的孩子都得好的吃,好的穿,快樂過圣誕節;窮人的孩子該得在街上餓死,凍死,而且沒有人理會他——這是貧富不平等的結果。[16]
可見,教材選編這篇童話,旨在使學生認識到社會中的貧富生活的巨大差距,階級之間的極端不平等,以此培養學生對現實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滿,對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憎恨。
這種政治化的解讀束縛了學生的想象力,限制了學生對文本的多元理解。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為滿足統一思想的需要,實現教育為革命為階級服務的目的,體現教育為政權服務的導向功能,這種教化作用的影響還是十分深遠的。
參考文獻
[1][2][3]李紅葉.安徒生在中國[J].中國比較文學,2006(3):155,157,155.
[4]周作人.隨感錄(二四)[J].新青年,1918,5(3).
[5]仲密(周作人).王爾德童話[N].晨報副鐫,1922-4-2.
[6]李華興.民國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11.
[7][10]國立編譯館.實驗國語教科書[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111.
[8]趙景深.初級中學混合國語教科書[M].上海:北新書局,1931:54.
[9]李少峰.北新國語教本教授書[M].上海:北新書局,1932:127.
[11]朱劍芒,陳靄麓.初中國文指導書[M].上海:世界書局,1932:92.
[12]范泉.新兒童文學的起點[N].大公報,1947-4-6.
[13]茅盾.論兒童讀物[N].申報副刊:自由談,1933-6-17.
[14]大眾文藝.第二次座談會[J].大眾文藝,1930,2(4).
[15]金星.兒童文學的題材[J].現代父母,1935,3(2).
[16]傅東華,陳望道.基本教科書·國文[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