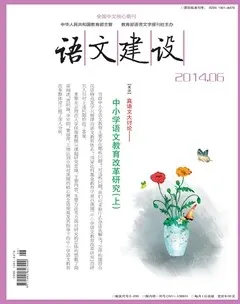《詩經·邶風·靜女》主題新探
《靜女》,出自《詩經·邶風》,是《詩經》中的愛情佳篇,其詩云:“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1]
第一章中“靜女”之“靜”,釋義頗眾,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解釋為貞靜、不輕佻等。毛《傳》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鄭《箋》云:“女德貞靜,然后可畜美色,然后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之。”[2]毛、鄭解“靜”為“貞靜”,言女子雖內心渴望與男子約會,但是行為上毫無超越禮教之處,“自防如城隅”,強調了女子有德守禮法。第二類解釋為閑雅、安詳、幽靜。歐陽修《詩本義》以為:“據(jù)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見而彷徨爾。”朱熹《詩集傳》:“靜者,閑雅之意。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3]聞一多《風詩類鈔》亦解“靜女”為“幽靜之女”。這是位天性安靜的女子,“從男女互相吸引、互相愛慕的角度,指出男子看中的是女子文靜嫻雅的內在氣質”[4]。“靜”重在指女子氣質之嫻雅、性格之幽靜。第三類為假借義釋,是指善女、淑女。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靜女其姝……《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靜,善也。鄭詩‘莫不靜好’,《大雅》‘籩豆靜嘉’,皆以‘靜’為‘靖’之假借,此詩‘靜女’亦當讀‘靖’,謂善女,猶云淑女、碩女也。故‘其姝’‘其孌’皆狀其美好之貌。”[5]認為“靜女”其實就是指相貌美好的淑女。第四類以“靜”為“情”之假借,當作“通情”解。證據(jù)有“靜”與“情”在古音里同屬耕部、從母,平聲,為同音字,其互通符合古音通假原則。《逸周書》卷七《官人解》篇,周公曰:“飾貌者不靜。”盧文昭校曰:“靜,《大戴》作情,古通用。《表記》:‘文而靜。’鄭云:‘靜或為情。’”《白虎通》卷三《情性》亦有云:“情者靜也。”“靜”通“情”,“靜女”實為“情女”。此說可為一解。
此女子既與男子期于城隅,且故意躲藏起來,急得男子搔頭徘徊,可見女子天性中的那份調皮與活潑。俟人于城隅的行為實在不是“能執(zhí)彤管以為誡”的女史所為;又與性格安詳、氣質嫻雅的文靜女子有異;至于貌美之說,與下文“姝”重義,不能說美麗的女子很美麗。觀察該女子行為,倒是不失為一位多情的少女。可以想象,女子看到戀人等候已久,急躁不安地走來走去,躲藏著的她心中充滿愛情的甜蜜。“靜女”實是“情女”,與情人約會在城隅,為多情女子。將“靜”解釋為“情”,想來離詩的本義不算太遠。
第二章中“彤管”有筆赤管、樂器、紅管草三解。一說,彤管為筆赤管。毛《傳》、鄭《箋》持此觀點。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鄭《箋》:“彤管,筆赤管也。”[6]《周禮·天官·女史》:“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凡后之事,以禮從。”賈公彥疏引鄭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是以掌王后禮之職事。”《左傳·定公九年》引“君子”的話說:“茍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靜女》有邪,唯“彤管”可做“無邪”的發(fā)揮。這些都是從經學禮教角度出發(fā),認為彤管是女史所持的紅色之筆,借以宣揚女德,以刺世風。一說,彤管為樂器。段玉裁引《風俗通義》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說文》:“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芽,故謂之管。從竹,官聲。”高亨《詩經今注》:“彤,紅色。管,樂器”,“彤管當是樂器,《詩經》里的管字,都是指樂管”。從當時音樂發(fā)展狀況而言,樂器說似有可能。一說,彤管為紅管草,即茅芽,與“荑”同物。“管”與“菅”同義,《說文》:“菅,茅也。從艸,官聲。”20世紀30年代的辯論中,顧頡剛認為是“紅管子”;魏建功與劉復認為是“樂器”;劉大白認為是植物,為“紅色的茅苗兒”;董作賓亦主張“管”和“荑”同物,指初生的茅芽。[7]余冠英也認為:“彤管是紅色管狀的初生之草。郭璞《游仙詩》:‘陵岡掇丹荑’,丹荑就是彤管。”[8]依此說,此章的彤管就和下章的荑同指一物。
朱熹《詩集傳》解釋:“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9]沒有指出彤管究竟為何物。《詩經》的年代距今久遠,固然不能確定“彤管”為何物,但是考慮到《詩經》重章疊唱的特點,或許它就是第三章中的“荑”,即紅管草。不然的話,就無法理解作為女史的女子為何將王宮女史之筆送人,也無法解釋女子在一次約會當中為何送給男子兩件禮物,更無法體現(xiàn)第三章與第二章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試想,第二章為男女見面,女子贈紅管草;第三章寫男子與女子分別后,手持女子所贈茅草,思念愛人之美)。
第三章中“荑”的解釋與“牧”聯(lián)系密切。或說,“荑”為茅草嫩芽,“荑”與“彤管”是同一物。毛《傳》:“荑,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終。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10]歐陽修《詩本義》:“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為美,聊貽美人以為報爾。”朱熹《詩集傳》:“荑,茅之始生者。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11]各家在“荑”為茅芽這一點上取得一致,但是關于荑之來源及送荑女子存在爭議。
這就涉及“牧”的解釋。毛《傳》:“牧,田官也。”[12]鄭《箋》釋“牧”為“牧田”。朱熹《詩集傳》:“牧,外野也。”方玉潤《詩經原始》:“牧,郊外也。”[13]《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孟子·公孫丑下》:“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注:“牧,牧地。”由“牧”的不同解釋可得三種釋義:“靜女”,或為女史,戀愛對象為“田官”;或為牧羊女,在牧田放牧,采荑送給男子;或為鄉(xiāng)間少女,在郊野采荑送給戀人。
考慮到“彤管”的解釋,竊以為還是以“牧”為“郊野”適合。試想,女子在約會情人之前,可能是在郊外勞動或者是野游,于是順手采集了茅草,打算約會時候送給男子。更何況,古代有贈白茅表示愛情婚姻的習俗,“白茅已經成了頑強生命力和旺盛繁殖能力的象征”[14],作為“茅管”的“荑”具有植物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特殊意義。這樣理解的話,于男女身份和當時環(huán)境都是合情合理的。
《靜女》主題的不同說法,和上面釋義密切相關。其一為刺時說。《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wèi)君無道,夫人無德。”鄭《箋》:“以君及夫人無德,故陳靜女貽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15]方玉潤《詩經原始》:“刺衛(wèi)宣公納伋妻也”,“城隅,即新臺地也。靜女,即宣姜也……宣姜初來,未始不靜而且姝,亦未始不執(zhí)彤管以為法。不料事變至于無禮,雖欲守彤管之誡而不能,即欲不俟諸城隅而亦不得也……(宣公)無如世間尤物殊難自舍,則未免有‘佳人難再得’之意,竟不顧惜廉恥,自取而自納之,亦‘說懌女美’之一念陷之也”。[16]諷刺了衛(wèi)宣公納兒媳為妃的好色無禮、逆理亂倫丑態(tài)。
其二為約會說。歐陽修《詩本義》:“此乃述衛(wèi)風俗男女淫奔之詩。”朱熹《詩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17]姚際恒《詩經通論》:“此刺淫之詩也。毛、鄭必反之,牽強為說,不知何意。”高亨《詩經今譯》:“詩中的主人公是個男子,抒寫他和一個姑娘甜蜜的愛情。”余冠英《詩經選》:“這詩以男子口吻寫幽期密約的樂趣。”[18]此詩為“男女相悅”“男女相贈答”“男女相與歌詠”之辭,甜蜜約會之歌,勾畫和諧愛情之美。
此外,有為人君求賢妃說。[19]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正義》:“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于君,使之有道也。”[20]也有懷才不遇說。《說苑·辨物篇》:“(賢者)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還有女史戀愛說。陳子展《詩經直解》:“《靜女》,詩人熱愛衛(wèi)宮女史之作。”均可備一說。但是,最主要的觀點還是要數(shù)前面刺時說和約會說兩種。
綜觀前代各家學說,竊以為《靜女》應為民間男女相贈之辭,是一首歡快的情歌,用男子口吻道出幽會密約的有趣情景。這首男女約會的詩既寫出了焦急的等待,又描繪了歡樂的會面,還有幸福的回味。
可以想象這樣一幅美麗畫面:在一個春天的傍晚(或許是其他時間,考慮到“人約黃昏后”,姑且設定為傍晚),癡情的男子前往城隅赴約,期盼見到心愛的女子,以訴衷腸。俏皮的女子手持從野外采集的茅草,明明已到,偏要悄悄地躲藏起來,看著男子搔頭徘徊(這大概是女子考察此男子的一種方式)。由于不忍看著戀人焦急等待,可愛的女子現(xiàn)身了,并鄭重地將茅草送給對方。男子歡樂地接過女子手中茅草,發(fā)現(xiàn)茅草赤色如女子紅顏,無限美麗。然而美好的時間總是短暫的,可是女子所贈的茅草在二者暫時分別后,延續(xù)了兩人的情意。男子回家后,看著手中的茅草,不禁想起女子的柔情,心中涌起無限美好,因為經過女子之手,連這茅草也變得“美且異”。
毫無疑問,《靜女》是一首愛情詩。我們不應該拘泥“靜”字,強解為“女德貞靜而有法度”,專從經學角度出發(fā),完全拋棄文學的眼光;也不可糾纏“彤管”之意,硬說是宮室女史戀愛之作,或是專門用來諷刺君王無德而作此詩。試著將眼光從“經”移回到“詩”本身,我們就會更好地品味詩中所含的美好感情。當《靜女》女主人公由“王宮女史”變?yōu)猷l(xiāng)間少女時,“淡化了情詩的美刺色彩,而多了民間情歌的氣息”[21],這也就回歸到詩的原始,一切也就會因其中蘊含的愛情而變得更加美好。
參考文獻
[1][2][6][10][12][15][20]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57:254-256.
[3][9][11][17]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8:26.
[4]匡鵬飛.從《靜女》看《詩經》毛亨朱熹解釋的差異[J].沈陽師范學院學報,2001(2).
[5]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9:156.
[7]陳俐.《靜女》主題辨析[J].信陽師范學院學報,2001(5).
[8][18]余冠英.詩經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33.
[13][16]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149,148.
[14]杜鳳坤.《靜女》中的“管”“荑”文化新探[J].現(xiàn)代語文,2008(9).
[19]楊合鳴,李中華.詩經主題辨析[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89.
[21]劉展.歐陽修《詩本義》“淫奔詩”說解讀——以《靜女》詩為例[J].科技信息,20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