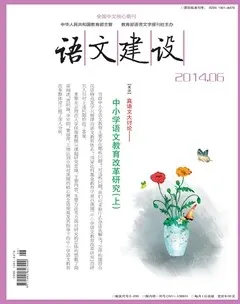傲岸的人格與“特立”的西山
《始得西山宴游記》居柳宗元“永州八記”之首,其中“頹然而醉”之“頹然”,是易為人所忽視的問題。從字面看,“頹然而醉”的意思就是“醉倒”,然而,何以“頹然”卻值得斟酌玩味。柳宗元的“頹然”,究竟是怎樣的情態(tài),其“西山宴游”中的心境又如何呢?
一、“怪特”的焦點如何得來
宴游而“頹然”,在于西山的“怪特”,這是宴游的焦點。“高山”“深林”“回溪”“幽泉”“怪石”,“凡是州山水有異態(tài)者,皆我有也”,說的是游歷的對象。“日”,每天。每天帶著一幫人,上山入林,以為窮盡“異態(tài)”,敘寫的是頻率。從時間維度看,“無遠不到”的涉獵,每天漫游的頻繁,卻“未始”有西山般的“怪特”。
于空間而言,柳宗元選擇了兩個視角,一為法華西亭遠眺,一為西山峰巔俯臨。“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所作西亭,“其高且廣”,在此觀賞山水有天高地僻之奇(《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指異”西山之“始”,即在這視野“曠焉茫焉”的法華西亭。和上述時間維度一樣,作者采用了借賓定主的襯托手法。同樣,作者在文中幾乎沒有直接摹寫西山的形勢,而是烘云托月以“培塿”來凸顯西山的“特立”。“窮山之高而止”,登臨西山之巔,山下“數(shù)州之土壤”,或“岈然”深邃,或“洼然”低凹,高下之勢盡在眼底;“尺寸千里”“莫得遁隱”,視野不可謂不闊大。“若垤若穴”,螻蟻般渺小;“攢蹙累積”,局促拘謹:包括前所謂“異態(tài)”在內(nèi)的永州山水,在西山腳下蛻為庸常。
俯臨使“怪特”得以聚焦,那么俯臨僅僅是“窮山之高而止”的基本空間使然嗎?柳宗元筆下的永州山水,有“突怒偃蹇”“爭為奇狀”的怪石(《鈷潭西小丘記》),有“顛委勢峻,蕩擊益暴”的激流(《鈷潭記》),也有令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的清潭(《至小丘西小石潭記》)。這些奇異的景象,固然有其現(xiàn)實的客觀性,但更有作者主觀視點能動性的作用,或者說是由主觀視點出發(fā)而建構的一個個心理空間整合后產(chǎn)生的藝術效果。俯臨也是一個主觀性極強的視點。且看如何俯臨。
“攀援而登,箕踞而遨”,作者登上西山之巔。
關于“箕踞”有一個著名的故事。《史記·高祖本紀》:
酈食其為監(jiān)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于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踞”,伸開兩腿而坐,因其形像箕畚,故稱“箕踞”。沛公“踞”見酈生,雖無拘無束不拘小節(jié),但待人則顯得傲慢無禮。太史公以典型的細節(jié),寫出了沛公“意豁如”的性格特點。
此時柳公的“箕踞”,亦無拘無束,“意豁如也”。只不過劉邦式的傲慢無禮,表現(xiàn)在柳宗元身上,則是阮籍“箕踞嘯歌”般的放誕不羈和超脫世俗的兀傲。置身山巔,暫時掙脫了世俗困擾,柳宗元性格中傲岸的成分得以外顯,以兀傲的態(tài)度俯臨,山下的一切自然局促而渺小。
二、“冷熱”的色調(diào)如何調(diào)配
柳宗元的絕句《江雪》寫得奇寒,然而胡應麟?yún)s以“鬧”評之。“絕”“滅”飾以“千”“萬”,足見“寒”之寥廓;“孤”“獨”于冷峭中又添了許多寂寥。無邊的寒荒,冷寂徹骨!在絕滅的虛靜中,孤寂的漁翁不畏嚴寒,篤守著人格尊嚴,彰顯著不屈的靈魂。篤守和不屈,需要何等的生命強力!這樣的冷峭中涌動著一腔熱血,滿懷著古道熱腸,極冷的色調(diào)中有熱的情懷。
與之相反,“西山宴游”寫得極熱,卻顯得頗冷。
“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三字短句,迫促急切,樂游且熱衷于山水游歷之態(tài)畢現(xiàn),但迫切中又似乎有點一旦進入余者則不管不顧的意味。故而,“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一醉方休。且“意有所極,夢亦同趣”,然則“意”為何“夢”又為何呢?罪臣“恒惴栗”的內(nèi)心恐懼是重要的因素,乃至夢中都難以掙脫。謫居五年四遭火災,瘴氣加之郁悶,罹患“痞疾”,三十多歲的盛年,卻“行則膝顫,坐則髀痹”(《與李翰林建書》),何況相依為命的母親到永州半年即病逝。也正是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致信京中親戚故舊求援,“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與李翰林建書》),其情凄惻。“意”,由一個個事件構成的心理空間疊加整合而成,輸出而入“夢”。由此觀之,不管不顧乃至決絕地投入,恰是現(xiàn)實世界諸多凄苦有憂難忘的表現(xiàn),極熱而極冷。
也許這還只是“始得”前的心理感受。西山之游的“猶不欲歸”頗值得玩味。“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是“不欲歸”的原因。這里不僅有天地境界的闊大,也有內(nèi)心舒展、自在而無拘束的灑脫,所謂“心凝形釋”也。即此,“頹然”則可視為放蕩不羈、舒展自適貌。“猶”,連接“暮色”已至的時間與“無所見”的空間,“歸”在所必然;“欲”,主觀愿望的底層是必須歸的客觀現(xiàn)實。“不欲歸”,卻只能回復到“覺而起,起而歸”的過往。“惴栗”之“恒”,不會因“始得”而斷裂。據(jù)此整合而成的心理空間自然很難說會是歡愉乃至昂揚的。
再看“箕踞”。將“數(shù)州之土壤”,至于“衽席之下”,對腳下雖“不欲歸”卻必須歸的現(xiàn)實世界的藐視并不亞于劉邦對酈食其的傲慢,只不過以兀傲的態(tài)度對待客體,固然顯示了主體生命的強力,但須以強力的姿態(tài)迎接,對手的力量亦不容忽視。胡應麟稱《江雪》“鬧”,恰恰是因為人格的堅守、理想的追求與孤獨寂寥間的糾結格斗表現(xiàn)出異乎尋常的張力。“箕踞”,正是這種張力的體現(xiàn),因而,“頹然”應該還有凄傷的味道。
三、“掙扎”的靈魂如何清洗
中國的士人或者說知識分子,他們在生命的歷程中需要解決兩個重要問題:如何對待天下與如何對待自己。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也。老子也說過:“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遭逢黨禍,不必等“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嚴詔頒下,痛苦也好,屈辱也罷,柳宗元必須冷靜下來,清洗自己的靈魂:“我”是誰?“我”何以自處?《江雪》《漁翁》就表現(xiàn)了作者在靈魂清洗中的思考,后世大家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蘇東坡的《赤壁賦》,也借山水進行著自我清洗。
柳宗元在永州寫了大量游歷吟詠山水的詩文,但對山水的喜愛卻是有限度的。他在《與李翰林建書》中寫道:
仆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肢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元和十年,柳宗元在《囚山賦》中發(fā)出“積十年莫吾省”的怨嘆與“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的浩問。山成了囚禁之地,在柳宗元的心理空間中,對山更多的是怨尤。此時“永州八記”包括被稱為“九記”的《游黃溪記》皆已完成。
與柳宗元筆下的諸多永州山水一樣,西山的“怪特”奇崛是“我”柳宗元首先發(fā)現(xiàn)的。它被棄置僻地無人知曉與“我”被貶蒙辱而無人理解是一致的;它“特立”超拔與“箕踞”兀傲的“我”是相通的。西山,不類培塿,與顥氣俱,與造物者游,卓然不群,自成高格,如此人格化的“西山”,是“我”柳宗元的寫照。在對山水的發(fā)現(xiàn)中,“我”發(fā)現(xiàn)了自己,體察到作為“人”的地位與尊嚴。作者在敘記山水中清洗著自己的靈魂。
但既然說到“清洗”,就不會沒有難以滌蕩的“層積”。宋人晁補之這樣評論《囚山賦》:“宗元謫南海久,厭山不可得而出,懷朝市不可得而復,丘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阱也,故賦《囚山》。”《江雪》之“鬧”,有“山林”“朝市”的糾結,“始得”的特立、“賢而辱于此”的幽怨、“以余故,咸以愚辱焉”的自嘲,難掩對“朝市”的企盼。這便是士人心中的天下,也是在屈辱與苦難中不肯降心辱志而努力掙扎著的靈魂的顯現(xiàn)。重入“朝市”的努力與追求——入世之心,在山林自然中進行與實踐——出世其形。“箕踞”的“我”、獨釣的漁夫、欸乃中的漁翁,疊印的是掙扎著的靈魂在清洗過程中的不同幕段。再貶柳州,柳宗元興辦學校、釋放奴婢,完成了靈魂的清洗,這是后話。
心理空間的建構,有語法、語境的作用,也有文化的壓力。“始得”而傾倒,“頹然而醉”。傲岸的人格尊嚴與“特立”的西山“冥合”相融,忘形亦忘情。然而,“僇人”的身份,“恒惴栗”的處境與心境,積淀著揮之不去的“凄傷”,難以“太上忘情”,“頹然”亦是心境。故而,“頹然”是諸多意蘊渾成而至的境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