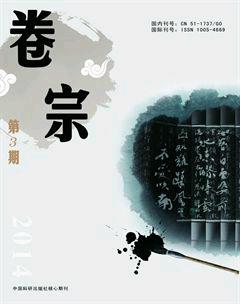探尋檢察制度的起源
韓政霖
摘 要:檢察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探尋檢察制度的起源,應當自古希臘時期和古羅馬時期。這兩個時期的政治制度為檢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文旨在通過介紹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重要政治制度,探尋檢察制度的起源。
關鍵字:古希臘時期;陪審法庭;監察官;古羅馬時期;公犯之訴
檢察制度的發展并非一蹴而就,無論是以法國為代表的將檢察權視為“準司法權”性質的國家權力的大陸法系國家檢察制度,還是以英國為首的將檢察權局限在公訴權范圍內的英美法系國家檢察制度。其發展經過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土壤培植,又經過了歐洲中世紀的進一步發展,檢察制度確立了其發展的基礎和雛形。
1 古希臘時期
在古希臘時期探尋檢察制度的起源,主要是雅典的陪審法庭以及斯巴達時期的檢察官制度,這兩種典型的古希臘時期政治制度為檢察制度的起源起到了基礎的作用。
1.1 雅典陪審法庭
在雅典,全體公民享有城邦的主權,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享有最高的權威和最后的裁斷權。雅典就是根據這一主權屬于全體公民的原則,設置國家機構的職能和運作。公民大會是雅典國家唯一的最高權力機關,全體20歲以上的男性雅典公民,無論財產多寡,都可以平等參與公民大會,而其他國家機關,如陪審法庭、五百人議事會、貴族會議等都隸屬于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是雅典國家的最高行政機關,是公民大會閉會期間行使雅典國家政府職能的常設機構。主要負責為公民大會準備議程、預審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以及執行公民大會的決議與管理日常行政事務,如監管國家財政及兵制和戰備情況,監視造械廠、造船廠,監督戰艦和港口的建造等。
陪審法庭是雅典城邦的最高司法機關和監察機關,在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我看來,雅典的陪審法庭對現代檢察制度的影響較公民大會和五百人議事會而言更加深遠。陪審法庭在當時被稱為是“民主政體的支柱”,因為陪審法庭在古代雅典時期,每年選舉一次,任期一年,并且每位雅典公民都有權參加。陪審法庭是雅典城邦最重要的司法審判機構;它可以通過受理“違憲立法起訴”對雅典城邦立法行使審查權;還有權對城邦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及各級官員實行監察。其一,雅典陪審法庭的司法權。在雅典的政治架構中,陪審法庭掌握了相當獨立的司法權能,能有效地制衡立法權和行政權。除兇殺案和少數重大的特殊案件由公民大會審判外,其他一切刑事和民事案件都由陪審法庭作出判決。眾所周知,無論是由國王代理人發展而來的法國檢察權還是英國以公訴權為主的檢察權,實際上都是司法權的一種體現,它們都具有司法機關的性質。其二,雅典陪審法庭具有行政監督和違憲審查的功能。它有權審查、監督官吏,裁決五百人議事會或公民大會的決議和議案是否違背法律等。并且,薩拜因在《政治學說史》中曾說,雅典法庭的行政監督和違憲審查的功能甚至比司法權的功能更為重要。就我國檢察機關而言,憲法對我國檢察機關的定位為法律監督機關,這一定位又是借鑒了前蘇聯國家的經驗。這說明,從古希臘雅典時期開始,陪審法庭的權能、運作方式就與現代檢察官制度存在著眾多相似之處,對后世西方檢察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斯科特·戈登所言:“雅典政治的最重要特征不是其確定國家政策的方法,而是作為一種控制政府官員的權力行使的陪審法庭制度的運用。”
1.2 斯巴達的監察官制度
斯巴達是靠征服建立的國家,它位于希臘半島南部的拉哥尼亞平原,三面環山。斯巴達國家的政體不同于古代雅典時期的民主政體,而是實行寡頭政治。它既反對個人獨裁,也就是僭主政治,又反對眾人治國,即民主政治。因為,在斯巴達人的觀念中,他們極力打造社會經濟領域的“人人皆兄弟”的平等觀念,那么,在政治體制中也就要相應地創造某種平衡的狀態。斯巴達設置國王為國家元首,但它同時有兩個國王。國王的主要職責是負責斯巴達的對外戰爭,統率軍隊出征,是戰場上的司令官,通常一王出征,另一王坐鎮國內,而率軍在外的國王身邊總有兩名監察官防止他濫用權力。元老院是最重要的權力機關,擁有實際上的創制權和決策權,同時它也是最高的審判機關,其成員擁有同等的表決權。他們可以向公民大會提出法律和其他議案,并且對于公民大會修改的有關決議,他們有權否決和中止會議。總之,元老院的作用就是使整個國家的政治活動能夠有最安全和井然有序的安排。公民大會由元老院主持,后來也由監察官主持,它由30周歲以上斯巴達男性參加,每月召開一次。與雅典公民大會不同的是,盡管其在斯巴達的政治生活中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也只是形式上的“最后的權力”。
監察官制度便是我們所說斯巴達政治制度中對后世檢察制度的建立影響最深刻的。斯巴達的監察官由普通公民選舉產生,共有五位,任期一年。監察官的當選不分貧富等級差異,代表著普通公民的利益,集監察權、司法權、立法權和軍事權于一身。監察官的監察權是對所有公民的監督權,包括國王和大小一切官吏。他們有權中止公職人員的權力,可以代表人民指控國王,甚至能逮捕或拘禁國王。監察官的司法權讓其有權審判任何違法的斯巴達公民,甚至可以不接受辯護即宣布判決,還可以不經審判處死罪犯。此外,斯巴達監察官的立法權主要體現在它是公民大會的實際召集人,控制著大會的實際程序,并且,監察官也有權向公民大會提出議案。監察官還享有一定的軍事權主要是他雖然沒有直接指揮戰爭的權力,但是卻擁有許多與之相關的權力。監察官有權制訂戰利品的分配方式,有權決定某次戰役所應征發的士兵及輔助人員的年齡,征調必需的物資,還有權宣布戰爭和媾和。斯巴達的監察官制度是一個代表平民,為平民利益的制度,在鞏固和平衡斯巴達寡頭統治方面有重要的作用,與現代檢察制度在職權和效能方面有許多契合之處,可以說是現代檢察制度的原初形態。
縱觀古希臘時期,雅典的陪審法庭和斯巴達的監察官,都為現代檢察制度奠定了基礎,為現代檢察制度的發展培植了土壤,孕育了萌芽。使得現代檢察制度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合理配置檢察權,最終達到檢察權的合理優化。
2 古羅馬時期
耶林曾在《羅馬法精神》一書中寫道“羅馬帝國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亡,宗教隨著人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縮小了影響力。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為持久的。”顯然,古羅馬時期的法律對后世法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那么對檢察制度的發展而言,古羅馬時期刑事控訴制度中的“公犯之訴”和監察官制度的影響較大。
2.1 公犯之訴
古羅馬時期的刑事控訴制度隨著其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而演變。從最初的只能由被害人本人提起訴訟,也就是以不告不理為原則的模式,轉變為對于涉及國家利益的案件,將以雙方當事人為主導的彈劾式訴訟模式轉變為以法官為主導的糾問式訴訟模式,法官由被動轉為主動。公犯之訴,也就是古羅馬時期的“公訴制度”,成為現代檢察制度中公訴制度的雛形。
在古羅馬時期,人們意識到,除了關涉私人權益的“私訴”是必要的,那些侵犯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公訴”也是必不可少的。而所謂“公犯之訴”就需要有“公訴”。“公訴”就需要能夠代表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機關或組織來承擔。在古羅馬,根據犯罪性質不同,主持“公訴”案件的主體不同。針對敵對行為的犯罪案件,由兩人審委會主持。兩人審委會在主持下,由執法官向民眾大會提出控告。雖然沒有明確的說明,執法官在當時承擔公訴的職能,但實際上當時的訴訟程序已經帶有現代檢察制度中提起公訴的性質,而執法官就是公訴機關,這里就能一定程度地體現出公訴制度的雛形在古羅馬時期的體現。隨著“公犯”與“私犯”范疇的不斷界定,“公犯”的范疇不斷擴大,執法官便逐步取代了兩人審委會主持“公犯之訴”,權力也相應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執法官依舊是向民眾會議提起訴訟,只是執行官要在民眾出席的情況下進行三次非正式預審。在經歷了三次非正式的預審后,如果執法官仍不打算放棄訴訟,那么執行官就要進行正式的預審,也就是第四次會議。執行官在正式的預審中提出控告,并提出自己的起訴書。這種訴訟方式與現代檢察制度有相似之處。那么檢察制度的起源就可以追溯至此。陪審團參與的刑事訴訟也是如此,隨著“公犯”范疇進一步擴大,一種新的普通刑事訴訟程序——刑事法庭程序應運而生。而陪審團的產生起初是因為《索賄罪法》的規定。它規定在審判索賄罪案件的時候,除了授權一名裁判官外,還應挑選一個陪審團參與審理。在古羅馬,裁判官可以允許代言人代表受侵害的羅馬市民的共同利益參與訴訟,這種代言人制度是建立公訴制度的基礎。而陪審團參與的刑事法庭程序,又是在公訴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公訴制度的建立是確立陪審團參與刑事法庭程序的關鍵。
這幾種類型的“公犯之訴”都體現了公訴制度的雛形在古羅馬時期的應用,這為現代檢察制度中的公訴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2 監察官制度
公元前443年,在平貴斗爭下產生了監察官,用來分擔執政官的部分權力。監察官最初是由于人口登記的需要設立,任期五年,但后來職權越來越大,具有很高的地位,是不負實責的最神圣的高級官職,受到高度尊重。
監察官的職責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進行公民調查。公民調查起初是對公民的姓名、年齡、住址、財產等進行登記,并確定稅額,這也是唯一根據。后來,隨著公民等級劃分越來越嚴格,對于健康狀況、公民品德、官員有無瀆職及收受賄賂、公民在戰爭中的表現等都需要調查和記錄,這一記錄在案,公民、士兵和官吏都會更自覺地規范言行,并且這一職能對防止權力濫用、提高公民整體道德水平有很大的作用。二、監督公民道德。監察官有權干涉公民中不道德的行為,還可對公民的行為做出評估。監察官每五年就會對公民做出一份“監察官評注”。公民對評價報告非常重視,也很可能會因此受到懲治,甚至喪失名譽。總之,監察官的總體職能就是監督。于現代檢察制度而言,與現代國家的反貪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有許多相似之處,對羅馬道德腐化有抑制作用,對于權力制衡也有重要作用。
古羅馬的監察官制度從不同方面起到監督制約的作用,對后代檢察制度的形成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并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何勤華, 張進德, 鄧繼好. 檢察制度史[M]. 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9.
[2]周枏. 羅馬法原論[M].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