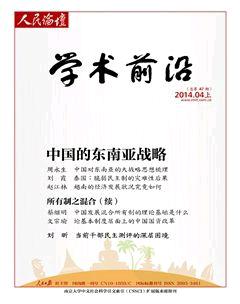東盟國家的戰略兩難與中國之對策
胡必亮+葛成
【摘要】伴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實施,日本和菲律賓與美國密切配合,越南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緬甸成為西方國家的拉攏對象, 印度乘機推進其“向東”政策,歐盟和俄羅斯也開始將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美國和歐盟更是加快了推進TPP和TTIP談判步伐。中日韓自貿區談判、中韓自貿區談判、東盟主導的“10+3”和“10+6”自貿區談判乃至“10+1”自貿協定現在看來都有可能出現不確定性。中國與東盟經濟關系總體良好,但投資形勢卻不容樂觀,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受融資規模和缺乏政策引導等因素限制, 發展相對遲緩。中國此時應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采取一系列有效的財政政策引導民間資本充分融入中國—東盟經濟整合進程之中,為對沖與化解目前東盟可能出現的變局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中國—東盟關系 財政政策 民營中小企業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標識碼】A
自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與東盟全面恢復外交關系以來,雙邊關系發展迅速。1991年,中國與東盟開啟對話進程;1997年,雙方建立睦鄰互信伙伴關系;2003年,雙方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中國作為域外大國率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多年來,中國與東盟政治互信不斷增強,經濟合作成效顯著,各領域合作持續拓展。中國—東盟合作已成為中國周邊外交一大亮點。至2013年,中國已經坐穩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位置,雙邊貿易額達到4400億美元。
然而,在快速發展的背后,中國與東盟關系在近些年來也面臨著嚴峻挑戰。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世界各主要大國,特別是美國、日本、印度等加緊調整其東亞及亞太地區戰略。美國自2010年起強勢推進“亞太再平衡”,并在經貿領域拋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以下簡稱TPP);日本在安倍政權上臺后,加速“右傾”,接連在釣魚島問題、歷史問題以及教科書問題上拋出挑釁言行,并著手策劃對中國的外交圍堵;同時,印度也不甘落后,其“東向”(Look East)戰略已經涵蓋東亞及西太平洋地區,并與日本及澳大利亞等國加強合作,對中國崛起多有防范。出于各自不同的戰略需要,這些國家均無一例外地加強自身與東盟的經貿、政治與安全聯系,在各個領域拉攏甚至分化東盟各成員國,旨在中國周邊制造反華“包圍圈”。因此,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鞏固中國與東盟業已存在的緊密聯系,成為中國整體國家戰略的重要課題之一。
中國—東盟關系正處于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
2010年10月,以“中國—東盟”實現和平與繁榮戰略伙伴關系行動計劃(2011~2015年)聯合宣言的簽署為標志,雙邊關系發展達到歷史高峰。在經濟方面,五年計劃明確地提出了支持國家級和次國家級的經濟、貿易和商業合作,以及更深層次的金融及跨行業合作與交流。實際上,許多列入計劃的項目已經處于開發階段,而且一些議題也被限制在討論范圍以外(如南海問題),行動計劃的規模與范圍充分地反映出雙方經貿聯系的高水平,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未來關系發展的信心。
2013年10月9日,李克強總理在文萊出席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其所闡述的中國—東盟“2+7合作框架”成為會議的點睛之筆。李克強總理指出,中國與東盟要以長遠眼光看待彼此關系,凝聚兩點政治共識和加強七個領域的合作,使今后10年雙方合作朝著寬領域、深層次、高水平方向發展。①
中國與東盟過去10年的交往被國際社會稱為“黃金10年”。中國將東盟作為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雙方政治互信、經濟互惠、睦鄰友好,共同筑牢了中國—東盟關系穩固的堤壩,成功地抵御了各種風浪的侵擾。站在新10年的起點上,中國與東盟關系迎來開啟未來的“鉆石10年”的新機遇。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演講時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將與東盟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②
然而,隨著中國在東亞地區的快速崛起,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都開始紛紛調整其亞太戰略,對中國加以防范甚至圍堵,這從客觀上對中國與東盟關系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這其中又以美國主導的TPP談判進程以及日本安倍政權對中國的圍堵最為顯著。
TPP對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構成直接挑戰。2009年底,美國正式推出TPP計劃,并全方位主導談判進程。2013年7月,日本在歷經反復之后,正式加入TPP計劃中與馬來西亞舉行的第18輪談判。日本的加入,使TPP談判參與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之和達到26~27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總量的近40%,貿易額占全球貿易總額的約30%。TPP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競爭”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TPP采取閉門磋商的方式,對其談判內容始終諱莫如深。從談判初始,參與談判的各方代表便負有保密義務,談判結束前不對外公布技術文本,以至于眾多媒體報道和學術評論都只能推測其談判內容與主要議題。從已經公布的概念文件可以看出,TPP試圖突破傳統自由貿易協議(FTA)模式,達成亞太地區迄今為止標準最高、覆蓋最廣的經貿一體化協議。如果其目標順利實現,將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在TPP出臺前的10余年間,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進展迅速,形成了“10+1”、“10+3”、“10+6”等經貿合作機制,并且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逐漸取代日本成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核心力量。同時,專注于反恐戰爭的美國在區域內的貿易份額持續減少,面臨著被排除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之外的窘境。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亟需更深入地參與到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經濟體系中,以保證其國內經濟的復蘇、增加就業機會并鞏固其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和其對亞太政治、經濟、安全秩序領導者的地位,同時稀釋乃至瓦解中國在該地區逐漸增強的影響力。
結合奧巴馬政府“重返亞太”的戰略部署,TPP在美國全球經貿戰略結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由于TPP成員國在經濟、政治、安全等領域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很大,因此美國主導談判進程的阻力甚小。在推進TPP談判進程這個問題上,美國的決心不應該受到懷疑。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亞太地區在國際格局中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重要;二是奧巴馬政府執政5年多來,其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在國內受到重重阻力,譬如說,他推行的加強金融監管(規范華爾街)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重振制造業的結果也不顯著,依靠“5年出口倍增”計劃而試圖實現200萬新增就業崗位的任務也難以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對外經濟合作與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愈發不容有失。由此可見,奧巴馬政府很可能在剩余近3年任期內,加快推進TPP承諾早日兌現。endprint
美國從未對主導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意圖加以掩飾。在TPP概念文件“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中,美國明確了其TPP戰略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促進美國出口,增進美國就業”(Increasing American Exports, Supporting American Jobs),并強調美國將致力于達成一個強有力的協議,以回應美國商界和工會在21世紀的重大關切。③事實上,大多數東亞國家或地區(包括日本、“四小龍”、“四小虎”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崛起,莫不與這些國家或地區與美國的經濟聯系(主要是貨物貿易)密切相關。美國仍然是整個東亞(中日韓和東盟)最重要的區外經濟合作伙伴,也是東亞地區3個發達國家(日、韓、新加坡)共同的同盟國。在新興經濟體目前普遍出現經濟增長乏力、“南南貿易”逐漸萎縮的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反而出現了加速復蘇的情景,于是東亞國家增強對美經濟聯系的愿望變得更加迫切起來。就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當美國推出由自己主導的TPP計劃時,馬上就吸引了一批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緊密追隨。
日本延伸至東盟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在第一次出任首相期間,安倍便十分青睞谷內正太郎從美國引進的“自由與繁榮之弧”路線。這一路線主張日本應該在“自由、民主主義及法律支配的普遍價值的基礎上,明確自己的主張與主見”,日本國內稱之為“價值觀外交”。谷內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高出中國一頭,在經濟上日益落后于中國的情況下,通過強調價值觀而使日本在外交上增加一些信心。然而,對于當年日本明確地使用價值觀概念來孤立中國的策略,西方國家并未給予積極回應。況且日本本身在安倍第一次執政期間也同時提出了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系”的概念,因此對中國的第一次“圍堵計劃”無果而終。
2012年底,安倍在其第二次就任內閣首相的當晚,便將已經從外務省退休的谷內正太郎重新調入內閣任內閣官房參與,安排其直接向外務省發布外交指令。對于時隔6年重新擔任首相的安倍來說,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已經從預計變成了現實,這在客觀上加劇了其再次利用“自由與繁榮之弧”概念來“圍堵中國”的戰略欲望。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及其內閣較其前任相比,更加強了與東盟國家的接觸。2013年新年剛過,時任副首相麻生太郎便訪問緬甸,大方地將緬甸拖欠日本的3000億日元債務一筆勾銷,同時還慷慨地向緬甸提供了500億日元的貼息貸款。至于剛剛擺脫軍政統治的緬甸是否與日本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則完全不需商榷,只要緬甸成為自己的朋友就行了,這樣就可以在“自由與繁榮之弧”棋局中落下第一粒棋子。此后,日本在菲律賓、越南等國也表現積極,通過貿易與投資合作、技術經濟援助等方式,彰顯自己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存在,并試圖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東盟國家的戰略“兩難”
自成立以來,東盟國家大多堅持奉行大國平衡戰略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形成了獨特的外交和戰略文化,被譽為“東盟方式”。在長期的對外交往實踐中,東盟國家認識到,只有發揮中小國家集團的“智慧”,巧妙實施大國平衡戰略,才能最大限度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繁榮。
東盟的大國平衡戰略,至少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在宏觀層次上與各大國盡力保持均衡外交態勢,避免過于倚重某一大國,從而淪為其附庸和“槍手”。二是在中觀和微觀層次上,不排斥與某一大國拉近關系,但最終目的并不是倒向某一大國的懷抱,而是借助其影響力,制約和威懾另一大國,最終維持與各大國之間的等距離外交。同時,東盟國家始終堅持在地區合作中發揮核心主導作用,力求突出自己的特色,不愿淪為大國的陪襯。東盟成員國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提出了“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設想。1997年底,東盟倡議并舉辦了第一屆“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峰會”,開啟了“10+3”機制。此后10年余間,東盟逐步營造了以東盟為核心、以“10+3”、“10+1”、“10+6”(東盟—中日韓+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機制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合作體系。
經過40年艱難探索,東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也面臨著新世紀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在美日等國加緊拉攏甚至分化東盟各國、進而對中國形成“圍堵”的情況下,東盟面臨著自成立以來最困難的“兩難”選擇。對于東盟各國而言,對外期望在于保持政治獨立、強化安全環境、獲得經濟發展這三項之間的均衡發展。但在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日本推動“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的雙重壓力下,東盟不得不面對經濟上更加依賴中國,但在政治安全領域更加偏向美日的“兩難”困境。
問題在于,除了個別和中國存在主權爭端的國家外,東盟大多數國家并不情愿、也不愿意進行這種“二選一”或“挑邊站”的選擇。在美國拋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后,不論是和中國關系比較密切的柬埔寨,還是美國老牌盟友菲律賓,甚至和奧巴馬“沾親帶故”的印尼,都或直接、或委婉地表達了“不希望中美對抗”、“東盟想和各方發展友好關系”的良好愿望。2012年東亞峰會期間,東盟各國宣布達成了“不使南海爭端國際化”的共識,并將把注意力集中在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架構機制上。
從客觀上講,東盟各成員國正面臨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社會轉型期矛盾突出的嚴峻挑戰。近年來,新加坡、馬來西亞經濟受中國、印度經濟快速發展的帶動,保持了比較快速的經濟增長,但也面臨著對外依存度過高、國際競爭力下降、發展后勁不足等問題,因此提出了發展知識經濟和“多媒體走廊”的計劃。泰國實施“他信經濟”多年,經濟表現頗為不俗,但2006年以來的軍事政變激化了各種矛盾,導致了國內政局的動蕩不安,經濟發展也被迫進入調整期。印尼、菲律賓則長期以來都表現出典型的“有增長、無發展”的情況,外資流入不斷減少,經濟增長乏力。越南、老撾、柬埔寨近年來保持了比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它們都還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初期階段,基礎設施建設仍然比較薄弱,經濟增長仍不穩定,社會矛盾與沖突仍然比較嚴重。endprint
因此,除菲律賓等個別國家外,東盟各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仍然是希望與該區域外的大國“交朋友”,繼續著力促進其經濟發展,至少目前是這樣的。譬如說,東盟國家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系,主要是需要美國的市場和資金,同時也希望美國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話語權對東盟有用;東盟國家很愿意與中國加強聯系,因為東盟的經濟結構與中國具有很好的互補性,雙方都能從中得到好處,同時還因為中國既愿意又有能力為東盟各國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所需的資金、技術、人才等;東盟國家也愿意結交日本,因為在上世紀70年代后的“雁陣經濟”理論主導下,東盟多個國家和日本形成了密切的產業之間的上下游關系。
正因為如此,不論是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還是日本推行“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都能夠起到鞏固和強化這兩個國家與東盟之間的關系的作用,而且能使東盟的優勢更加顯著,這自然對東盟而言是好事。但是,倘若美國和日本意在“獨占”東盟地區而試圖將其他經濟體、特別是企圖將中國從該地區排擠出去,這就不符合東盟長期以來所秉承的大國平衡戰略了,問題就出現了,而且問題還比較嚴重和尖銳。
對于多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東盟各國而言,其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期望首先是市場容量,其次是投資來源,第三則是適當進口自己急需而又負擔得起的關鍵產品、設備和技術。總體而言,中、美、日等大經濟體都符合東盟國家的“三要素”期望,但又都各有短板——中國在高科技產業領域尚不成熟,日本國內市場狹隘,美國自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升級,且對海外投資的意愿尤其對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意愿不高。因此,和三家對等發展友好經濟合作關系,可以做到擇利避害,是東盟各國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戰后屢受金融風暴沖擊的東盟各國痛定思痛后的必然抉擇。美國和東盟各國談合作、促雙贏,應該是很受歡迎的,如這些國家對于希拉里在澳大利亞所說的話就持歡迎態度,那就是“太平洋足夠寬”,可以容納下美、中和各國。但如果讓東盟各國在中、美、日中做“三選一”或“二選一”的選擇題,實際上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是不愿意的,也不敢有所得罪,因此就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這就是東盟目前所處的困境。
堅持以經濟合作為中心,推動中國—東盟關系持續發展
目前,“中國—東盟”雙邊貿易額已經從1997年的223億美元增長到4400億美元(2013年),這種經貿聯系的快速擴張反映出中國與東盟經濟之間高度的互補性:東南亞國家偏重于提供資源類產品和半成品,而中國則更加偏重于工業制成品。支持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是一系列以促進中國深化與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為目標的雙邊和多邊經貿聯系機制。其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有兩項:一是清邁倡議以及由此發展而來的多邊協商體系,二是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當然,目前“中國—東盟”經濟關系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譬如說投資領域進展相對遲緩、制度建設不太完備,等等。
清邁倡議及其發展。清邁倡議(CMI)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關于如何確保該地區內各國以后免受類似金融風暴沖擊的討論。雖然它最初是與亞洲貨幣基金(AMF)議案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然而后者的爭議性導致了其發展停滯不前,但清邁倡議卻引起人們的普遍興趣。清邁倡議設計了一個“雙邊貨幣互換和貨幣回購協議運行機制,并使其在東盟國家以及中、日、韓三國間構成完整網絡”。④清邁倡議的目標可以大致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擴大和加深雙邊互換的規模與層次,以便在某個經濟體面臨類似危機時可以獲得充足的資金供應;第二,確保在資本流動方面的信息共享;第三,將金融合作機制確定為現存區域合作機制的補充;第四,加強區域內各經濟體對經濟動蕩的監測工作,建立預警體系⑤。作為清邁倡議的一部分,東盟貨幣互換協議的融資額度從先前的2億美元擴大到了2000年的10億美元,并在2005年進一步增加到了20億美元。該協議的關鍵在于中日韓三國。2002年,三國給予該協議的融資額度為200億美元,并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擴大到了335億美元。到2009年,雙邊互換協議全部可使用金額已經達到900億美元。⑥
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雖然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聯系歷史久遠,但長期以來都缺乏一個既能促成雙方實現短期利益最大化、又能保證雙邊關系持久發展的基礎。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正式啟動,作為類似協定中覆蓋市場最大的一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覆蓋19億人口,區內合計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萬億美元(2013年)。在2010年的頭9個月中,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總量上升了44%,達到2110億美元。據預測,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總額將于2015年突破5000億美元關口。雖然東盟仍屈居歐盟、美國、日本之后,位列中國外貿伙伴第四位,但中國自2009年以來已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對東盟經濟發展發揮著重要影響。根據估算,自2000年提出自貿區議案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正式啟動,東盟經濟獲益大約為16240億美元,中國也從中獲益5170億美元。⑦根據李克強總理在“中國—東盟峰會”期間的講話,中國甚至希望通過“鉆石10年”的發展,在2020年把雙邊貿易總額推上萬億美元大關。
雙邊投資發展相對滯后。長期以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投資發展落后于貿易發展。事實上,中國至今仍不是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投資者。2010年,在東南亞的主要投資者當中,占據前四位的分別是:歐盟,占18.3%;日本,占13.4%;東盟內部投資,占11.2%;美國,占8.5%。⑧眾所周知,前幾年日本、美國和歐洲均陷入了比較嚴重的金融危機,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增加了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并在這一指標上遙遙領先于中國。
為了盡快改進這方面的工作,加快促進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發展,2009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宣布創建“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CAIF)。作為一個鼓勵中國企業到東南亞開展投資業務的平臺,“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以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能源開發作為重點,在滿足中國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加強其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很顯然,我們目前對CAIF運行機制的有效性做出任何評價都仍顯得為時過早,但CAIF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于,它的關注重點與該地區的投資模式并不匹配:東盟地區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是服務業,其次是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與能源產業位居末席,但該基金明確提出了它的投資重點集中于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和自然資源領域。此外,依據該基金單筆業務5000萬美元至1.5億美元的投資規模,這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對于那些希望投資于東盟國家服務業領域的中國民營企業顯然缺乏吸引力。endprint
經濟合作的制度建設比較缺失。總體而言,目前的中國—東盟經濟關系的基本制度仍然是很不完備的。雖然已有越來越多的意見認為以經濟聯系為基礎建立戰略同盟是可行的,但這一同盟在性質上卻只能是短期或中期的。前面提到的“早期收獲項目”的結果證明,盡管政治意愿可以在初始階段決定貿易的流向,但最終指導貿易的只會是經濟運行的自然結果。這一點在中國與印尼的經濟交往中已現端倪。獲益于早期收獲項目以及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兩國間的貿易經歷了十分明顯的快速增長。然而,貿易平衡只在協議運行的初始階段得到了保持,其后就迅速地發展到只是對中國愈加有利。換句話說,盡管中國確實抱有支持東南亞國家搞經濟建設的意愿,但市場運行的規律最終會重新調整雙方的經濟關系。進一步而言,考慮到東亞地區現存的主權糾紛與信任缺失,因此社會與政治矛盾也很容易就會給經濟合作造成阻礙。這些干擾和破壞直接削弱了區域整體的合作計劃,也就使得其他的替代方案變得更加有吸引力了。
相反,投資活動(需要資本的逐步積累而非僅僅是銷售產品)的本質是長期性的,意味著其必須以更緊密和更長期的穩定合作為基礎。在這一方面,中國在東南亞的支配力量遠遜于其貿易所發揮的作用。盡管在某些領域,譬如說在資源開發與利用領域,中國對這一地區的投資正在增加,但這樣的產業目前在該地區的全部經濟活動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缺乏大額投資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就擁有了更大空間來拓展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更為深入和更為長期的伙伴關系。對中國來說,貿易一直以來都是構成區域合作的主要手段;但對大多數其他國家來說,投資往往都是與貿易并重的。因此,雖然過去中國曾依靠貿易發展以及締結貿易協定獲得了自己在東南亞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但這一地位卻時刻受到國內環境、雙邊關系、其他貿易伙伴的壓力等因素變化的影響而充滿了比較大的不確定性。
啟動財政政策,鞏固并發展中國與東盟間密切的經濟關系
目前,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在政府層面獲得了快速發展,雙方在基礎設施、能源和資源類項目開發中的合作比較密切。但從民間投資領域來看,由于融資規模有限以及缺乏政策引導,發展相對遲緩。具體表現在:第一,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導和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重復性和無序競爭;第二,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缺乏對東盟投資環境、政策、法律等方面的了解,同時東盟各國對中國民營企業的了解和信息溝通與交流也不夠;第三,許多民營企業在認識上也存在誤區,短期行為比較嚴重,譬如說,許多企業認為東盟4個新成員國都比較落后,對商品的要求不高,于是就大量地向這些國家出口積壓商品,導致這些國家的消費者對中國商品質量形成了十分差的印象;第四,一些企業沒有制定整體投資戰略和行業規劃,也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和行業導向,投資的隨意性很大;第五,民營中小企業融資渠道一般都比較狹窄,嚴重地阻礙了其對東盟的投資能力。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快速出手,盡可能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與措施,首先是要穩定好中國與東盟的經濟關系,同時還要力爭改進和加強這種聯系。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更加充分地利用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營資本投資東盟的引導,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加強對進入東盟各國的企業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實行窗口指導,進一步挖掘民營資本在促進我國與東盟各國經濟發展方面的潛力。借鑒美國、歐盟等的相關做法,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具體的政策建議:
設立主要針對民營企業的“中國—東盟中小企業援助基金”,支持中國民營企業更多更好地在東盟進行投資布局。從地緣環境來看,東盟是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最合適的起點,是全球南南合作的典型地區。東盟和中國緊密相鄰,經濟結構既有相似之處,又有很強的互補性(特別是在資源稟賦方面),加上文化上較為相通,尤其在中南半島(包括越、老、緬、柬、泰國及馬來西亞)地區,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從目前的發展勢頭來看,如果我們假設美國和日本目前所實施的各方面“干擾”不會對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產生重要的不利影響的話,中國對東盟的投資規模會越來越大。此外,東盟是世界第六大經濟體,這一地區人口超過6億,其中一半以上都在30歲以下。因此,東盟地區應該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戰略之地。
目前,“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CAIF)已經開始運行,但其固有缺陷使得民營中小企業難以從中獲得支持。如果我們能夠設立一個類似的但專門針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新基金,就可以彌補目前這一基金的缺失,有利于促進“中國—東盟”雙邊投資的更快發展,尤其是有助于擴大民間資本投資的交流與發展。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建議這個基金主要用于幫助民營中小企業了解東南亞市場信息、對當地市場進行實地考察、舉辦展覽會、從事營銷咨詢等,更進一步地開拓東南亞市場;另外,也可以用這一基金對民營中小企業在東南亞市場上所從事的研發、技術創新與職業培訓以及從本地市場選聘專業人才進行適當補貼;如果民營中小企業遭受到了不可預測的災難,也可以從這一基金中獲得補償;對于那些適應東盟市場需要進行結構調整的企業,適度通過此基金來支持其從事這樣的結構調整工作;等等。
由中央財政設立“中小企業投資東盟周轉金”。這個“周轉金”主要是對那些初次進入東盟市場的民營中小企業進行支持,資金到期歸還,可以不付利息。如果到期虧損無法歸還,則周轉金可以沖減部分虧損(一般只是沖減少部分虧損,大部分虧損仍然應由企業自己承擔)。對于所有投資于東盟各國的民營中小企業而言,中央財政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給予一定的投資補貼。對于那些實力比較強的、與東南亞有密切聯系的企業而言,政府可以支持其發行企業債券,并可拿出一定的資金來認購這些債券。也可以由財政出資建立專門的“東盟貿易信貸計劃”或者建立一個專門的“東盟貿易信用保證基金”。當然,不論是信貸計劃,還是保證基金,其目的都是為從事與東盟國家相關的貿易提供信貸擔保。
設立財政專項貼息貸款,進一步擴大中國民營企業對東盟國家的出口。通過有選擇的財政貼息貸款發放,一方面可以實現財政的“杠桿”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投資東盟的企業、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實施有效的政策引導。具體來說:一是可以用很少的財政資金吸引大量的社會資本進入到我們希望鼓勵發展的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方向;二是通過優先項目的選擇,引導那些更具競爭力的企業優先進入我們希望鼓勵發展的東盟的重點行業領域,避免盲目投資以及重復建設;三是通過貸款項目的后期監管,保證在東盟投資的中國企業加強產品質量管理,在整個東南亞地區樹立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良好形象。endprint
對從事與東南亞市場經營有關的經營活動根據具體情況實行適當的稅收優惠政策。例如,可以考慮對所有投資于東南亞市場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提高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同時實行所得稅減半征收的政策。
加強對布局東盟的中國“走出去”企業的窗口指導。在財政支持的專項基金以及專項貼息貸款項目下,可以給那些有意愿布局東盟的中國企業提供窗口指導。窗口指導原本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勸告和建議來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一種溫和的、非強制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是一種勸諭式監管手段。對于專項基金和專項貼息貸款項目下的窗口指導而言,我們認為仍然具有同樣的意義,即同樣具有對投資東盟的企業進行勸告和建議的含義,主要形式是通過基金和貸款監管機構向企業解釋說明相關的政策意圖,并提出相應的指導性意見與建議,或者根據監管信息向企業提示投資風險等。
加大力度支持民間資本對次區域合作領域的投資開發。次區域經濟合作是相對于區域經濟合作而言的,指若干國家接壤地區之間的跨國界的自然人或法人,通過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而開展的比較長期的經濟協作活動,主要表現為在這個地緣范圍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一體化。中國和東盟的次區域合作已經具有較長的歷史了,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時也在一些具體開發項目上存在一定的問題。
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為例,這一項目于1992年由亞洲開發銀行發起,涉及流域內的6個國家(中國、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旨在通過加強各成員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次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客觀地講,GMS是一個在平等、互信、互利基礎上,實現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聯合自強的區域合作機制,也是一個通過加強區域經濟聯系而促進次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務實合作機制。但是,自成立20多年來,GMS在(地方)政府合作層面投入較多,而民間資本加入這一機制的程度很低。究其原因,與民營企業投資東盟的問題如出一轍,同樣集中在缺乏政策引導以及融資渠道狹窄上面。因此,通過財政手段提供支持,也能給民間資本充分融入中國與東盟次區域合作起到促進作用。
由于我國的廣西和云南分別與東盟的有些國家如越南、老撾、緬甸等接壤,中央財政也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方式支持廣西和云南從區域發展層面推進這兩個省(區)與東盟鄰國更深層次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中央財政要與有關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實行密切配合,聯合開展前期調查研究工作、實施有效監管,以保證所出臺的各項財政支持政策都取得盡可能好的效果。
注釋
《李克強在第16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10/c_125503937.htm,2013年10月10日。
《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17591652.htm,2013年10月3日。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ENHANC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SUPPORTING JOB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UTLINES OF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November 12, 2011, 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fact-sheets/2011/november/outlines-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
ASEAN,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of the 11th ASEAN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Chiang Mai, Thailand, 5 April 2007", http://www.asean.org/communities/asean-economic-community/item/joint-ministerial-statement-of-the-11th-asean-finance-ministers-meeting-chiang-mai-thailand-5 april-2007.
陳凌嵐、沈紅芳:《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深化:從“清邁倡議”到“清邁倡議多邊化”》,《東南亞縱橫》,2011年第5期。
ASEAN, ASEAN statistical Year Book 2010, http://www.asean.org/images/archive/documents/asean_statistical_2010.pdf.
Thitapha Wattanapruttipaisan: "Watching Brief on China and ASEAN, Part Two: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ASEAN", ASEAN staff paper, http://www.asean.org/news/item/watching-brief-on-china-and-asean-part-two-risks-and-opportunities-for-asean-by-thitapha-wattanapruttipaisan.
ASEAN, ASEAN Economic Chart Book 2010, http://www.asean.org/images/archive/documents/AEC-Chartbook-2010.pdf.
責 編/鄭韶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