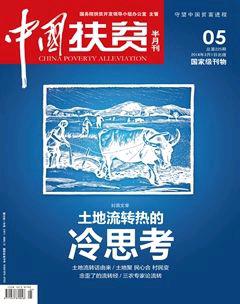念歪了的流轉(zhuǎn)經(jīng)
土地流轉(zhuǎn),是廣大農(nóng)民的自發(fā)行為,是生產(chǎn)要素的重新整合,是農(nóng)業(yè)集約化的關(guān)鍵,是促進(jìn)城鄉(xiāng)一體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在風(fēng)起云涌的土地流轉(zhuǎn)熱潮中,種種亂象也漸欲迷人眼。
土地流入易 產(chǎn)業(yè)轉(zhuǎn)活難
2013年5月9日,在山東省棗莊市領(lǐng)導(dǎo)考察后的一個多月,身背1090畝土地流轉(zhuǎn)抵押貸款的“山東省優(yōu)秀誠信農(nóng)村經(jīng)紀(jì)人”邵長寶跑路了。
2005年,邵長寶成立了銀苗兔業(yè)。2012年初,棗莊被劃定為農(nóng)業(yè)部的24個農(nóng)村改革試驗(yàn)區(qū)之一,主要擔(dān)負(fù)農(nóng)村土地使用產(chǎn)權(quán)制度改革試點(diǎn)任務(wù),探索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權(quán)抵押貸款。之后不久,從無大規(guī)模種植經(jīng)驗(yàn)的邵長寶成立了 “銀苗糧食種植專業(yè)合作社”,自任理事長并實(shí)際一人控制合作社業(yè)務(wù),在2012年6月間流轉(zhuǎn)土地1600多畝。邵長寶給出的土地流轉(zhuǎn)條件十分豐厚:每年“芒種”前后支付每畝租金1000元,村里人到他的兔子廠和地里打工,給出日工資50—80元,賣力的員工還能得到印有“銀苗兔業(yè)”標(biāo)志的電動車一部。
2013年2月,以“左手保右手”的方式,邵長寶以銀苗兔業(yè)作為銀苗糧食種植專業(yè)合作社的擔(dān)保,順利拿到嶧城區(qū)農(nóng)村信用社的300萬元土地流轉(zhuǎn)抵押貸款。但因種植失敗,在頭一年被評為“山東省優(yōu)秀誠信農(nóng)村經(jīng)紀(jì)人”的邵長寶,在第二年卻成了當(dāng)?shù)亓鬓D(zhuǎn)土地抵押貸款的“跑路第一人”。留在他身后的,是80萬元的農(nóng)民工資和300萬元的土地融資債務(wù),以及被扣押在銀行的金陵寺村1000多畝土地使用權(quán)證。
這一案例中,有兩點(diǎn)值得質(zhì)疑:
一:在利用土地抵押貸款之前,邵長寶已有200萬元銀行欠款,但首次資質(zhì)審批竟然通過,這說明,信用社、經(jīng)管站、村干部、融資擔(dān)保公司都未能把好資質(zhì)審核關(guān)。
二:邵長寶利用由妻子任法人的“銀苗兔業(yè)”擔(dān)保自己欲申請貸款的“銀苗糧食”,本身就不合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金陵寺村多位村民表示,盡管盼望再有人來流轉(zhuǎn)土地,但他們再也不敢只收一年租金了,“起碼一次給足三年五年”是村民的共識,而這無疑會大大占用后來接手者的流動資金,疊加還要為邵長寶償還300萬元債務(wù),以及債務(wù)還清前該村土地不能像棗莊其他農(nóng)村土地一樣流轉(zhuǎn)后申請抵押貸款的因素,金陵寺村土地的再次流轉(zhuǎn),顯然困難更大、機(jī)會渺茫。
比山東棗莊的邵長寶跑路案件動靜更大的,是湖南省長沙縣烜赫一時(shí)的圣毅園農(nóng)莊。之前做房地產(chǎn)生意致富的湖南長沙縣人周猷庚,于2008年簽訂土地流轉(zhuǎn)面積達(dá)1萬畝,平整耕地8100畝,2009年被長沙市政府列為“長沙市農(nóng)村土地流轉(zhuǎn)綜合配套改革示范點(diǎn)”。
周猷庚1萬畝土地的流轉(zhuǎn)期限為18年,流轉(zhuǎn)價(jià)以稻谷650市斤/畝標(biāo)準(zhǔn)折合當(dāng)年市場收購價(jià)支付。但好景不長,因管理跟不過來,資金出現(xiàn)瓶頸,2011年即陷入困境,難以為繼。把土地流轉(zhuǎn)出去、在農(nóng)莊打工的農(nóng)民因無法領(lǐng)到工資,在“問政湖南”網(wǎng)站上給鎮(zhèn)政府留言尋求解決,但鎮(zhèn)政府給出的答復(fù)也只能是:“至于農(nóng)民工資,確因企業(yè)資金周轉(zhuǎn)困難而暫未支付,政府支持你們以合理、合法途徑索要工資。”
周猷庚的農(nóng)田整理是高標(biāo)準(zhǔn)的,并給當(dāng)?shù)氐拇迩f環(huán)境帶來了明顯變化,一開始很受當(dāng)?shù)卮迕駳g迎。正是因?yàn)檫@些原因,在他失敗后,依然有當(dāng)?shù)卮迕駪涯钏5珶o論如何,不懂農(nóng)業(yè)的他憑著一腔熱血投身這個風(fēng)險(xiǎn)極大而脆弱的產(chǎn)業(yè),還是使自己血本無歸,也使打工的村民拿不到血汗錢。
對于周猷庚的失敗,一名長沙縣的農(nóng)業(yè)部門負(fù)責(zé)人尖銳地指出周的不足,“因?yàn)樗欠康禺a(chǎn)出身,對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經(jīng)驗(yàn)不多,無法預(yù)知具體的風(fēng)險(xiǎn)。”
土地流轉(zhuǎn)易,產(chǎn)業(yè)轉(zhuǎn)活難。這些投資農(nóng)業(yè)失敗的案例,給那些急匆匆要去農(nóng)村大賺一把的投機(jī)者和興沖沖要去農(nóng)村創(chuàng)業(yè)的投資者潑了盆涼水:做農(nóng)業(yè),急不得。從農(nóng)業(yè)上賺錢,沒那么容易。周猷庚曾經(jīng)說,他也知道做農(nóng)業(yè)風(fēng)險(xiǎn)大,但他準(zhǔn)備用60%的資金發(fā)展農(nóng)業(yè),40%的資金發(fā)展房地產(chǎn),用房地產(chǎn)來補(bǔ)貼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試問,這種東墻補(bǔ)西墻的補(bǔ)貼,能堅(jiān)持多久?
邵長寶和周猷庚的流轉(zhuǎn)初衷,我們不得而知。他們究竟是“為融資而圈地”,還是“為生產(chǎn)而流轉(zhuǎn)”,對于這兩種結(jié)果相似、初衷殊異的行為,地方政府理應(yīng)加強(qiáng)甄別,萬不可為追求政績而放松警惕,致使政績成為敗績。
狼狽為奸 農(nóng)民遭難
2008年的最后一周,河南上蔡縣農(nóng)戶張保國的養(yǎng)鴨場連續(xù)遭到數(shù)次襲擊,“十幾號人手拿鐵锨、大錘,見墻就砸,見房就拆;我們上去勸止,這些人沖我們喊:‘我們都有艾滋病啊,碰著哪兒了,莫怪我們!”
上蔡氣候比較溫和,適合發(fā)展養(yǎng)殖業(yè)。在農(nóng)業(yè)、畜產(chǎn)部門的支持下,上蔡有不少農(nóng)戶通過自愿流轉(zhuǎn)的方式,租用鄰近村組的土地搞養(yǎng)殖,成為當(dāng)?shù)剞r(nóng)民脫貧致富的一條捷徑。但因這里地段好,發(fā)展住宅樓升值潛力大,當(dāng)?shù)卣氵B哄帶騙,誘使不少村民以每畝22500元的價(jià)格轉(zhuǎn)讓了自己的承包地。張保國、吳俊良等一些養(yǎng)殖戶不愿簽字,遭遇了野蠻拆遷。
“每畝地一年按1000斤麥子算錢,聽起來不多,可是總能保我們一家五口的口糧,為2萬塊錢把地一下全賣了,有個啥事兒這錢花完了,以后可咋辦?”吳俊良說。
這一案件漏洞頗多。要建一磚廠的該地段本屬耕地,要變成建設(shè)用地,需要經(jīng)過省里的審批,但縣國土資源局并未報(bào)批。而信用社在沒有合法手續(xù)的情況下,就為村民發(fā)放了征地補(bǔ)償。在張保國、吳俊良等人不愿搬遷的情況下,相關(guān)部門出動人力大打出手。這一系列做法,違背了土地流轉(zhuǎn)的自愿原則,流轉(zhuǎn)程序更是不規(guī)范。不僅屬強(qiáng)制流轉(zhuǎn),且存在暴利行為,相關(guān)部門不是權(quán)為民用、利為民謀,而是以權(quán)謀私、橫行鄉(xiāng)里,嚴(yán)重?cái)牧嘶鶎狱h和政府的形象。endprint
“尊重農(nóng)民意愿,人人都講,但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在當(dāng)前鄉(xiāng)村治理格局下,農(nóng)民的意愿很容易被能量比他們大得多的工業(yè)項(xiàng)目、建筑項(xiàng)目所扭曲、所遮蔽。”中國人民大學(xué)農(nóng)業(yè)與農(nóng)村發(fā)展學(xué)院教授汪三貴如是說。要避免這一問題的發(fā)生,土地確權(quán)是一個辦法。但一紙紅色的確權(quán)證書,就能保證農(nóng)民合法的土地承包權(quán)今后再不被侵犯嗎?恐未必。問題的實(shí)質(zhì),恐怕還應(yīng)該是為誰服務(wù)的問題,是為人民服務(wù)?還是為人民幣服務(wù)?
土地是香餑餑,已經(jīng)成為土地投機(jī)者的共識。2012年9月27日,記者參加了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組織召開的《農(nóng)地制度改革與三農(nóng)發(fā)展論壇》,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農(nóng)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在論壇發(fā)言時(shí),激動地說:“我最近跑了幾個省,真是越看越害怕,現(xiàn)在資本在農(nóng)村搶地都搶瘋了。”他“搶瘋了”的話音剛落,臺下聽眾就報(bào)以長時(shí)間的熱烈掌聲,聽眾中,絕大多數(shù)是來自全國各地合作社的農(nóng)民。
我國農(nóng)地的集體所有制性質(zhì),為資本占有農(nóng)民土地設(shè)置了障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hù)了農(nóng)民的基本權(quán)益。在去年年底的中央農(nóng)村工作會議上,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堅(jiān)持農(nóng)村土地農(nóng)民集體所有,這是堅(jiān)持農(nóng)村基本經(jīng)營制度的‘魂。”而類似臺灣、日本的土地私有性質(zhì),則容易使得農(nóng)民在不利狀況下失地。在中國,可以說,如果沒有基層政府的配合,對農(nóng)地有瘋狂野心的資本便難有作為。但目前,官商勾結(jié)的強(qiáng)制流轉(zhuǎn)并不鮮見,就連拉開中國農(nóng)村改革大幕的小崗村也未幸免。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村民以按手印的方式,表達(dá)了希望自己經(jīng)營土地的愿望。30多年后,他們再次以這一中國農(nóng)民的獨(dú)特方式,表達(dá)了對強(qiáng)制流轉(zhuǎn)的抗議。嚴(yán)美昌,小崗村當(dāng)年18位“大包干”帶頭人之一,以順口溜的形式,表達(dá)了自己的心聲:“手中有地種不穩(wěn),四處老板來劃分;東挖溝,西扒豁,良田變成茅草窩。”
對此,有微博稱:“中國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何去何從?多年不公開賬目,強(qiáng)征土地,毆打村民,當(dāng)年按手印承包帶頭人@小崗村嚴(yán)宏昌等人被全面控制,金錢賄賂妖風(fēng)四起,糊弄幾任來視察的國家領(lǐng)導(dǎo)人,領(lǐng)導(dǎo)來視察,異議分子被控制在家。據(jù)@小崗變變變 反映:大批警察、執(zhí)法隊(duì)、干部強(qiáng)占大包干帶頭人宅基地,聲勢浩大堪比鬼子進(jìn)村。”
在這里,公眾不禁要問,是誰,把鬼子引進(jìn)了村?是誰,為了在虎視眈眈的資本面前分一杯羹,而置農(nóng)民的權(quán)利于不顧?
騙招競技 花樣翻新
在多家網(wǎng)站上,記者看到了這樣的秘笈:“玩”轉(zhuǎn)土地(土地經(jīng)營)的九種絕招。在此略舉幾例:
第四招:偷梁換柱,變相租給城里人。化整為零,變成只有幾分地的城里人開心農(nóng)場,每分地租500元以上;偷梁換柱,溫室大棚變城里人的鄉(xiāng)間別墅,收益更高!
第七招:扭轉(zhuǎn)乾坤,別人投資我圈地。搞一個農(nóng)業(yè)科技項(xiàng)目、編一個科研報(bào)告,“忽悠”政府低價(jià)給地,高價(jià)評估;“忽悠”投資人投大錢占小股。
第九招:錢更生錢,大家攢錢我掌控。注冊一個合作社、引幾個技術(shù)、寫一個規(guī)劃、做一個產(chǎn)業(yè)、建一個新村、畫一個藍(lán)圖,用農(nóng)民每家不多的錢、攢一個幾萬戶的資金互助。農(nóng)民又得利、又得產(chǎn)、又得房;合作社又得錢、又得業(yè)、又得名。幾個主要負(fù)責(zé)人名利雙收,呼風(fēng)喚雨!
……
“玩”轉(zhuǎn)土地的絕招堂而皇之地被多家網(wǎng)站轉(zhuǎn)載,可見農(nóng)村土地的誘惑力之大。老實(shí)的農(nóng)民與精明的商家過招,后果可想而知。
在此,記者不禁想到了一則關(guān)于駱駝的寓言。
主人牽著駱駝行走在沙漠上,天氣冷了,主人睡在帳篷里,駱駝不甘心。第一晚,駱駝?wù)f:“尊貴的主人,我能否把我的一只腿伸進(jìn)帳篷取暖?”主人答應(yīng)了。第二晚,駱駝要求再進(jìn)來一只腿,主人看看地方還夠,又允許了。第三晚,駱駝?wù)f:“尊貴的主人,您要是允許我再邁進(jìn)來一條腿,我就能更暖和點(diǎn)”,主人就往帳篷的一角縮了縮,邁進(jìn)了第三條腿的駱駝,已是大半個身子進(jìn)入了帳篷。第四晚,駱駝毫不客氣地占據(jù)了整個帳篷,主人被擠到了凜冽的寒風(fēng)中。
在土地流轉(zhuǎn)中,農(nóng)民會不會也因自身識別能力不高,而被“駱駝們”步步緊逼、排擠到“帳篷”之外?
據(jù)報(bào)道,在一些地方,土地中介人已成為一種新興職業(yè),他們指導(dǎo)投資者找到五個身份證注冊一個合作社,然后便可以幫著流轉(zhuǎn)土地,套取國家的補(bǔ)貼政策,在將流轉(zhuǎn)到的土地加價(jià)出手后,又能大賺一筆。一位隨相關(guān)部委參與過地方調(diào)研的專家直言,“現(xiàn)在等著鉆政策空子的人很多,利用自身和農(nóng)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認(rèn)為可以在改革中撈一筆,成立一個空殼合作社其實(shí)是掛羊頭賣狗肉,倒買倒賣囤地等漲價(jià)。”
最近,因被網(wǎng)友舉報(bào)擁有“百套房產(chǎn)、身家20億元”而落馬的東莞市原厚街鎮(zhèn)黨委委員、武裝部部長、人大副主席林偉忠,在借地生財(cái)上就頗有一套。他先是違規(guī)獲取使用社區(qū)集體土地建成房產(chǎn);建成后,利用曾擔(dān)任厚街鎮(zhèn)城建辦主任等職的職權(quán),二次違規(guī)給這些違建房產(chǎn)辦理了房產(chǎn)證等相關(guān)證明,以實(shí)現(xiàn)把違建“合法化”。靠土地?cái)烤挢?cái),林偉忠們可謂“生財(cái)有道”,但這條道是邪道,身后,是逃不脫的法律懲罰。
在一家農(nóng)業(yè)網(wǎng)站上,記者看到了廣東、四川、北京、湖北等十多個省、市的土地流轉(zhuǎn)排名和數(shù)字,流轉(zhuǎn)畝數(shù)竟然精確到了個位,排在第一的是廣東省。拋開數(shù)字的來源、準(zhǔn)確性先不論,這種不考慮各地實(shí)際情況就進(jìn)行排名的做法,是否有點(diǎn)緊鑼密鼓催行的態(tài)勢?如若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喜人的數(shù)字、領(lǐng)先的排名、耀眼的政績,而對土地流轉(zhuǎn)大加行政干預(yù)、經(jīng)濟(jì)刺激,那么,流轉(zhuǎn)中就難免出現(xiàn)問題、產(chǎn)生冤情。好“經(jīng)”念歪,這樣的教訓(xùn),還少嗎?
在最近的國新辦新聞發(fā)布會上,中央農(nóng)村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副主任、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現(xiàn)在一些地方確實(shí)存在炒作土地的現(xiàn)象,國家正在抓緊制定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遏制土地被轉(zhuǎn)租之后非糧化、非農(nóng)化,避免農(nóng)地違法改變用途,打消人們的投機(jī)心理。
土地流轉(zhuǎn)是方向,流轉(zhuǎn)得當(dāng),物盡其用、得歸其所,于國于民皆好。流轉(zhuǎn)失控,則必殃民禍國。在這一趨勢中,如何堅(jiān)持流轉(zhuǎn)的自發(fā)自愿原則,切實(shí)保障土地承包人的基本權(quán)益,是一件從土地轉(zhuǎn)出者、到土地轉(zhuǎn)入者乃至政府都需要慎重對待的事情。 endprint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