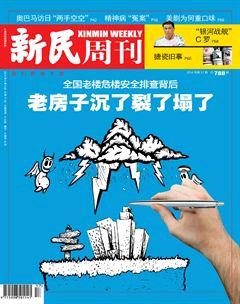新環(huán)保法與公眾參與
劉鑒強(qiáng)

修訂后的《環(huán)保法》出臺(tái),跟以前相比,不乏突破:第一是推動(dòng)建立基于環(huán)境承載能力的綠色發(fā)展模式,第二是推動(dòng)多元共治的現(xiàn)代環(huán)境治理體系,第三是賦予行政監(jiān)管部門更大權(quán)力。
但要解決目前嚴(yán)峻的環(huán)境危機(jī),這部法還有不足,特別是在保障公眾參與方面。
以公益訴訟為例。公益訴訟是懲誡環(huán)境破壞行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經(jīng)過(guò)公眾再三的強(qiáng)烈反對(duì)與建議,最終通過(guò)的環(huán)保法修訂案,將提起公益訴訟的主體擴(kuò)大到“在設(shè)區(qū)的市級(jí)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連續(xù)活動(dòng)5年以上且無(wú)違紀(jì)記錄的社會(huì)組織”。
這里有一個(gè)漏洞。目前全國(guó)在積極推動(dòng)公益訴訟的公益組織中,比較突出的有兩家,一是“自然之友”,一是“自然大學(xué)”,它們是中國(guó)公益訴訟領(lǐng)域的領(lǐng)軍者。但它們都注冊(cè)在北京的某個(gè)區(qū)內(nèi)。直轄市的區(qū)級(jí)注冊(cè),并不包含在“在設(shè)區(qū)的市級(jí)以上政府民政部門登記”這一條文內(nèi)。當(dāng)然,一般來(lái)說(shuō),直轄市的區(qū)級(jí)單位相當(dāng)于省的地級(jí)市。但法院完全可以“法律沒有規(guī)定”為名,不承認(rèn)此類機(jī)構(gòu)的公益訴訟主體資格。
目前公益訴訟的最大難題是法院不愿受理,比如去年全國(guó)公益訴訟的法院受理數(shù)為零。比如最近蘭州市民訴訟導(dǎo)致飲用水污染的企業(yè),就受阻于當(dāng)?shù)胤ㄔ翰皇芾怼?/p>
地方法院不愿受理環(huán)境公益訴訟,有幾個(gè)原因:一,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事件層出不窮,如果受理,則同類案件可能蜂擁而至,法院招架不住;二,環(huán)境公益訴訟會(huì)影響當(dāng)?shù)亍敖?jīng)濟(jì)發(fā)展”,地方法院不能不考慮地方政府發(fā)展GDP的需求。而且,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的受害者往往是群體性的,為所謂“維穩(wěn)”,當(dāng)?shù)赝鶅A向于不予受理;三,法院即使受理,也難以判決,而判決之后,也難以執(zhí)行。不能執(zhí)行的裁決會(huì)影響法院權(quán)威,所以干脆不受理。
法院想盡辦法找不受理公益訴訟的借口,而新環(huán)保法恰恰留下了漏洞。從根本上說(shuō),將公益訴訟主體資格以行政級(jí)別限制,不符合“公眾參與”理念。“自然大學(xué)”創(chuàng)辦人馮永鋒說(shuō),新環(huán)保法關(guān)于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的規(guī)定,暗藏著“社會(huì)組織的等級(jí)思想”,這“有違法律的基本精神,有違環(huán)境公益的基本哲理,有違生態(tài)保護(hù)的基本理念”。
目前在全國(guó)的村、鄉(xiāng)鎮(zhèn)和縣城,有一大批非常活躍的公益組織,這一條文將它們都排除在外了。馮永鋒說(shuō),“只讓城市的人有公益訴訟權(quán),不讓農(nóng)村居民有公益訴訟權(quán);只讓地級(jí)以上的人有公益訴訟權(quán),不讓地級(jí)以下的人有公益訴訟權(quán)。這道理、這心態(tài)無(wú)論如何都說(shuō)不過(guò)去。”
這部法在監(jiān)管部門的權(quán)力和懲治力度等方面有突破,也承認(rèn)了“多元共治”和公眾參與,但其重點(diǎn)仍是政府治理為主,而公眾知情、參與和監(jiān)督,仍處附屬地位。比如主益訴訟主體仍以“級(jí)別”限制,而不是以專業(yè)資格、專業(yè)能力來(lái)判定,這里面有濃厚的自上而下“控制治理”的遺風(fēng);對(duì)于信息公開、保證公眾參與的渠道,也語(yǔ)焉不詳。
目前有些地方的環(huán)保部門聲譽(yù)不佳,一是失職,二是徇私舞弊。權(quán)力越大,貪腐的可能性越大。如果沒有問責(zé),環(huán)保部門權(quán)力擴(kuò)大,環(huán)境狀況不會(huì)必然變好。而問責(zé)的壓力不應(yīng)只來(lái)自當(dāng)?shù)卣ōh(huán)保部門往往聽命于當(dāng)?shù)卣鼞?yīng)該來(lái)自信息公開與公眾參與。只有將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比如說(shuō)公益訴訟)結(jié)合起來(lái),才能保證環(huán)保部門正確使用監(jiān)管權(quán)力。要有效治理中國(guó)環(huán)境,這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來(lái)看,這部法是有缺憾的,不可盲目樂觀。正如環(huán)境公益律師夏軍所說(shuō),從政府行政管理的角度來(lái)說(shuō),這部法是大大加強(qiáng)了,“但這只是一部行政管理法嗎?難道不應(yīng)該是一部保證公眾參與環(huán)境保護(hù)的法嗎?”
他問得有理。
(作者為“中外對(duì)話”網(wǎng)站北京總編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