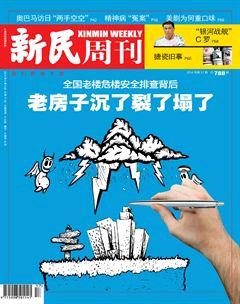米利安事件困惑了美國精英
朱宇倫


最近美國知名學府,全美排名前十的杜克大學的校長,可能會有些許苦惱和尷尬。這份苦惱與尷尬不是來自學校學術水平或者社會捐贈的下降,也不是因為杜克引以為傲的NCAA籃球隊出現了什么問題,問題完全是出在杜克大學的一位法律系新生——米利安·維克斯身上。
這個從照片上看其實并不算多么出眾的女生,不僅僅是杜克大學的大一新生,同時,她還有著一個特殊的身份——貝爾·諾克斯,色情片女演員。
高材生&色情片女演員
這樣兩種在普通人心目中八竿子打不著的社會角色,竟然在米利安身上發生了聯系,一方面她是擁有著極高受教育水平的美國名校學生,社會地位超出常人,另一方面她卻又有著令普通大眾所難以接受的、成人色情片女演員這樣一個用出賣身體、博人眼球來換取金錢的職業。在正常人看來,米利安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甚至有一位科羅拉多州男性讀者來信對米利安說:
之前你提到由于杜克(大學)學費太高,而你又不想背負巨額債務,自己沒經過其他職業培訓,所以決定投身色情業。在某種意義上,你是在暗示,為自我辯解,你沒有別的選擇——我指的是經濟上的選擇。
也就是說,如果你擁有大眾可以接受的職業技能,你很可能就會做其他事情去了,不會進色情業。
然而,當事人卻似乎不這么想,她這樣解釋:她和普通人一樣,都是為了掙錢而工作,我才不需要你們的同情。
而就在前些日子,適逢美國NCAA的瘋狂三月,米利安甚至許諾如果杜克大學的籃球隊能夠在瘋狂三月中笑到最后,她將為每位隊中成員贈送禮物,而禮物的內容極其露骨——私人性愛影片。
4月14日,米利安以其藝名貝爾·諾克斯在美國《赫芬頓郵報》網站撰文以回應那位男性讀者。
在文章中,米利安這樣寫道:人們以為我支持性工作者和色情業的立場站不住腳,因為我是為了金錢從事這一行,而非出于真愛。性工作者本不是我的夢想職業,他們搞得好像很震驚似的。我小時候沒有在學校“求職日”寫上“我想成為色情明星”,也沒有因為將來會在攝像機前做愛賺錢而興奮地和朋友們大聊特聊。老師也沒有告訴我,我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宇航員、總統,色情明星也可以哦!顯然這不是我夢想的生活方式——是出于“無奈”——所以,這就成了道德污點,我就成了可鄙的婊子,供人唾棄。
色情業不是我的唯一選項,而是我心理預期中最審慎、最明智的選擇——用最少時間交換最大利潤。我有能力輕松還掉學費貸款,我選擇不背這個債。我為什么要增添本不需要的5萬多美元學債呢?我的選擇不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無奈的交換”。
米利安的灑脫與坦然,在留給我們一個瀟灑的背影的同時,也倒是留給了我們一個巨大的疑問:數以萬計的家庭花費了這么多時間、精力與金錢,完成了象征精英階層的大學教育,但是這么多代價,對于這個價值觀正在走向多元化的社會來說,到底值不值得?
“米利安事件”,在重視大學文化并且引以為傲的美國人心中,已然掀起了軒然大波。世界上哪里都會有窮人和富人的差別,即便是在世界第一強國美國,也不會例外。隨著美國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失業率的居高不下,上大學尤其是私立名牌大學已經漸漸有了奢侈品化的趨勢,盡管家境富裕者大可不必為花銷擔心,但數量更多的家境一般者乃至家庭困難者卻不得不天天為高昂的學費愁眉苦臉。即使兢兢業業地度過了四年,畢業的他們卻還是面臨著社會的無情篩選,而美國早已固化的階級,往往會讓那些僅僅是依靠勤奮而沒有多少財富的青年人難以邁入更好的階級,難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如此周而復始,階級一步一步固化,貧富一步一步分化,美國夢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
盡管在那一篇復信中,米利安說她的選擇并非“無奈的交換”,但是,仔細翻看米利安的家庭履歷,我們就會發現,米利安選擇成為色情片女演員,也就是我們常說的AV女優,著實是有不少難言之隱。
米利安的父親凱文·維克斯是一名駐阿美軍的隨軍軍醫,一年的收入約為20萬美元,這在美國算是中等收入水平,但他的妻子沒有工作,而家中除了米利安每年需要交納6萬美元的學費之外,還有兩個孩子正就讀于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僅憑凱文一個人支撐整個家庭的支出,顯然捉襟見肘。于是,米利安選擇做女優掙錢,每次可以獲得1500到2000美元的報酬,花費時間不多而報酬卻相當可觀。
或許是覺得做女優確實有失“體面”,米利安沒有把真相告訴父親,所以老凱文直到回國才知悉女兒竟然在拍攝成人色情片。我們不知道這位父親的內心究竟會如何五味雜陳,但是一點苦澀,是少不了的。
上大學=上大當?
美國的各大主流媒體,在得知米利安的故事之后,爭相報道,并由此引發了諸多爭論。
在這些主流媒體的爭論之中,教育無用論再次被提上臺面。
其實早在2012年,奧巴馬上任之初,這樣的論調就曾經被拋出,當時的《星島日報》 報道稱,美國大學學費昂貴廣受社會詬病,然而大學生身負重債換來的學位,不僅不能保證高薪厚職,在經濟不景氣的當下,許多年輕人走出校門即加入失業大軍。在這種背景下,“教育無用論”的呼聲再起,論者呼吁學生和家長別再繼續上大當,他們鼓勵年輕人應放棄求學,自行創業。
報道指出,全美學貸總額現已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金額之大、增幅之快在消費貸款類別中名列首位。從個人來說,部分學生畢業時,負債可達10萬美元。但投入大量金錢和時間得到學位后,年輕人的就業前景并沒有改善,預料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將達8.5%,反觀只有高中學歷的人士,失業率則只有8.1%。失業率驚人之余,大學生的收入也下降了5%,同樣令人懷疑教育的價值。
本身年輕 時從斯坦福大學輟學,后來參與創辦PayPal而致富的商人迪爾就表示,除非有意投身醫學、學術界等少數領域,否則年輕人根本不用報考大學,他甚至設立計劃,以每人每年10萬美元的獎勵,鼓勵年輕人離開校園創業。
迪爾接受《60分鐘》節目訪問時,把高等教育與房地產泡沫相提并論,說樓市泡沫時人人以為自己需要買房,因此不惜代價置業,現在也是人人以為自己需要一張高等教育文憑,花再多的錢也要讀大學,學生和家長其實“都上了大當”。endprint
迪爾質疑,有才華的年輕人入讀常春藤名校,但最終都投身金融界,只幫助富人累積財富,不能造福社會,天資稍遜的入讀牟利大學,偏偏這些大學好像樓市中的“次貸銀行”,學生被推向負債深淵,走出校園后,過半數人失業、就業不足,又或者無法學以致用,只能在零售或餐飲業從事低技術工種。
而隨著奧巴馬刺激經濟計劃實施的并不成功,并且在中期選舉中丟失了對于眾議院的掌握權之后,類似于這樣的言論再次成為了反對派攻擊奧巴馬政府政策不給力的有力論據。
拋開政治不談,那么大學教育真的如同教育無用論所說的那樣,毫無價值可言嗎?
曾經在國內流行過這樣的段子,說的就是比爾·蓋茨求學中途從大學退學,和保羅·艾倫一起創辦微軟公司,最終成為世界首富的勵志故事,類似的心靈雞湯還有很多,這無疑刺激了那些持教育無用論的人的神經,于是他們大肆鼓吹教育無用論。
但是這些段子的編輯者顯然沒有告訴你的是,蓋茨的父母是IBM公司的股東,有了父母的支持,他才成功獲得了第一桶金,從此一發不可收。
編輯者同樣不會告訴你的是,一萬個大學退學生中,都未必出得了一個比爾·蓋茨。
所以,所謂教育無用論,從根本上就有些站不住腳跟,更別提沖擊美國人豐富而又悠久的大學校園文化了。
“大學不能保證一個高薪的好工作,但不讀大學卻是一個高風險的選擇。未來會更優待那些受過更多教育而非更少教育的人,瞬息萬變的經濟形勢更偏好那些擁有終生學習能力的人。”一位分析人士如是說。
教育真的無用?
但是有趣的是,在“米利安事件”見諸報端之前,美國主流媒體之一的《紐約時報》,卻似乎一直在和美國的大學教育唱著“反調”,它不止一次地刊登勸阻眾人上大學的文章。
這著實令人費解。但是仔細思索之后,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勸阻不無道理。盡管美國一直以《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平民社會自詡,關于美國夢的那些成功事例我們也都有所耳聞。
但是,平民社會僅僅是美國的一面而已,美國的另一面就是精英階層的教育世襲,無論是布什家族連續四代都就讀于耶魯大學,還是前副總統戈爾所有子女均為哈佛所錄取,我們都會從中窺見美國精英階層代代相傳的特點,富人與政客的下一代似乎必然不會差到哪里去,而階級之間的壁壘卻并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
《華爾街日報》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腦袋”也要擠進常春藤名校,為的是延續經濟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門第的出現和延續,是這一教育投資的重要回報。
而據《紐約時報》統計,隨著藍領中產階級的衰亡,大學教育成為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分水嶺;最窮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口子女獲得大學學位不到9%,而最富四分之一人口中達75%。
這也就無怪乎,《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們時常奉勸父母們不要把孩子送進大學了,當然,這或許只是針對那些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大學所能帶來的價值。
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經在1947年說過:“花費在教育上的錢是國家最明智和最合理的投資,要讓這種普遍認識在全國得到很好的發展。”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教育系榮退教授、《美國高等教育通史》作者亞瑟·科恩說得更具體:“盡管一些職位不要求學位,但這些工作仍基于一些通用的知識和特質:計算和語文素養、合作的風度、責任感、機敏的反應,乃至恰當的著裝與舉止,即所謂的‘軟技能,這些通常都是在大學習得的。對雇主來說,這些積極的態度和觀念比任何高等教育證書都重要。”
發生在米利安身上的故事其實僅僅算得上一個小小的關于大學教育的插曲,連她自己都承認拍攝色情片僅僅是為了掙取學費,由此可見,大學教育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即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大學教育。
所以我們大可不必擔心美國大學教育的未來,但是,它還需要改進,需要演化,它不應該讓學生們背上沉重的負擔,而是應該讓所有人在享受教育的同時,為國家創造更多的財富,創造更多的價值。
而這一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