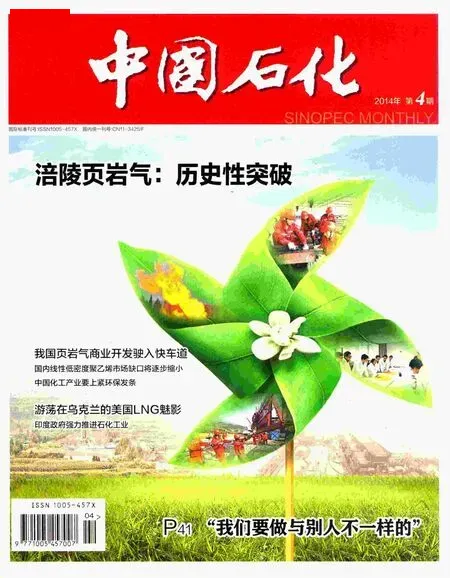中國化工產業要上緊環保發條
王玉振 曹鳳中
化工產業是建設美麗中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產業發展的同時,保護好環境刻不容緩。

化工產業發展的同時也要保護好環境。傅紹同 攝
伴隨我國化工產業快速發展,污染排放量不斷上升。我國燃煤和重化工業造成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均超過2200萬噸,位居世界第一,煙塵、粉塵排放量為1446.1萬噸,均遠超出環境承載能力。冬季取暖北方大部分地區燃煤量大幅增加,導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急劇上升。
解決中國現實的環境污染問題是當務之急。消除中國經濟要發展、環境要改善的瓶頸,環境保護工作必須實行改革,著力點是強化我國經濟與環境政策的聯動。化工產業是建設美麗中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產業發展的同時,保護好環境,是時代的要求。
強化源頭控制
強化項目與規劃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發展缺乏整體性、戰略性,產業布局缺少統籌,遍地開花,是我國化工產業的突出問題。一些煤炭富集區片面強調對煤炭的開發利用,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和約束,發展煤化工項目存在盲目性;一些企業則順水推舟,借著地方政府提高煤炭就地轉化率等政策要求,以發展煤化工圈占煤炭資源。相關資料顯示,規劃和新增煤化工產能中,相當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批準的。
國家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考慮將化工產業納入直接審批的建設項目目錄,提高環境準入門檻,并結合國家有關化工產業發展的總體思路,嚴格控制規劃布局、限制總量,提高新型化工產業準入門檻,及時遏制化工產業盲目、無序發展的態勢。
盡快頒布戰略環境影響評價條例。建議盡快開展煤化工產業發展戰略環評,探索煤炭富集區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研究制定差別化的環境管理政策和調控手段,突破西部地區煤化工產業發展的水資源瓶頸,引導煤化工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為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提供決策依據。
強化環境保護協同控制政策,做好編制綜合名錄工作。編制環境保護綜合名錄,就是要通過對產品、工藝、設備進行深入分析、科學論證,來反映其對環境的影響,通過有差別化的政策,將資源稀缺程度和生態價值內化為企業內部成本,強化企業的生態環境責任。同時,建議國家有關部門采取差別化的經濟政策和市場監管政策,遏制“雙高”產品的生產、消費和出口,鼓勵企業采用環境友好工藝,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藝的權重,并加大環境保護專用設備投資,達到以環境保護倒逼技術升級、優化經濟結構的目的。
強化末端治理
在化工企業實現完全的零排放是不經濟的,也是不可能的。提高末端污染物排放標準,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近年來“零排放”作為一種廢水污染控制模式,開始在一些煤化工項目進行示范。但從總體而言,煤化工項目“零排放”仍面臨投資巨大、處理成本高、處理工藝能耗高、濃縮物易形成二次污染等眾多技術及管理難題。
石油化工生產對水的污染相當嚴重。石油開采、加工都需要水。同時,在石油的運輸過程中,有時會由于一些主客觀原因,造成石油在運輸過程中的泄漏,也會污染水源。
因此,首先要切實加大環保投入。其次要利用先進技術與現代化手段,搞好環境保護。對還未建立遠程在線監控系統的排放口的污染物排放情況進行不定期抽測,確保做到穩定達標排放。要優選工藝流程與優化工藝操作,在廢物的處理上,結合現在的生物技術降低污染。
嚴格實施總量控制
實施總量減排政策,就必須進行科技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強制性地轉變發展方式。實際上,就是采取經濟與環境融合的政策,在發展的同時解決環境問題。
除了要繼續重視COD、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這四項主要污染物減排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外,特別要重視關于PM2.5以及針對有毒有害物質、營養性物質、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污染減排政策的制定。嚴格執行大氣污染物總量倍減計劃,對于華北6省聯防聯控區中的重點控制區和大氣環境質量超標城市,新建項目實行區域內現役源2倍消減量替代,一般控制區實行區域內現役源1.5倍消減量替代。
在2015年后,碳減排工作逐步強化,一方面有利于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另一方面碳排放背后有著對國家利益的深遠謀劃。發達國家利用全球減排框架,一方面可以加速推動自身節能減排新產業、新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可以確立減少碳排放的國際道義體系,使其通過技術壁壘打壓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產品出口的行為獲得合法性。根據對中國經濟、產業中期發展趨勢的分析,環境保護的中期路徑,主要是通過在重化工業中推進先進的生產方式、管理方式和技術,來減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形成頂層到底層的良性互動
架構“政府—市場—社會”共同治理模式。隨著經濟的發展,在環境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進行適當干預,以保障公眾的信息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非常有必要。應實施更有效的環境信息公開政策,利于公眾參與、監管、維權,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環境的共同治理。
我國環境保護政策體系基本上是完善的,關鍵在于實施機制的軟化,從執法的機制與體制上進行改革是根本選擇。
統籌考慮產業布局與地方收益的關系,平衡各方利益,從根源上消除資源富集區發展陷入“資源依賴”的體制性原因。應完善政績考核體系,從制度上消除地方各級政府通過開工程、上項目刺激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改變政府為化工產業高速、盲目發展做“推手”的角色,使市場調控機制在推動化工產業健康、有序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
只有從頂層到底層的上下良性互動,才能真正實現我國經濟與環境政策的聯動,走出我國環境保護面臨的困境。這種互動既包括環境保護的制度政策設計與執行,也包括工業的組織形態與生產方式轉變,更包括社會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監督與問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