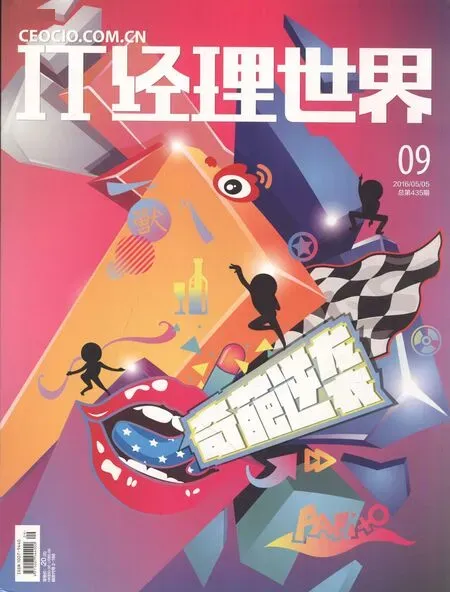為觀念定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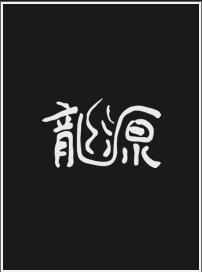


觀念的價值,僅當與互補觀念相遇時才可實現。觀念改變世界,前提是,互補的觀念可以足夠低的代價相遇。各國基礎教育實行免費制度,于是教育成為每一個人改變自己命運從而社會不平等程度得以逐漸緩解的首要條件。互聯網之所以具有“社會革命”之效果,因為絕大部分知識是免費在網絡之內傳播的。任何旨在鼓勵觀念自由傳播從而迅速提升社會生產力的公共政策(例如知識產權政策),永遠面對這樣的權衡:一方面,觀念定價不能太低,否則很難維持觀念原創人的收入水平。天才對人類貢獻最大,而天才夭折的比例最高。另一方面,如前述,觀念定價不能太高。因為觀念未分享時,信息不對稱性足以阻礙觀念的需求方拒絕支付供給方提出的觀念價格。
信息不對稱性處處存在,在任一物質商品的交換過程中,買方對賣方出售的商品通常知道得不如賣方詳盡,所以才有著名的“檸檬原理”,以及2001年這一原理帶給阿克勞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物質商品市場里的信息不對稱程度足夠高,那么,“檸檬原理”意味著,市場有可能(而不必定)“坍塌”,也可能陷入“高水平均衡”或陷入“低水平均衡”,或多重穩定均衡的某一狀態。于是存在市場效率的損失,因為有許多潛在交易無法實現。與物質商品相比,觀念定價過程除了包含信息不對稱之外,還因觀念可以無限分享(復制)而要求觀念所有者支付高昂的產權成本(反盜版)。假如你與另一人均分你的一片面包,那么,均分使你對這片面包的產權貶值至最初的一半。假如你與另一人分享你的一項觀念,那么,你對這一觀念的產權貶值至零。因此,在傳統社會,知識以“師徒相承”方式緩慢傳播。緩慢,因為徒弟必須多年侍奉師傅,僅當“父子”關系可信時,師傅才傳授“秘訣”。現代社會尊重產權,擴展至知識領域,例如學術界,人們普遍尊重觀念的原創權。牛頓和萊布尼茲關于微積分發明權的那場爭論,既涉及英德民族情感的糾結,也表明社會對觀念原創人的尊重。
對觀念原創人的尊重,演變為對學術權威的尊重,于是有對權威人士的信任,以及信任感在社會網絡之內,首先在學術界的傳播。在有信任感的社會網絡之內,觀念可在師傅(權威)與徒弟(學生)之間自由傳播。這樣的社會網絡通常規模很小,現在稱為“俱樂部”或“會所”,以前稱為“學社”或“書院”。這是關于觀念傳播的一項經濟學原理:凡知識可以迅速傳播的社會網絡,信任感是第一要素。
徒弟何時出師?通常由師傅決定,而師傅則要權衡多種因素,例如,學派的影響力(權威及對這一權威信任感傳播至更大的社會網絡)、徒弟升級為師傅的資格與能力、徒弟另立學派的可能性、新學派與既有學派的關系……這些因素,通常在知識社會學的考察范圍之內。
醫患關系,患者愿意為醫技付費,越是權威的醫生,患者愿意支付的費用(代價)越高,這是“名醫”的定價基礎。雖然,對權威的信任感不能確保醫技對特定疾病的治療效果。由代價引致的預期未能滿足,于是可能有“醫患”糾紛。教育的效果遠比醫療效果更難預期以致連“供求”糾紛的依據都難以獲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家長投資于子女的教育,回報固然很高,風險其實也很高。降低投資風險的方法是尋找更權威的教師或更可信任的學校,這是“名校”的定價基礎。
在穩態社會里,名家的名聲能夠傳播廣泛且帶來足夠高的收益(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收益足夠高,故而名家愿意支付維護名聲的費用(物質的、社會的、精神的)。在轉型期社會里,名聲傳播不易且損耗極快(轉型期的關鍵特征是折現率太高)。故而收益低,以致名家不愿為維護名聲支付費用。由此不難理解教授抄襲及其他類型的學術不規范行為,在“工具理性”視角下,有充足的理性依據。
中國社會是典型的轉型期社會,如上述,因為缺乏信任感,觀念在這樣的社會里很難定價。也因此,我一直鼓吹在中國降低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參閱汪丁丁“概念格、互補性、塔爾斯基不動點定理”,《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其實,越嚴格的保護政策越形同虛設。姑且承認“知識是第一生產力”,中國是盜版大國,也是經濟奇跡大國,二者之間難道沒有因果聯系?
目前流行的“微信”,兼有“臉書”的特征,二者都有“俱樂部”的形式——會員資格以及入會之后的免費觀念分享。只不過,網上的俱樂部還是虛擬的,不易獲得真實的信任感。也因此,原創觀念最初只在摯友之間傳播。網上形成的俱樂部,若不能形成深層情感交流,將很難實現原創觀念的自由分享。俱樂部財富的最終來源是原創觀念,不能有深層情感交流,也就不能長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