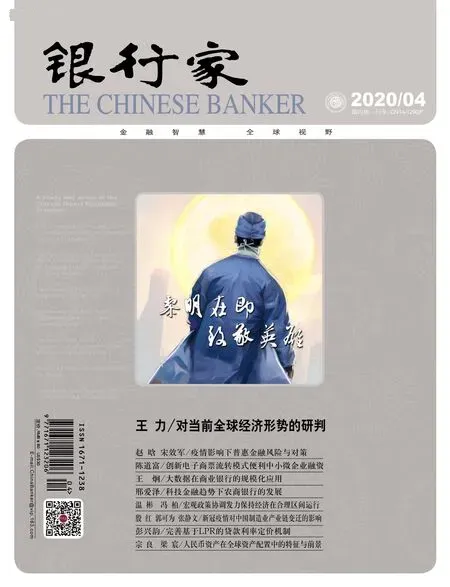唱空中國經濟?—我不同意
張晶
市場全面唱空2014年中國經濟的理由
當前,由于國內各種經濟數據再度疲軟,美國QE(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沖擊預期再度提升,新興市場幾乎全面遭遇沖擊,逐漸有全面唱空2014年中國經濟的聲音出現,這是目前海內外同行對中國經濟的核心討論。同時,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國處于“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觀點,更是強化了市場的看空預期。
近期各項數據顯示,匯豐與中采PMI(采購經理指數)走軟,匯豐PMI新訂單與產出指數持續下滑,能源與非能源產品價格走低,黑色金屬與有色金屬價格走低,全國主要煤種均價走低,國內主要地區水泥均價走低,鋼材價格指數走低,國內主要鋼鐵品種均價走低。就結論而言,可以看到2014年中國經濟下臺階、利率中樞下行、匯率全年呈貶值態勢。但是,筆者在這里要談談不同看法。
未來中國經濟的風險點
外部風險
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風險主要來自美國。圖1數據顯示,美國國債長端收益率走高,預計上破3%,同時通脹預期進一步走高。如果美國步入加息通道,美元資產的吸引力就會大增。若前期積累了過多的套息、套利資金需要平倉,資金將蜂擁而出,人民幣大幅貶值,人民幣資產泡沫破滅。
內部風險
內部風險主要是國內經濟主動下臺階、信用風險爆發導致的資金鏈大面積斷裂。大致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因地產夾層融資與供應鏈融資的斷供,導致市場對地產資產的不信任大幅蔓延,惜貸情緒擴散;第二層是,過去不讓關廠停廠的,現在松動了(決策層的主動行為),即步入習近平主席所說的“結構調整陣痛期”,經濟需求實質性下降。這反映了國內風險溢價的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進入到第二層還意味著,地產對經濟的捆綁被主動放松了。因此,“吸金”大戶對資金的需求降低,市場利率下行。
同時,與外部風險相類似的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吸引力下降,在全球資產配置中的吸引力也進一步下降。人民幣匯率貶值,人民幣資產泡沫破滅。當然,上述情形還只是筆者的假想,但市場目前已不乏全面看空中國經濟的聲音。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勢究竟如何,在做出對這一問題的判斷之前,有必要首先對流動性、利率以及人民幣匯率的邏輯進行相關的分析與梳理。
流動性與利率
流動性與利率的核心表現在于:流動性矛盾有所緩和,但利率中樞下臺階尚未到來。近兩年利率中樞上升的核心邏輯就是中國經濟沖向債務閥值且停留時間較長的一個集中表現,兩塊吸金大戶——地方融資平臺與地產,他們對利率的敏感度偏低,可以承受更高的財務成本,搶奪了更多的資金資源。
2014年是融資的大年,這主要是由于前期債務到期的壓力非常大,且在債務集中到期的時候,難免有信用風險的出現,筆者認為,市場普遍存在的“剛性兌付”預期可能會被打破。一旦不再是“剛性兌付”,風險溢價水平毫無疑問將會上升。理論上,信用風險上升時,利率債會成為“香餑餑”。但是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屆時銀行會盡力規避自身出現的大量不良資產,所以劣幣驅逐良幣,變賣利率債填窟窿的情景又可能出現,正如同2013年下半年的類似情況。
同時,央行的貨幣政策并未整體轉寬松。節前看到的“放松”,應該是結構性的、季節性的變化。因為央行貨幣政策全面轉向的條件只有一個,即經濟總需求的快速萎縮。
從上述三個方面來看,未來利率應該還是會往上走。但是春節之后央行雖然幾度正回購回籠資金,市場的利率仍然向下(圖2),且能夠感知的流動性依然相對寬松。這種現象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深思。筆者認為,短期的變數存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央行公開市場上出現了“結構性的、季節性的變化”,結構性的變化是指央行加強了預期管理,對金融穩定性的訴求更上一個臺階,比如常設借貸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操作常規化,平滑了流動性的波動。第二,2013年加杠桿仍然是十分迅猛的,商業銀行想盡辦法規避2012年年底以來的各種新規,但這個邊際效應無疑也是遞減的。在所謂“9號文”出臺之后,商業銀行的加杠桿行為還是得到了約束,資金需求邊際減少,無疑將釋放出一定的流動性。第三,投資一旦下滑,對資金的增量需求也就會相應減少。
因此,當前判斷流動性和利率的核心因素在于,短期的變數什么時候結束,以及中長期的邏輯是否發生了變化。筆者的觀點是:一方面,短期利好利率的變數還將存在一段時間,需要一定時間消化,尤其是兩會前后市場可能會有新的預期和邏輯出現(比如對投資的預期、對債券供給的預期等或有調整,同時,3月還將迎來2014年的第一次償債高峰)。另一方面,中長期的邏輯沒有變化,也就是說利率中樞下臺階還未到來。中國還沒有進入到去杠桿時期,只是加杠桿的進程放緩了。如果出現需求的快速萎縮,央行的貨幣政策全面轉向,利率中樞下行才是順理成章的事。
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貶值的原因
人民幣匯率的表現體現為:人民幣貶值為央行的短期引導,而并非是趨勢。從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節之后的資金面是相對寬松的,且還可能維持一段時間。此外,人民幣最近連續貶值,并創下年內新低。但與其他新興市場匯率狂貶、利率飆升的現象不同,中國目前是匯率貶、利率降。筆者認為,中國的金融市場仍在自我控制、自我修正的軌道里運行。事實上,從2012年9月開始,人民幣即期匯率強勢與人民幣流動性趨緊并存的現象反復出現,這是過去十年中未曾見過的。
2005年之前,由于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對于潛在的進口者來說,與其通過銀行借款或其他舉債的方式籌措資金用于進口資本品,不如通過FDI(即外商直接投資,下同)籌集資金更有吸引力。簡言之,中國國內儲蓄不得不通過國外的資本市場轉化為國內的投資。此外,資本項目管制、外來資本的超國民待遇、地方政府政績函數包含FDI等等,使得FDI迅速增長成為資本項盈余的主要貢獻者(余永定,2006)。但是從2005年開始至2008年,經常賬盈余顯著超過FDI,成為外匯儲備增長中最主要的貢獻力量。2009年以后,資本項盈余又重新超過了經常賬盈余,成為外匯儲備增長的重要貢獻因素。這無疑與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有關——2004年之后,剝離了大量不良資產,并進行了股份制改造的銀行系統獲得了新的力量。然而,經常賬快速收窄反映的并不是國內儲蓄率的下降,而是投資率的上升,特別是在2009年之后表現更為突出。同時,由于國內投資的擴張,導致境外資本流入的擴大,統計口徑內的國內機構外債借入規模快速上升,外債從2008年的3900億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8229億美元。
而目前,外匯占款新增對流動性的指示性已越來越差,更多的是總量掩蓋了結構的問題——投機性資金的進入屬于名義上的收入、實質性的負債。所以,進來的是短錢,流出去的是長錢。短錢經過銀行中介又進入到經濟的長期資產,這就造成了金融系統脆弱性不斷累積的隱患。因此,2012年9月之后人民幣匯率市場發生的變化,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為防止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出現與自我強化,中國央行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加強了主動的管理,這種“管理”(而非“浮動”)成為決定人民幣匯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盡管在債務包袱壓力下國內流動性持續緊張,央行仍有意維持一個穩定的匯率預期,同時,由于利率上升,反過來又推動了投機資金的涌入,推動了人民幣升值,自此形成一個“怪圈”。
央行實際上也是兩難的,因為人民幣升值速度的加快無疑會對國內出口部門形成更加嚴峻的壓力。所以,人民幣的走勢單邊上漲絕非央行的最優選項。從2013年年底起,新興市場的動蕩反而導致投機資金更為青睞人民幣,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太快,且相對于一籃子貨幣而言走得太快太遠。央行目前有意愿引導人民幣走軟,以穩定出口形勢、抑制套息資金流入。同時,目前的時點也十分合適,因為每年2~3月份都屬于出口的淡季,人民幣走軟是順理成章的。
人民幣的趨勢走向
理論上來看,決定匯率的短期因素通常是外匯的供給與需求,而貿易差額又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但值得強調的是,從2012年年初開始,由于國際間勞動生產率水平的相對變化,中國外匯占款的波動性將明顯增強。2013年以來,套息套利交易的增加更是放大了這一現象。
然而,2014年將是大考之年。從外圍看,美國經濟復蘇前景明朗,加息預期將漸行漸近,美元資產的吸引力日益增強;日本在前期用匯率和股市的兩筆提振了信心,用“重典”贏取了下一筆結構改革的時間,未來日本將繼續維持目前的量化寬松政策,貶值的道路仍未走完。相對而言,人民幣明顯缺乏彈性,過去的5年已積累了過多的壓力,人民幣資產的泡沫越積越大。而國內的結構性改革尚未有實質性進展,“去杠桿”進程尚未展開,人民幣的包袱還無法解除。所以,2014年人民幣的走勢大概率仍是穩定走強,但升值的幅度將較2013年明顯收窄,為了穩定經常賬、抑制套息資金,預計央行的主動干預將會增多。
政策路徑推演
當前國內經濟走衰苗頭再度顯現,目前已不乏各種預期的自我強化,那未來政策的抉擇,是任其自由發展,還是將其扼殺在搖籃中?這一問題可以推演出如下幾種情形。第一種情形,美國的經濟趨勢不受國內政策控制。國內能做的,只是略為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比如不能再是單邊升值的政策取向,可以配合經濟形勢,主動放低姿態、適度貶值。同時,不斷增加主動干預,讓人民幣匯率盡可能穩定。第二種情形,若經濟下臺階是主動選擇的行為,這表明不會有太多“托底”的政策出現(其實“托底”也是飲鴆止渴),這種情況下政策可以做的,就是不能讓債務滾動的鏈條大面積出現斷裂,屆時經濟需求還是在真實下行,但由于央行的干預,金融系統的風險還是可以避免。另外,實際上還會有第三種可能性(這也可能是最大的可能),就是經濟主動下臺階屬于中期愿景(比如2015年之后)。畢竟2014~2015年屬于償債高峰年份,外部風險相對2013年也更敏感,現在這個時點主動下臺階無疑會埋下許多隱患。因此,結構調整陣痛期會在稍晚的時間到來。
反觀美國,即便美聯儲決定在2014年年末進入加息周期,其對美元資產價格的拉升、對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的抬升也存在滯后效應。此外,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的相對吸引力還沒有消除。中國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匯率受到管制,這的確在過去5年當中積累了太多的風險,但同時,由于中國的外匯儲備積累豐厚,政府對金融資源的掌控力較強。同時,在結構改革(或準備轉變)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出現。比如,據報道中國正在準備核準一批未來的國家級重大項目(其重點將是對結構轉型的支持和傾斜),銀監會擬推出的平臺貸款再融資也能緩解2014~2015年債務集中到期的壓力,若政策銜接得當,經濟下滑也會得到一定平抑。
最后,筆者來大致預計在上述第三種情形為真的情況下,資本市場的表現。第一,股票。小股票的邏輯依然成立,但是風險溢價水平無疑上升了(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風險偏好下降、風險溢價水平的上升意味著波動率會增加)。第二,債券。資金邊際需求下降會帶來利率債的投資機會,但仍不排除部分信用風險爆發時帶來的擠出效應,信用利差或擴大。第三,人民幣匯率。維穩仍是主旋律,央行的主動干預會增多,人民幣匯率彈性略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