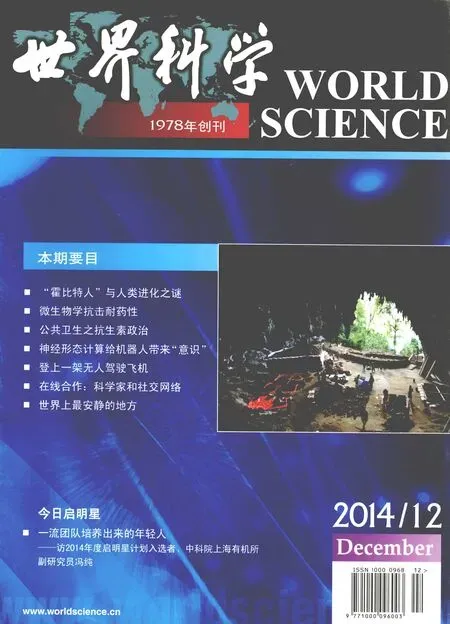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一定能夠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繁榮嗎?
繆其浩
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一定能夠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繁榮嗎?
繆其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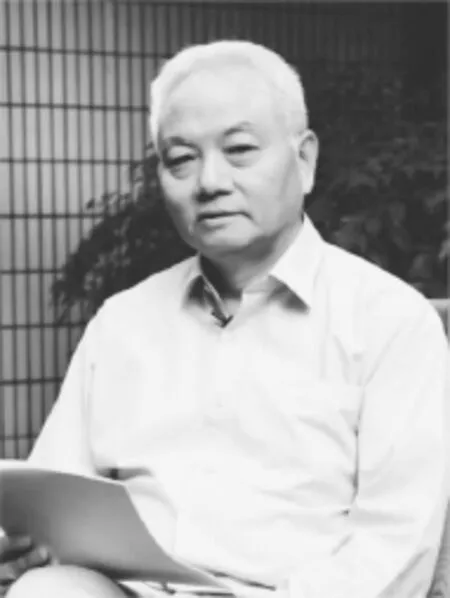
繆其浩,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情報(bào)研究所研究員,曾擔(dān)任上海科學(xué)技術(shù)情報(bào)研究所副所長(zhǎng),上海圖書(shū)館副館長(zhǎng)
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生革命性的重大變革可能是這個(gè)時(shí)代的潮流之一,近幾年來(lái)有人提出了基于數(shù)據(jù)的科學(xué)研究“第四范式”,國(guó)內(nèi)也有專家提出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概念;第二機(jī)器時(shí)代、第三次工業(yè)革命和最近開(kāi)始熱起來(lái)的工業(yè)4.0等說(shuō)法則跨越科學(xué)、技術(shù)一直延伸到了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
世界經(jīng)濟(jì)自2008年遭遇危機(jī)以來(lái)尚未恢復(fù),除美國(guó)等目前稍有起色,歐洲仍在苦苦掙扎,而發(fā)展中國(guó)家也因各種原因普遍出現(xiàn)增長(zhǎng)速度降低,后續(xù)沖勁乏力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各國(guó)普遍對(duì)這場(chǎng)科技和產(chǎn)業(yè)革命予以強(qiáng)烈關(guān)注,政府也紛紛推出政策措施,力圖抓住機(jī)遇以創(chuàng)新推動(dòng)發(fā)展,不難看出對(duì)新一輪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帶來(lái)新經(jīng)濟(jì)繁榮所抱有的期許。
然而與此同時(shí),一場(chǎng)關(guān)于技術(shù)革命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關(guān)系的爭(zhēng)議也浮出水面,焦點(diǎn)是,這一輪的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究竟能不能帶來(lái)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又一輪高潮。這個(gè)爭(zhēng)議其實(shí)并非自今日始。上世紀(jì)70年代以后增長(zhǎng)放緩,而這恰恰是計(jì)算機(jī)應(yīng)用開(kāi)始迅速擴(kuò)張的時(shí)期。1987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羅伯特·索羅在他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jì)獎(jiǎng)幾個(gè)月前發(fā)表的一篇書(shū)評(píng)上寫(xiě)道,“我們到處可以看到計(jì)算機(jī)時(shí)代,唯獨(dú)在生產(chǎn)率統(tǒng)計(jì)上看不到”。這句話后來(lái)被稱為“生產(chǎn)率悖論”,實(shí)際上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并非第一次,十九世紀(jì)電力剛剛引進(jìn)美國(guó)工廠時(shí),其生產(chǎn)率在其后20年時(shí)間里也沒(méi)有明顯增長(zhǎng)。順便提下,索羅決非是忽視科技進(jìn)步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把衡量資本和勞動(dòng)力運(yùn)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稱為“技術(shù)進(jìn)步”,就是由索羅開(kāi)始的。最近國(guó)外重新提起有關(guān)“索羅悖論”的話題,對(duì)同樣關(guān)注新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的中國(guó)來(lái)說(shuō),確實(shí)值得關(guān)注。
新一輪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確實(shí)正在到來(lái)
對(duì)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的期待和議論從來(lái)就沒(méi)有停止過(guò)。2008年金融危機(jī)爆發(fā)后,在匆忙“救市”的同時(shí),主流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就已經(jīng)把從根本上克服危機(jī)的希望寄托在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上。當(dāng)時(shí)人們憂慮上一輪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原動(dòng)力信息技術(shù)已顯頹勢(shì),曾被寄予很大期望的生物技術(shù)仍然步履艱辛,一度被看好的新能源似乎也難孚眾望,然而現(xiàn)在卻可以看到,新一輪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的輪廓似乎已漸漸清晰。
2012年4月,在同類雜志中通常屬于比較謹(jǐn)慎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人》以一個(gè)專輯的形式報(bào)道了“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次年德國(guó)聯(lián)邦教育與研究部委托的工業(yè)4.0建議書(shū)出爐,而只要把它與美國(guó)正在熱議的工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和智能制造聯(lián)系起來(lái)看,就不難發(fā)現(xiàn)背后是當(dāng)前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同一種趨勢(shì)在起作用,只是在應(yīng)對(duì)策略上德國(guó)版和美國(guó)版的區(qū)別。在這個(gè)大潮中網(wǎng)絡(luò)信息依然是最活躍的精靈,然而器件物體正在成為“新寵”。前一陣媒體關(guān)注過(guò)的大數(shù)據(jù)、物聯(lián)網(wǎng)、3D打印和機(jī)器人等,都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
“生產(chǎn)率悖論”是不是依舊存在?
最近出版的《第二機(jī)器時(shí)代》(中譯本名為《第二次機(jī)器革命》)屬于技術(shù)樂(lè)觀派,書(shū)中對(duì)“生產(chǎn)率悖論”給出了一個(gè)解釋,認(rèn)為再延伸下去看,生產(chǎn)率會(huì)在一段時(shí)間之后出現(xiàn)強(qiáng)勁增長(zhǎng),所以作者肯定了技術(shù)革命對(duì)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的作用,但是注意到二者會(huì)發(fā)生一個(gè)時(shí)間差,作者用了一句玩笑話,“要等到上一代經(jīng)理人退休以后”。
而另一方面,曾為“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推波助瀾的《經(jīng)濟(jì)學(xué)人》周刊今年10月4日發(fā)了一組“世界經(jīng)濟(jì)特別報(bào)道”,頭篇開(kāi)宗明義就認(rèn)定技術(shù)革命造就了“窮人更窮、富人愈富”。第二篇文章標(biāo)題干脆就叫“技術(shù)不管用”,不僅提到2000年以后正當(dāng)網(wǎng)絡(luò)和智能技術(shù)大發(fā)展的時(shí)期美國(guó)生產(chǎn)率出現(xiàn)停滯,而且對(duì)于那種“作用滯后”的解釋,也拿出一位據(jù)說(shuō)對(duì)生產(chǎn)率統(tǒng)計(jì)更為權(quán)威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觀點(diǎn)加以質(zhì)疑。文章認(rèn)為媒體上大肆炫耀的“技術(shù)革命”對(duì)長(zhǎng)期生產(chǎn)率的正面作用是可疑的,而打壓工人平均工資倒是確鑿的。
今天仍然健在的索羅本人對(duì)于 “生產(chǎn)率悖論”是怎么看的呢?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今年9月份對(duì)這位已經(jīng)年過(guò)90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進(jìn)行了訪談,最后一問(wèn)提到了“索羅悖論”,問(wèn)題是,你認(rèn)為這個(gè)說(shuō)法在當(dāng)時(shí)是對(duì)的嗎?如果是的,那么現(xiàn)在是不是還是正確的呢?
索羅做了如下回答:我說(shuō)那句話時(shí)正在閱讀某人的一本著作,當(dāng)時(shí)那是正確的,但是今天已經(jīng)不再是正確的了。實(shí)際上你可以追尋到信息技術(shù)對(duì)生產(chǎn)率的影響。回溯過(guò)去,在制造業(yè)、零售和批發(fā)行業(yè),在所有大的經(jīng)濟(jì)部門(mén)學(xué)會(huì)如何有效利用信息技術(shù)會(huì)造成一個(gè)延遲,這或許是難以避免的。但是現(xiàn)在你可以毫無(wú)疑問(wèn)地衡量出計(jì)算機(jī)對(duì)大用戶生產(chǎn)率帶來(lái)的效益。
生產(chǎn)率之外還有其他爭(zhēng)議
如果說(shuō)“悖論”的始作俑者出來(lái)說(shuō)了話,對(duì)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效益的長(zhǎng)期影響可以比較樂(lè)觀的話,還有一些問(wèn)題恐怕遠(yuǎn)不是那樣輕易可以解決。特別是對(duì)就業(yè)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貧富差距進(jìn)一步加大的擔(dān)憂還會(huì)繼續(xù),這場(chǎng)爭(zhēng)議短時(shí)期內(nèi)看來(lái)難以平息。
關(guān)注德國(guó)工業(yè)4.0發(fā)展不會(huì)不注意到西門(mén)子公司近年來(lái)不斷裁員的信息。2014年4月西門(mén)子再次確認(rèn)了其結(jié)構(gòu)性的裁員,撤銷(xiāo)了四個(gè)最重要業(yè)務(wù)的中間構(gòu)架,計(jì)劃裁員5千到1萬(wàn)。而該公司不僅是世界著名的制造業(yè)巨頭,更是工業(yè)4.0的先鋒。當(dāng)然,這次幾乎可以肯定這不是推進(jìn)工業(yè)4.0的結(jié)果,但是如果工業(yè)4.0真的到位,這類超級(jí)大公司的結(jié)構(gòu)肯定進(jìn)一步扁平化,中間層的壓縮可能更為慘烈。
對(duì)新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抱有疑慮的還不止是生產(chǎn)率增長(zhǎng)不如期許或者貧富差距進(jìn)一步加大,還有例如人工智能和機(jī)器人發(fā)展可能對(duì)人類帶來(lái)危害的擔(dān)憂,從新銳企業(yè)家(如埃隆·馬斯克)到偉大科學(xué)家(如霍金)同樣都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爭(zhēng)議對(duì)我們的啟示
盡管如同許多類似的爭(zhēng)議那樣,皆大歡喜的共識(shí)恐怕永遠(yuǎn)無(wú)法產(chǎn)生,但這個(gè)過(guò)程本身對(duì)我們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在中國(guó)主流輿論中,技術(shù)革命一直扮演一種“正能量”角色,人們關(guān)注第三次工業(yè)革命或工業(yè)4.0,恐怕很少是出乎對(duì)探求未知的興趣,而恰恰是寄托了提升產(chǎn)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從而加快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巨大期望。一些智囊和咨詢研究機(jī)構(gòu)的建議和政府部門(mén)的對(duì)策也或隱或現(xiàn)急功近利的色彩。對(duì)于科技的突破能夠帶來(lái)巨大的經(jīng)濟(jì)效益似乎沒(méi)有任何懷疑,擔(dān)心的僅僅是我們能不能在技術(shù)上趕上這班車(chē)。
最近重啟的這場(chǎng)爭(zhēng)議,至少再次提醒我們光環(huán)可能還存在的另外一面。特別是如果大量吸收中低端勞動(dòng)力的制造業(yè)發(fā)生重大的破壞性創(chuàng)新,就業(yè)可能就是無(wú)法回避的挑戰(zhàn)。這不僅影響流水線上的簡(jiǎn)單勞動(dòng),而且智能化高度發(fā)展也將對(duì)管理層帶來(lái)沖擊。更難以預(yù)料還有新技術(shù)造成結(jié)構(gòu)變化所帶來(lái)的深層次影響。德國(guó)最大的戰(zhàn)略咨詢公司羅蘭貝格今年3月份發(fā)布關(guān)于工業(yè)4.0的研究報(bào)告,甚至提出了制造業(yè)可能碎片化、將來(lái)IT或通訊公司可能成為制造業(yè)領(lǐng)袖這樣的極端遠(yuǎn)景。
即使我們堅(jiān)信新技術(shù)和產(chǎn)業(yè)革命可以帶來(lái)新一輪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和繁榮,這個(gè)過(guò)程本身肯定將充滿我們至今知之甚少的不確定性。
而與這場(chǎng)爭(zhēng)議的主角西方國(guó)家不同,中國(guó)更有一些自己獨(dú)特的議題。在我看來(lái),與這場(chǎng)正在到來(lái)的產(chǎn)業(yè)技術(shù)革命相伴而行的,還有一個(gè)增長(zhǎng)方式轉(zhuǎn)變和企業(yè)改革的重任,所以我們決不能只是被那些技術(shù)新名詞搞得暈頭轉(zhuǎn)向了。
[責(zé)任編輯:李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