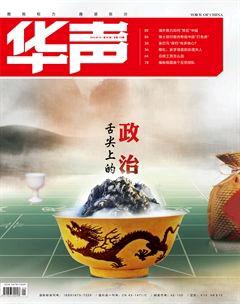境外勢力如何“策反”中國
田雄獅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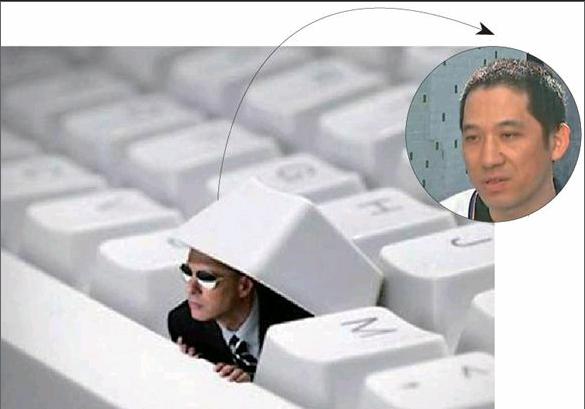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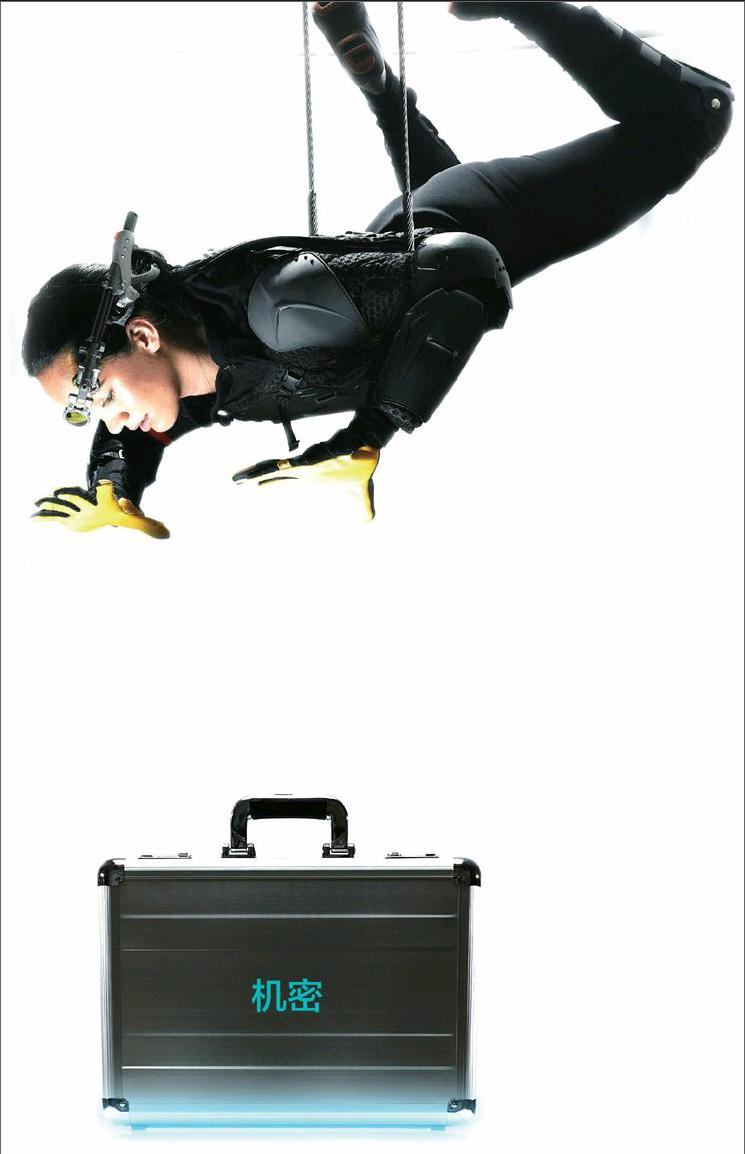
廣東省安全機關5月4日公布一起境外情報機構通過網絡策反境內人員,竊取中國軍事機密的案件,案犯李某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記者從國家有關部門獲悉,同一境外情報機構近年針對中國大陸學生實施了數十次網絡策反活動,境外間諜以金錢誘使涉世未深的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參與情報搜集、分析和傳遞。來自權威消息源的案例顯示,多數學生在網上求職或網聊過程中被境外間諜盯上,他們最初提供信息時并不知情,但部分人在覺察對方身份的情況下仍因貪利而持續配合,直至被國家安全機關依法處理。
三十多年來,被境外機構策反的中國人中既有普通民眾,也有學者,官員,將軍。他們是如何被拉下水?拉他們下水的“境外勢力”又究竟指誰?
一篇網上求助帖引來“釣魚”者
求職求助的學生、調研邀請、計件發酬,策反總是在看似合情合理的場景中揭開序幕。2012年4月,當廣東省某航海學校專科生徐鵬考入該省某重點大學時,他在QQ群里發了一條求助帖。徐鵬的父母都在農村,家里生活不寬裕,他在網上“尋求學費資助2000元”。
不久,一網名為“Miss Q”的人回帖,詢問了徐鵬的全名、手機號、就讀院校和專業,然后表示愿意提供幫助。徐鵬喜出望外,把銀行卡號告訴對方,第二天就收到2000元人民幣匯款。徐鵬按這名“好心人”的建議,寫了收條,用手機拍了照,然后通過QQ傳給對方。徐鵬當時知道的是,“Miss Q”是“一家境外投資咨詢公司的研究員”,需要為客戶“搜集解放軍部隊裝備采購方面的期刊資料”,希望徐鵬協助搜集,作為資助學費的回報。徐鵬痛快地答應了,但沒能在航海學校的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而“Miss Q”也未強求。
這么好賺的錢,讓當時正在實習的徐鵬心理發生變化,他開始覺得實習“又苦又累錢又少”。2012年5月,徐鵬主動聯系“Miss Q”,對方向他提供了一份“田野調研員”的兼職,月薪2000元。徐鵬所在的廣東某大城市有一個軍港碼頭和一家歷史悠久的造船廠,他的“調研”工作就是到軍港拍攝軍事設施和軍艦,到船廠觀察、記錄在造在修船艦的情況,并將有船艦方位標識的電子地圖做成文檔,提供給“Miss Q”。雙方約定的傳送方法是,手機短信約好時間,這邊徐鵬把加密文檔上傳至網絡硬盤,那邊“Miss Q”立即從境外登錄下載。
一年后案發,徐鵬23歲。徐鵬后來承認,做“調研員”不久,他就意識到對方是搜集我軍事情報的境外間諜。他曾因內心極度不安主動放棄學校的一些榮譽,但利誘當前,又難以拒絕對方。2013年5月,徐鵬被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審查。
有權威渠道的匿名人士告訴記者,境外情報機構最初與學生接觸時,只提簡單要求,如到圖書館查找資料、訂閱學術期刊等,這些公開信息大多難以具備情報價值,但持續聯系的過程,尤其是定期酬金支付極易讓年輕學生形成依賴。隨著要求具體深入,多數學生會覺察到對方身份,一些學生主動終止聯系,一些人被威脅,也有人因貪利而繼續配合。
該境外情報機構重點選定大陸一些地區和高校,勾連策反特定專業在校生。在涉及北方某重點航空航天院校的一起策反案中,該校一名大四學生在校內論壇找兼職時,看中一則待遇不錯的“網絡兼職”信息,并主動發郵件聯系“雇主”。之后5個月里,這名學生多次向網名為“吉娜”和“Roby”的兩名境外間諜提供航天、航空、船舶、武器裝備類學術資料,并幫助他們訂閱和翻拍內部學術期刊。
鼓動報考涉密崗位公務員
廣東方面5月4日披露的案件中,境外間諜“飛哥”利用“網上書店”、軍事愛好者網站等渠道,7年來在廣東收買利用12人,在全國20余個省市收買利用40人。記者從權威消息源獲取的資料顯示,“飛哥”所屬的境外情報機構,同樣利用網絡渠道收買利用大陸學生。從近年的多起案例看,該境外機構以20歲左右的在讀高校生為主要目標,借助網聊工具、校園論壇、招聘網站等物色“調研員”。“受聘”學生先做一些搜集、整理、匯總的活兒,即便提供的信息不具價值,也會定期收到數百或數千元酬金。
一名安全官員告訴記者,當學生對這種快速的收益上癮后,該間諜機構將進一步安排更有針對性和機密性的信息搜集任務。如果學生不從,對方會威脅將此前的聯系內容和金錢交易報給中國安全部門。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學生被發展為“情報員”,領取固定月薪,當這種控制力達到一定程度,境外情報機構開始安排和支配學生的就業選擇和發展道路。
2012年下半年,浙江某重點大學畢業生宋飛在招聘網站投遞簡歷。12月初,“市場研究公司專員李華”發來郵件,邀宋飛加盟。李華稱,該公司主要業務是為在大陸投資的外資企業提供信息服務,宋飛的工作是搜集中央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資料和撰寫調研報告,報酬在2000元—5萬元不等,高質量報告獎金豐厚。
宋飛先后接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農村工作會議、行業重組、能源產業發展等10項“調研課題”,他通過學校圖書館、論文期刊數據庫、校內學術講座等渠道搜集資料,向李華提交多份“研究報告”。其間,李華曾讓宋飛到他所在高校臺灣研究所搜集兩岸關系材料,但宋飛不熟悉臺研所的人事和情況,沒能做成。
李華的要求逐漸深入,他要宋飛積極培養人脈,從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智庫、學者那里抓幕后、聽觀點,“拉關系的錢全由公司出”。2013年1月,宋飛著手報考公務員,李華表示全力支持,為讓宋飛全心備考,還暫時停掉“調研課題”,并提供每月3000元生活補助。李華還對宋飛報考的基層公務員崗位提出異議,因為“對公司獲取信息沒有幫助”,建議報考省級機關、智囊和研究部門。
上述安全官員表示,鼓動境內學生報考省級或國家公務員、安全部門、軍情機要等涉密崗位,是境外情報機構的慣用手段。案發后宋飛承認,李華是“放長線釣大魚”,將來會要求他提供更多內部機密信息。
高校“窩案”令人心驚
據統計,2012年以來,僅由該境外情報機構實施、證據確鑿、被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審查的網絡策反境內學生案件,就有近30起,遍及中國大陸十余省市。有接近情況的匿名人士告訴記者,之前境外間諜也對年輕學生下手,2012年以來校園案發率上升,“這些機構越來越不擇手段,利誘對象包括未成年人”。
記者梳理近年相關案例發現,涉案學生初期防范意識薄弱,中后期無法克制貪念,且對自身行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認識不足。目前,有效的安全觀教育在校園和社會缺失。記者進行簡單的網絡搜索,僅能獲得極個別境外情報機構在中國大陸活動的當代案例,且信息簡單,難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網上倒是流傳著一份2009年上半年出現的“中國民間防間諜不完全手冊”。這份來源不明的手冊介紹了當代間諜活動的基本手段,以及美國、歐洲、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針對中國大陸學生和留學生的策反思路,一度受到熱捧。
傳統上,情報機構主要靠金錢利誘,以情色或經濟問題要挾,許諾未來和個人成就,以及通過冷戰時期相當管用的意識形態訴求等手段勾連策反,被發展的本地情報員負責搜集、刺探、竊取、分析信息,其中部分人負責前方人員和后方總部間的信息傳遞,術語稱“交通”。情報員也會策反他人,拓展情報來源。
網絡策反學生的案例中,境外情報機構主要以積極兌現酬金的形式吸引和黏住學生,兼以要挾等手段,但不見面。涉案學生多數是個體行為,較為惡劣的案例中,境外間諜會誘導、建議學生發展自己的同學。2008年四川成都某高校就發生一起“窩案”:本科生吳某通過Skype找英語聊友,結識自稱“外籍華商”的境外間諜。吳某介紹同學馮某加入,馮某又在校內論壇發布招聘廣告,吸收同校研究生劉某、趙某。4人均在聯系初期即覺察到對方“網特”身份,但仍簽訂“保密工作合同”,先后提供國內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大量內部期刊資料,其中包括多份“秘密級”刊物。案發時,4人共獲得報酬4萬余元。
通常,境內涉案學生短期內能接觸到的核心信息和人員都比較有限,多數人案發時尚未造成嚴重的現實危害,有關部門強調,對“認罪悔過態度較好”的年輕學生要教育挽救。對此,國內安全部門官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和其他社會人員涉案情況不同的是,若發現學生犯案,有關部門往往會第一時間警示學生,要求其中止與對方聯系,而不會刻意放線,這么做“全部是出于對孩子的保護”。
2011年湖南湘潭曾發生一起性質較為嚴重的策反案,涉案人年僅16歲,但作案情節包括竊取政府文件和為境外間諜傳遞加密資料。這名安全官員說:“境外間諜機構利用年少懵懂的未成年人去做明確構成犯罪的‘交通'角色,非常惡劣。”
最初,這名涉案的張姓高中生在網上謊稱自己畢業于軍事院校,境外間諜主動與他接觸,要求提供部隊內部文件。張某收到對方匯來的400美元后,編造了一份“演習計劃”,但難以蒙混過關。張某于是改口稱,自己真實的工作單位是教育局,之后根據境外情報機構要求,他先后組織多名同學進入教員辦公室,竊取“紅頭文件”。
按對方指示,張某開始接收快遞包裹,并對包裹內夾藏的存儲卡內加密資料進行處理,通過電子郵件發送出去。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信息顯示,這些資料是一名被境外機構策反的我重要單位人員出賣的涉密資料。
案發時,張某總計收取報酬約合人民幣2萬余元,其行為已涉嫌犯罪。國內有關部門接受采訪時表示,考慮到張某年齡較小,希望他能改過自新、擁有未來,“我們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他進行了從輕處理”。
解放軍少將也曾被策反
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告顯示:目前,網絡泄密已占泄密事件總數的七成以上,而且正呈高發之勢。美國情報部門認為,現在很多極有價值的情報都可以在互聯網上找到。美國軍方研究中國軍情的權威文件——《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中,有相當一部分信息取自中國軍迷們發布的網絡信息。有的軍迷為了炫耀自己的軍事“功底”,知無不言,有的軍迷想通過“爆料”吸引人氣,千方百計地搜索各種信息,甚至不辭辛苦進行現場勘查,拍攝一些“猛圖”,無形中為海外情報機構提供了便利。
兩岸關系緊張時期往往也是臺灣間諜的活躍時期。而大陸對臺灣間諜網絡的重創恰恰源自臺灣地區領導人自己的“泄密”。1995年至1996年“臺海危機”爆發,大陸對臺軍演,李登輝公開說“大陸所發的是空包彈”。這一言論引起大陸安全部門高度警惕,由此揪出潛伏多年的解放軍大校邵正宗和少將劉連昆。
2003年,陳水扁為求連任,在高雄“扁友會”成立大會上“精確”地指出大陸沿海地區的導彈部署數量。大陸安全部門迅速行動,將“軍情局”上校李運溥建立的間諜網連根拔起,另一名解放軍少將劉廣智也因涉案其中被捕。
如何防止網絡泄密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國家以及臺灣等一些境外間諜機構,針對大陸的網絡間諜活動日趨活躍,采用的方式手段也日趨多樣化,目的是套取大陸的政治、軍事、經濟以及企業的情報信息。1993年前后,大陸民航共發生劫機事件21起,成功10起,劫機目的地均為臺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臺灣搞的策反輿論宣傳,給劫機犯造成“只要到了那邊,金錢美女要啥有啥”的印象。
而出于政治目的,境內外反華勢力往往相互勾結,在中國互聯網上大肆散播謠言,蠱惑人心,并竊取有價值的情報。2009年3月份,國家有關部門揭露了一起美國官方機構與“藏獨”組織聯合針對中國的網絡行動計劃——“哲瓦在線”,“哲瓦在線”的任務很明確:利用互聯網對中國網民進行煽動蠱惑,滲透策反,制造謠言引發動亂并搜集中國情報。
“網絡間諜”的職能不局限于竊取情報,制造謠言、蠱惑人心、煽動鬧事也是它們的重要目的。曾有香港媒體報料說,美國情報機構每年都要花上數千萬美元,資助一批中國人對中國網民進行思想滲透、策反,這些所謂的“網絡漢奸”多是國內失意者,以及無固定工作人士;他們出沒于各大中文論壇、門戶網站,定期領取美國人支付的薪金。他們的活動也有規律可循:每每在中美、中日發生矛盾沖突時,互聯網論壇上造謠挑撥國家關系的言論就會悄然冒出,唯恐天下不亂。
據知情人士透露,境外間諜組織多在互聯網上尋找有軍政背景的網民,一旦選定目標,就通過各種方式策反,將其發展成自己的間諜。有退伍軍人僅僅因為在聊天室說得多就被境外情報部門盯上,這些掉入境外網諜陷阱的網民,自然逃脫不了法律制裁的命運。而此時,他們的“上峰”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要杜絕網絡泄密,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有保密內容的電腦和互聯網物理隔絕,原則就是“上網不涉密,涉密不上網”,再加上“涉密電腦不得使用移動存儲介質”。雖然絕大多數重要單位都制定了符合這類網絡保密原則的嚴格規定和制度,但很多單位都普遍存在網絡泄密的情況。尤其是大學和一些學術機構網絡泄密比較嚴重。一些學者參與國家重大課題、重要科研項目,有的是政府高層決策部門經常咨詢的專家,但他們的網絡保密意識比較淡薄,不少人圖工作方便,很多機密文件都存在隨身攜帶、常常上網的電腦里,幾乎等于向境外情報機關敞開泄密之門。
而在商業領域,相關單位“戒防”意識更加淡薄。加之我國刑法對商業間諜案件的懲罰過輕(最高獲刑7年),相較巨額收益,導致犯罪成本極低。近年已成泄密重災區。
出國談判中,核心人物所住的酒店被安裝竊聽器,手機號碼被偵聽,出行被跟蹤,這都是外國對手慣用的手段。而我國安全部門和保密局的相關培訓,參加的卻基本都是中層干部,而泄密的恰恰主要是高層,因為只有他們才掌握最核心的秘密。
國家保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只有20%左右的企業,將商業秘密交由“知識產權部門”或“法律部門”這樣的專門機構進行管理,約42%的企業由“財務”、“辦公室”、“人事”等部門兼職管理,更有約37.6%的企業沒有設立或明確管理商業秘密的部門。
網上被“釣魚”,誤中情報人員的圈套,也是造成網民泄密的重要原因。據一位曾從事過互聯網情報搜集的工作人員介紹:他們主要從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間的網站、論壇、聊天室公開發布的信息中搜集情報。為了引誘軍迷更加“開放”,他們故意稱其不懂軍隊,在網友的憤然回應中,竊取具有更大價值的信息。
無論是通過互聯網或者其他手段,可以想見,針對中國的竊密策反活動并不會一兩起案件的曝光而停止,要作好防范,除了需要國家的重視和行動,也需要強化個人戒防意識,嚴堵泄密漏洞。
資料來源:搜狐網、新華網、《環球時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