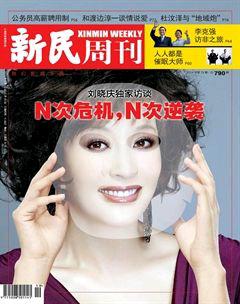抵制杜汶澤與“地域炮”
不小可
有句話說的是:許多網絡罵戰,不管開頭因為什么樣的事吵起來,到頭來都會變成開地域炮。有太多微小的理由能讓我們一棒子打死一船人——被一個帶外地口音的人插了隊,就說某地的人素質真差;身邊有幾個同鄉人恰好都有些城府,也會被迅速歸類。有個網帖叫“說說外省人對老家最大的誤會是什么”,在里面你能看到各種像笑話一樣的地域偏見。
一些根深蒂固的錯誤印象,再加上一點想當然,地域誤會就這么輕而易舉地產生了。而在所有的地域論戰里,又數港臺和內地的誤解最為頻發。杜汶澤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周杰倫也炮轟過“大陸歌迷”,說他們“素質很低,只會跟風,好像一棵墻頭草,他們根本不懂我的音樂”。臺灣新聞里講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娛樂節目里講大陸女生“連包包是什么樣子都沒見過”……
在這次的“杜汶澤事件”中,罵者與挨罵者的思維里,都脫不開這種“想當然”。杜汶澤在嘲諷某些網友素質低、只夠錢去上網的時候,并不需要進行全國經濟或者道德普查,就像一小部分香港人只需要一個近在咫尺的窮親戚就能對整個內地經濟下判斷。而網民在群起攻擊杜汶澤的時候,也不需要事先調查大部分香港人對內地的態度,只需要一個杜汶澤在某一時刻針對某一部分內地人的一小句批評就夠了。
隨著此起彼伏的“杜汶澤滾粗內地”,相信即使是此前根本沒有Facebook賬號、或者連杜汶澤原話截圖都沒看到過的人,也會在電影院看到宣傳海報上出現“杜汶澤主演”的那一刻,萌生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正義感,好像抵制了他演的電影,就為內地人在香港人面前掙回了一番面子。
2012年時,陳奕迅也遇到過同樣的聲討。當他在歌里唱:“跌跌碰碰要到醫院插隊接生”,“蝗蟲螻蟻,尋求默契,相稱禮貌”時,曾引起震怒,讓無數人叫他“滾粗內地”,“要把他的歌都刪除”。但是在一部分港媒那里,陳卻成了“為港人發聲”的直言人物。同樣,杜汶澤在遭遇內地網民抨擊時,也受到了一部分香港網民的支持。說到底,杜汶澤、陳奕迅,還有近年來甚囂塵上的代購奶粉、海港城D&G阻止港人拍照、內地幼童當街便溺等等新聞事件,追根溯源都是同樣的發端:不是大陸人素質差不差的問題,是資源焦慮。
驕傲的另一面,往往是自卑。杜汶澤的矛盾也是很多香港人的矛盾:本土市場縮小,內地潛力無限,一方面覺得自己家鄉最好,一方面又家道中落不得不背井離鄉,諸多不慣諸多磨合。而內地網民對這些人的敵對情緒之所以那么容易被煽動(五一檔期歷來是電影片方必爭之地,把杜擠走自然有人得利,有利的地方就有人舍得出力),也變相證明了雖然已經富起來有底氣挺直腰桿罵回去,但心態到底還一時走不出積貧積弱時代的思維定勢:你說我窮,我就把錢堆起來給你看;你說我素質差,我就把你趕出我的領地。
當然你也可以說,每個人都有自由,你有言論的自由,我有不看你電影的自由。但這就像爭論“幼童當街便溺”和“當街拍幼童私處”哪個更沒素質一樣,到頭來一定是兩敗俱傷,唯一有建設性的是討論“如何解決香港街頭如廁難”。
事到如今,最傷的其實是電影投資方。杜汶澤主演的《放手愛》雖然本來也屬于“一周下檔”的小片,但總不至于像現在這樣票房只收一兩百萬,以至于片方不得不發出與他斷絕關系的聲明:“確實是我們的失誤,用了一個沒有藝德的演員。”聽起來有點絕情,但這也恰恰是杜汶澤此次最錯的地方:忽視了職業操守。
雖然他自己在Facebook上表示不在乎失去大陸市場以后的金錢損失:“你說給我五億賺,我夠膽要,但是改天我沒得賺,也行!因為對著人民幣一時,對著自己良心一世。”但對于電影片方來說,他就是“代言者”,身為代言一方,有必要慎重自己的公開言論,這既無關人品無關智商也無關個人政見或審美趣味,純粹是一個“代言者”的職業操守和“媒體情商”——杜汶澤的言論,就像為可口可樂代言的明星喝起了百事,在他自己和一些擁躉看來可能是真性情的表現,但論職業操守和媒體情商,則是敗筆無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