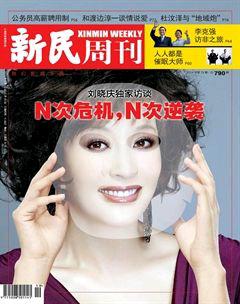何森:回歸與超越
王悅陽


提起畫家何森,熟悉當代藝術史的一定會記得他那些帶有強烈表現性色彩的畫面以及那些“頹廢”、“墮落”的女孩形象。作為上世紀90年代的新生代藝術家成員之一,何森與尹朝陽、趙能智、忻海洲等藝術家一起共同代表那個時代西南藝術青年們對于社會的看法——他們并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熱衷于將自己的藝術與政治發生直接的聯系,也不想與體制發生瓜葛,他們在激烈的社會演變中,選擇了自我放逐與逃離。當然,由于具體成長環境的不同與偶然性的存在,在被問及為何選擇如此的態度觀看世界以及進行創作時,他們給出的解釋也不盡相同。而何森給出的答案是——也許是自己的天性趨于寧靜,或者是對于復雜社會的游離。
何森曾是“傷痕繪畫”的代表人物。其以人物為主的照相寫實主義的油畫作品,細如發、輕似夢的惆悵的紅灰色調,傳遞出或傷感、或激越、或凄迷的情緒。何森自言其作品表現的是“對成長的恐懼和對現實的逃避”。而如今的何森,面目清癯地坐在龍門雅集名為“晚歸朝發”的個人畫展之中,眼神平和淡然。“我承認,時間改變了我很多,或許我老了,也或許,時代改變了我們。”
找尋傳統
龍門雅集展出的十余幅大大小小的作品,很難與之前的頹廢女孩掛鉤。純粹以傳統宋元水墨畫為原型,油畫筆取代毛筆,但覆蓋著濃重的油彩的山水畫中,依然可以看到作者強烈的情緒。在當代思維與傳統意境中間,交融的嶄新繪畫手法,展現時空交錯、今古映照的中國當代藝術新世代篇章。
從2004年末、2005年初起,何森將一張張為人熟知的古代大師作品“搬入”自己的畫面。這在眾多同行眼中“冒險”的行為,何森做得義無反顧。何森并非不顧及成熟的市場與既有的當代評論體系,只是他更愛自由地創作,正如他所說“天馬行空”地作畫與遵行自我意愿的前行才是最高享受。而這種“自由”也是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能夠為當下社會提供的最有意義的價值觀。
事實上,當何森剛開始將馬遠、徐渭等古代繪畫大師的山水“搬入”自己的畫面時,許多人表示了擔憂。這是一次極大的冒險:放棄熟知的當代圖示,進入相對陌生的傳統領域,對于任何一個畫家來說都不輕松,尤其是像何森這樣一位已經擁有一定影響力和成熟市場的藝術家。但何森仍然堅持了自己的實驗,并且與藝術史中多次發生的“復古運動”不同,何森的“搬入”并非照抄,也不是恢復古人的趣味。在經歷了五四、新中國成立、“文革”等等政治文化運動后,傳統文化在當下除了殘存的零星片段,已經失去了體系性的影響,雖然它在逐步恢復,但仍需時日。何森本人也毫不諱言自己對于傳統文化知識的缺失,他將自己的行為定義為一種修煉與體驗——在臨摹古人的山水時,他也在體驗畫面背后隱藏的古人心境。這種體驗一方面幫助他逃離紛繁喧鬧的現實,同時也為他打開了一扇窗口用以觀察在傳統文化中古人觀看理解世界的方式。
其實,在當代藝術領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再認識并非只有何森一人。作為“傷痕藝術”的代表,何多苓早在1990年代就開始將傳統視覺中的大量元素融入自己的創作;周春芽則將中國文人繪畫中偏愛的石頭與桃花作為自己的創作主要圖示;而陳丹青把古代的山水和名畫以書籍的方式搬入自己的畫面;曹靜平、沈娜也在近期開始使用自己的方式繪制為人熟知的歷史圖符;青年藝術家郝量則一直堅持以南宋院體畫中的工筆描繪當代情景……在這種種變化的背后,是中國本土文化的日漸復興。
對此,評論家呂澎也特別著重指出:“作為畫家,何森清楚中國繪畫史上的圖像的特殊性,當太多的畫家利用意識形態濃厚的圖像來解讀當代問題的時候,何森將出發點放得更遠,直接通過與古人發生關系來擺脫政治聯想與意識形態反映論的習慣。這是新世紀新繪畫的一種新的方向,我們在周春芽的桃花、曾梵志的風景里看到了敏感的藝術家們已經徹底地退回到歷史的源頭,他們從古人的作品中感受恒定的氣質,他們敏銳地感到這個探索路線也許能夠徹底地與西方藝術的文明背景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全球化資訊即刻就能夠獲得的今天,尋求真正的個性與特殊性再一次成為藝術家新的目標,在這個目標的要求下,觀念必須與感受相結合,當代應該與歷史聯姻。”
從回歸到超越
出身于軍人家庭的何森,從小就不是一個愛“熱鬧”的孩子。相比較枯燥的應試教育,何森毅然選擇了繪畫的道路。在試圖考入四川美院附中未果后,何森進入了美術職高。雖然是時“文革”的影響并未消除,“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美學仍然是社會的主流,但幸運的是,在1980年代初,“傷痕美術”與“鄉土寫實主義”給何森帶來了新文化的曙光。在經過重重的努力后,何森進入了四川美術學院學習,并接受正規的學院訓練以及西方現代主義藝術與文化的洗禮。而此時中國傳統的文化,對于何森來說,更多只是幾個古代畫家的故事或者是已經不具有現代價值的陳舊之物——王廣義在1988年黃山會議中提出的一切“古代藝術”或者“古典主義”都應當是被清理的人文主義熱情,因為那是虛假與脫離實際的。
直到2002年,早已因“頹廢女孩”系列揚名的何森因為巴黎的個展去了歐洲,并借此機會遍覽法國、德國、意大利著名的美術館與博物館,瀏覽了大量的西方美術史中的經典作品。在此之后,他又多次奔赴歐洲與美國,遍覽經典。他在對西方的藝術表示由衷欣賞與稱贊之時,也逐漸對將西方的藝術作為中國當代藝術標準與歸途的看法產生了疑問,他開始認為中國當代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的內核才能真正地發展下去。
也許是強烈的文化形態對比所致,當何森在西方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形態時,產生了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感受——“忽然覺得之前學習和看到的那些西方藝術一下就消失了,那種震撼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是從來沒有過的。”在此影響下,何森在2005年開始了自己的嘗試。
無疑,這是一種回歸,更是一種超越。誠如何森自己所說的那樣:“每個積極奮力前沖的人腦子里大概都藏著個格瓦拉似的英雄,每個謙恭緘默后退的人心里幾乎也住著個嵇康般的隱士,這里根本無關榮耀與羞愧、自信與自卑、輝煌與黯淡,只跟天性和參照有關。這些年來,我從內心越來越不喜歡像‘國際化的‘當代藝術那種作品,因為這在漸漸成為有法可循的接近中國美術院校標準素描石膏像作業的東西。如今的藝術現實有點荒謬:我看很多形態大膽前衛的作品往往覺得似曾相識、卻能在不少方式保守的作品中發現創造性。對我來說回望和前瞻本身就是分割不開的一回事,只是我們不斷賦予它新的意義而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