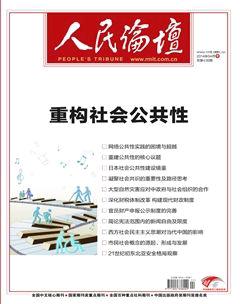網絡公共性實踐的困境與超越
互聯網的快速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公共性的結構轉變,并為公共性創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實踐空間。這一空間吸引各種不同觀點的人參與其中,就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和公共事務展開討論和行動。由于其在人們日常社會生活中逐漸扮演了無所不在的角色,因此成為推動社會結構和行為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互聯網拓展了公共性的實踐空間
公共性是一個歷史性概念,雖然其涵義極其豐富,且一直處于變動之中,但公共性仍有被大家強調的基本內涵,即在國家權力之外,公民自由討論公共議題,自愿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這種公共性實踐,是在具有公開性、批判性和合法性特征的公共行動空間中展開的。阿倫特把人類活動區分為勞動、工作和行動三種形態,認為公共領域是由行動所塑造的,它以道德同構和政治平等為根本前提,以言語、勸服而非暴力為基本手段,表現為公共場合對話的公開性,其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實踐和政治參與。阿倫特強調,這種公共領域的實現,需要公共性借以呈現自身的無數視點和方面的同時在場。①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作為行動領域,是一個非個人的交往、信息和輿論領域,它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在公共領域中,人們在理性辯論的基礎上就普遍利益達成共識,以實現對國家活動的民主控制。②而湯普森認為,公共性作為一個由行動和事件所建構的能見空間,是經由符號交換,在公共領域中以能見性的過程而呈現的。③
在現代社會中,公共性與媒介有著密切聯系。哈貝馬斯肯定了印刷媒介對于公共領域的積極意義,但認為電子媒介阻礙了有距離的思考和批判性的討論;互聯網可能會肢解現有的公共領域,使富有意義的聯系化為烏有。與哈貝馬斯不同,湯普森強調互聯網創造了一種新形態的公共性。這種新公共性是一個象征形式的對話空間,不局限于特定的時空地點,并具有結構開放和參與者不在場的特征,是一種協商式的中介公共性。
從技術角度來說,網絡空間是一個開放、自由、匿名、彈性、去中心、網絡化的空間,這一技術空間為新的社會行動提供了物質基礎。正如卡斯特所說,一旦經由人們的社會行動,將互聯網的這種技術特性擴展滲透到整個社會,就會導致社會生產、經驗、權力和文化過程的實質性轉變。④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的快速擴張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公共性的結構轉變。互聯網塑造了一個不需要身體共同在場的虛擬公共空間,因而大大拓展了公共性的實踐空間。
首先,互聯網為公共性創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實踐空間。網絡空間不僅是一個技術空間,而且是一個由共識、想象和興趣凝聚而成的新社會空間。在這一社會空間中,各種傳統的社會邊界和社會機制正在發生轉變。互聯網通過對各種現實社會邊界的不斷消解和重建,創造了一個新的行動空間,吸引各種不同觀點的人參與其中,就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和公共事務展開討論和行動,這是一個比現實社會空間更加廣闊、開放、自由、靈活、自洽的公共空間。
其次,互聯網使信息獲取和傳播變得十分容易,并因此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意識,增加其政治和社會寬容度。哈貝馬斯認為,政治信息的獲取是公民行為產生的前提。網絡媒介的兼容性、交互方式多樣性等特點,使其匯集和傳播的信息十分龐大和豐富,這有助于網絡使用者擴展政治視野,增加政治知識,減少政治冷漠。而且與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不同,互聯網不僅使巨量信息的快速、廉價傳播變得可能,并極大地方便了網絡使用者的主動信息發布。這種主動發布十分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提升公民參與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此外,網絡空間中多元政治信息的呈現、傳播和交匯,各種不同觀點的分享、爭論、競爭和交鋒,也有助于增強人們對不同意見、觀點的容忍力與接納力,培育公共性建設所需要的寬容精神。
最后,互聯網具有強大的社交功能,網絡互動的便捷、低成本、跨時空限制、匿名、開放、方便在線交流等特點,特別適于培植社會資本、擴張社會網絡、發展集體認同、增進群組成員之間的信任。網絡互動不僅有助于擴展人們的社會關系網絡,而且有助于地理上分離的人們,組成各種類型的在線社會團體,如興趣小組、宗教團體等,并幫助團體成員展開有效的社會溝通、社會動員和社會支持。這種在線社會團體有助于促進團體成員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同時,網絡互動建構的松散關系網絡能夠為人們提供不同類型的社會資源,對于促進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也有積極的正向影響。
網絡空間中公共性實踐的類型
在網絡空間中,公共性實踐在多個維度和層次上得以呈現。其中最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網絡公共輿論。作為民意的一種綜合反映,網絡公共輿論常常是由某種公共利益或某個公共事件引發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眾對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公共事件的情緒、意愿、信念、態度和意見。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一個最重要的社會輿論場,一種全新的輿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在網絡空間中,公共輿論獲得了最直接的表達空間。通過在網絡空間中議論時政、針貶時弊、評論政府,人們竭力監督公共權力、伸張公共道德、保護公民利益,充分體現了廣大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當前,微博、微信、博客、網絡論壇、社交網絡、即時通訊等,是形成和傳播網絡公共輿論的主要場所。那些社會關注度和敏感度較高的公共事件和公共議題,如公民權利、公共權力、環境污染、官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公平、住房醫療等,容易引起網民的強烈、持續關注,從而引發公共輿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網絡公共輿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網民有可能因為對某一公共事件的共同意見和共同情感而凝聚在一起,形成規模龐大、邊界模糊、聚散迅速的意見群體。⑤這種意見群體沒有確切的規模和形態,也沒有明確的邊界,常常因為某一事件或議題而聚合,又隨著這一事件和議題的解決或轉移而消散,但卻隨時有可能因為一個新事件或新話題重新聚合。這種意見群體對公共事件的過程和結果往往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從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劉涌事件”、“SARS危機”,到后來的“周老虎事件”、“廈門PX事件”、“甕安事件”等,我們都可以看到意見群體的身影。網絡公共意見群體的興起,明顯地改變了傳統的公共輿論結構,使普通網民在權力監督、真相揭露、社會動員、經驗傳遞,以及推動政府信息公開等方面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網絡政民互動。近年來,網絡問政已經成為政府與民眾互動、交流的一種重要形式。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圍繞國計民生問題,在網絡空間中與網民展開互動和交流,聽取民意,接受網民監督,甚至廣泛吸取網民對社會問題的意見。這不僅拉近了官民距離,而且增加了民眾了解政府、反映民聲、參政議政的機會,推動了政府決策的公開化和民主化。其中政務微博是近年來網絡政民互動中最引人注目的形式。在政務微博中,政民互動越來越以民眾為中心,政府機構或政府官員已經開始習慣于放下身段,貼近網民,以網民熟悉的語言與網民進行直接互動,這不僅有效地降低了政民交流的成本,減少了政民互動中的信息損耗,而且促進了政民雙方的相互理解,增進了政民之間的情感互動,使政民互動更加真實、更加順暢。
互聯網給予了公眾充分的話語自主權。借助網絡這一公共話語平臺,網民可以暢所欲言,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意見,并通過交流和協商形成一致的看法,從而凝聚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在這一過程中,那些具有敏銳和精準的判斷力、能對信息進行深層解讀的網絡意見領袖,往往對信息匯集、信息快速擴散傳播、網絡意見群體的形成,起著一種引領作用。因此,在政民互動中,政府需要建立起與網絡意見領袖的有效互動機制。只有處理好與網絡意見領袖的關系,政府才能有效引導網絡公共輿論,切實推動網絡問政的良性發展,推動網絡公共性實踐在參與主體、互動模式、批評監督、參政議政方面,獲得實質性的拓展。
網絡公民行動。互聯網的發展不僅方便了網民參與發貼、轉貼、評論、互動等在線行動,而且使網民可以借助網上銀行、支付寶等網絡金融工具方便地參與網絡捐款等公益性、慈善性公民行動。可以說,互聯網已經創造了一種新的公民行動方式,網民不僅能夠在網絡空間中通過言論表達公共性理念,而且能夠通過具體的行動踐行公共性理念。
網絡空間是一個既連接又隔離的空間,它可以讓網民在身體不在場的情況下參與社會行動。身體不在場是網絡行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正是網絡行動的這一特征,使人們通過網絡互動建立一種陌生人之間的社會信任和社會共識成為可能。近年來,從“微博打拐”到“免費午餐”等網絡公民行動,正是有效地利用了網絡行動的這一特征,從而成功地動員了大量網民參與到網絡公民行動之中。可喜的是,“免費午餐”行動不僅得到了廣大網民的肯定和支持,甚至獲得了國家層面的關注和肯定,并進一步引領了國家行為。在行動發起半年后,國務院決定每年撥款160多億元,以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實現了公民行動中國家與社會的良好互動和合作。
網絡公共性實踐的困境與超越
互聯網降低了公民進入公共空間的門檻,拓展了公共性的實踐空間。在網絡空間中,公民可以突破現實社會的時空限制,廣泛參與公共討論、充分表達自己的公共意見、超越在場限制參與公民行動。然而,互聯網對公共性實踐的效應是復雜的,因為網絡使用者是能動的個體行動者,他們在與開放、自由、匿名、彈性、去中心的網絡空間遭遇后會以不同方式進行網絡表達,從而導致網絡公共性實踐呈現出復雜多元的面貌。網絡空間在拓展公共性實踐的同時,也在某些層面限制了公共性實踐的充分展開。
首先,互聯網雖然拓展了人們的信息交流和社會互動,但是人們在網絡空間中的聯系常常呈現出一種“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同質性偏向。除了大量陌生人之間的淺層次交往外,互動和信任程度較高的網絡交往,大都局限在那些興趣相同、觀點相似、利益一致的人群之間。網絡空間中信息交流和社會互動的結果往往是進一步強化了人們原有的意識和立場,仿佛與自己不同的意見都不存在。桑斯坦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回聲室效應”。⑥回聲室效應的一個后果就是造成“群體極化”,即各種對立的觀點越來越走向極端,不同團體之間、團體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越來越明顯,從而增加了不同意見群體之間的協調難度,甚至造成網絡公共空間的切割和碎片化。這意味著互聯網雖然能夠將不同的社會群體吸引到同一個信息和行動平臺中,但無論在討論議題的選擇上,還是在行動方向的抉擇上,互聯網并沒有能夠減少群體之間的分化與隔閡。而一個健康發育的公共領域需要各種不同意見、觀點之間的理性交流與討論。
其次,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社會后果是導致傳統的社會邊界和社會機制發生了轉變,互聯網創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社會空間。⑦在這一虛實交織的網絡社會空間中,個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前臺行為和后臺行為之間的邊界變得不再清晰,從而引發了個人行為公開化、后臺行為前臺化。一方面,以前只是作為私人話題的個人情感、內心感受,在網絡空間中成為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界限開始變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網絡空間中針對公共話題的討論,又很容易被偏激的網絡情緒所感染,導致公共討論淪為網民想象力的肆意發揮和情緒的無原則宣泄。語言暴戾、道德審判、煽風點火等非理性行為就是這種情緒無原則宣泄的具體表現,它們會對網絡空間中的公共性實踐構成威脅,甚至有可能最終毀滅公共性本身。
最后,網絡空間中行動者的身體不在場導致行動不確定性的加劇。當人們認為別人不知道自己是誰時,其網上行為有可能會變得肆無忌憚,這容易引發負面行為后果的產生。正如安德魯·基恩所說,互聯網就像打開的潘多拉盒子,它讓我們的社會產生了頻繁接觸色情文化的年輕人、從事網絡剽竊的盜賊、患有強迫癥的網絡賭博者以及各種各樣癡迷者;它誘使我們將人類本性中最邪惡、最不正常的一面暴露出來,讓我們屈從于社會中最具毀滅性的惡習;它腐蝕和破壞整個民族賴以生存的文化和價值觀。⑧這種因為行動不確定加劇而導致的負面效應,同樣也會腐蝕和破壞公共性實踐所賴以展開的價值基礎。
麥克盧漢認為,任何一種新媒介的出現都會引入一種新的尺度,從而引發信息傳播、社會結構和行為模式的轉變。互聯網塑造了一個虛實交織的公共性實踐新空間,觸發了公共性實踐的結構轉變。然而,網絡公共性實踐目前仍面臨著意見群體隔閡、公共空間碎片化、情緒性行為多發、公共性實踐的價值基礎受到行為不確定性的威脅等困境。要化解和超越網絡公共性實踐中的這些困境,亟需致力于培育具有自律精神、責任擔當和公共參與意識的網絡公民,培育具有公共性理念、踐行公共性價值的網絡公民團體;重建社會信任,尤其是公共權力部門與公民團體及普通公民之間的信任,推動公共權力部門與公民團體之間、公共權力部門與普通公民之間以及不同的公民團體之間的對話、交流和協商。
(本文系寧波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互聯網的社會影響研究”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我國公民網絡行為規范及引導抽樣調查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G14-ZX17、10BSH025)
【注釋】
①[美]漢娜·阿倫特:《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劉鋒譯,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88頁。
②[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汪暉譯,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25頁。
③J.B.Thompson,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5. p.245.
④[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567頁。
⑤劉少杰主編:《中國網絡社會研究報告(2011~2012)》,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2頁。
⑥[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頁。
⑦黃少華:“風險社會視域中的網絡社會問題”,《新華文摘》,2014年第6期。
⑧[美]安德魯·基恩:《網民的狂歡:關于互聯網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59頁。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