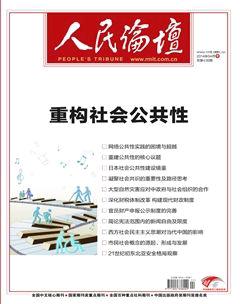重建公共性的核心議題
肖瑛
中國社會當下出現的公共性不足問題,癥結既不在于個人主義的泛濫,也不簡單地在于傳統道德的衰落,而在于“差序格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復興及其所引起的“自我主義”的過分膨脹。因此,重建公共性的核心議題是把個人帶回社會即重建個人主義,以個人主義建設為公共性提供價值基礎,以公共性建設來引導個人主義遠離自我主義。
個人與社會間關系的現代嬗變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整個人類社會始終都得面對的問題。在傳統社會下,由于人口基本不流動,個人對社會秩序的臣服雖然具體地看是一個難題,但在總體上不成為一個大的問題,因為其實質不是秩序本身的改變,而是如何用更有效的手段把個人拉回到既定的社會秩序之中。但是,隨著現代性的出現,這個問題的難度就空前地凸顯了,涉及的不僅是社會秩序如何維系,更重要的是對個人、社會以及二者之間關系進行重新界定。如在傳統中國社會,個人層面“君子”與“小人”相對;社會也由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構成;屬于禮治秩序。但在現代社會,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精神、人格、智識等層面看,“個人”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個人的物質需求被正當化、人格和尊嚴得以平等化、自我反思能力得到彰顯,這些都與“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格格不入;社會秩序觀念也因此發生了重大變化,熟人社會的道德共同體雖然在形式上存留,但等級制的禮治文明已經衰落,人際關系的平等化在增強,人口流動性在提高,民族國家、世界等宏大的抽象社會在人類生活中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這樣,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就直接轉變為個人主義與公共性的關系。
換言之,現代社會中理想的“個人”與“社會”與傳統社會的理想“個人”與“社會”都有根本性的差別:現代社會的理想個人形態是個人主義意義上的,社會則是公共性意義上的。從個人主義角度看,“獨立”(independence)、“自主”(autonomy)、“自信”(self-confidence)、“自尊”(self-esteem)、“堅韌”(perseverance)、“self-reliance”(自立)構成“個人”的本質內涵。這幾個概念從不同角度確立起了個人主義的基本理念:從物質上看,“個人”擁有其不可剝奪的物質財產和不可侵擾的私密空間,這種物質基礎保證了“個人”身體的獨立和自由,為“個人”精神上的獨立和自主提供物質基礎,因此構成公民權(citizenship)的前提;從權利上看,“個人”擁有參與與自身利益和權利相關的各種決策的權利;從價值上看,“個人”追求自身在精神、身體上的同一性(identity),塑造自身獨立的、有價值的、有尊嚴的和負責任的生活,即“人格”;從理性上看,“個人”具有自我評價的理性能力,能自我抉擇、自我行動和自我負責。
“公共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下是與《論語》中所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相似的具體人對人的愛戴和庇護關系,其泛可指君臣民之間,狹可指家族和家庭內部的家長與子女之間,或者熟人之間。但在現代性條件下,公共性的核心概念是“參與”,即平等和自由的個體自愿地參與到某些不僅關涉具體個人而且關涉抽象他人的活動中,通過平等對話、協商、行動來達成某種共識的過程。這個過程若能在參與者之間形塑出“共同體感”,那么公共性就不僅在客觀的權利和利益層面得以成型,而且在主觀的情感層面牢固化了。所以,在現代西方,“community”總是從議員、社會運動參與者、大學校長、市長到總統口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西方社會延展中的個人主義悖論
個人主義作為一種現代性現象,在西方社會也遭遇過很多的否定和批判。它在1820年后法國很多知識分子反思和批判法國大革命的遺產的過程中作為一個核心的“批判的武器”應運而生,據說是圣西門的追隨者最早使用了這個概念,用以批判現代性過程中的個人孤立、自私自利和社會分裂現象。托克維爾基本上處在這個脈絡之中,對個人主義持激烈的批判態度,認為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egoism)在社會后果上并無本質的區別,只不過后者是人之本能的表征,前者是民主主義政治思潮的產物。但與反基督教的思想家們稍顯不同的是,托克維爾把英國古典經濟學傳統中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等同關系給切割了,保留了自由主義的地位,而把個人主義推向了自由主義的對立面。
雖然個人主義從其出現開始就是一個消極概念,但大多數人從積極的角度來認識和使用它。馬克斯·韋伯認為個人主義是經濟理性主義的核心內涵,沒有個人主義就沒有現代市場經濟,現代性的核心“理性化”只有在個人言行中得以呈現之后才能有效改變社會。這種觀點延續了霍布斯、洛克、亞當·斯密等早期現代政治理論家和經濟理論家的思路,基本代表了現代人對于個人主義的態度。到今天,正如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迪蒙所說的,“個人主義”是現代世界中許多社會、國家或者民族所共有的理念和價值,沒有個人主義就沒有現代性,因此,“個人主義”堪稱“現代意識形態”。捷克學者沙拉漢在為其著作《個人主義的譜系》寫的中文版序言中也類似地說,“個人主義……已經被徹底地整合進西方的世界觀,以至于在西方堅持強調個人主義的作用已經是不必要的和徒然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
但是,正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表達的那種焦慮感所體現出來的一樣,個人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是人的理性化、自主性、人格、尊嚴以及創造性的彰顯,直接推動了現代性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則是人完全沉醉于對金錢的追求,片面發展工具理性,從而喪失了原初的公共價值意涵。這也是沙拉漢說“以至于在西方堅持強調個人主義的作用已經是不必要的和徒然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直接原因。換言之,在公平、正義、平等和自由的旗幟下展開的個人主義同時形塑出兩股軌道,一股是社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個人主義,另一股則是基于市場經濟的市民社會的個人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原子主義、自我主義。前者積極參與公共生活,通過公共參與彰顯自身價值,維護公共權利和利益;后者則以功利為唯一自我價值實現的參照,個人的成功與公共生活沒有直接關聯。這兩股思潮的同源和分岔構成了英國學者盧卡斯所謂的“個人主義的悖論”,也成了個人主義的批判者和支持者各自的理論依據。這一點在美國表現得特別明顯。
個人主義的批評者認為個人主義的張揚造成了人的極度功利化和公共性的淪喪,每個人都“躲進小樓求一統”,托克維爾曾經描述的美國人熱愛參與公共事務,熱愛結社的場面在今天已經不復存在,放眼望去,只剩下“孤獨的人群”和“沒有激情的個人”。換言之,個人主義的極度張揚造成了公共性的淪喪。但個人主義的支持者認為,應該區分道德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的個人主義,后者只為個人主義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真正的個人主義應該是道德意義上的;并且,道德個人主義在強調個人自主權和創造性的同時,也把個人從道德和去社會的邊緣上拉了回來,彰顯了現代契約精神以及公共道德和志愿精神取向,制約著經濟個人主義,推動公民社會和共同體的不斷重建,為公共性的彰顯奠定了價值基礎。
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等人關于美國人的“心靈的習性”的調查和分析接續了以上關于“個人主義的悖論”的爭論。他們認為,美國歷史上有四種類型的個人主義:圣經個人主義(biblical individualism)、公民個人主義(civic individualism)、功利型個人主義(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和表達型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后兩種統稱為“現代個人主義”。這三類個人主義構成美國基本的個人主義傳統,并共享一個最為基本的理念:“我們對個人尊嚴的神圣信奉。任何違背我們的自我思考、自我判斷、自我決定、我們自己認為適合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權利的行為,都不僅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而且是褻瀆神明的。我們至高至偉的渴望—不僅是對自己,也是對我們所關心的人,對我們的社會以及世界—都跟我們的個人主義息息相關。”
但是,除這一點外,三類個人主義之間絕少共同點:圣經傳統努力建立正義、包容和仁愛的道德共同體,此乃人類最基本的目標,比經濟成功重要得多;在此種共同體中,共同體要高于個人,其自有也是道德意義上的,即上帝與人的盟約意義上的,而非個人的為所欲為。共和主義理想超越了宗教限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人身、信仰、言論的自由,但試圖把貴族制與民主制結合起來,主張有道德的公民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以防止腐敗和不平等,并竭力建立一個憲政制度來使最優秀和最卓越的人被選拔出來治理國家。現代個人主義思想則強調自由就是實業精神與有權擴大自身財富和權力,強調個人先于和高于社會而存在。雖然這三種個人主義之間存在如此明顯的差異,但從建國到國內戰爭的美國社會就是在它們之間充滿張力的相互支持下運行的,個性張揚、人格獨立和尊嚴、個人成功同公共參與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用托克維爾的話說,雖然個人主義往往帶來個人孤獨感,但美國文化中對公共參與的鼓勵即結社恰恰為消解這種個人原子主義創造了極好的條件。由此可見,貝拉并非一般性地批判個人主義,而是在批判美國國內戰爭之后的功利型個人主義與表達型個人主義的過分強大,并尋求如何在城市化背景下重建美國早期鄉村社會時期的道德個人主義精神,以對功利型個人主義進行有效約制,重建公共性。
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個人與社會
近年來,道德滑坡、公德淪喪成為評價當前中國社會秩序狀態的最為熱門的兩個概念。從表面上看,這種現象是任何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過程中都難免遇到,因此,很多中國學者與輿論常常會模仿法國早期社會學家涂爾干的“失范論”,批判個人主義帶來了利己主義的盛行,儼然中國已經建立了個人主義的價值基礎。把涂爾干式的社會問題診斷法移植到中國,是否適合?為回答上述問題,需要回顧和厘定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道德構成及其在現代史上的演變。
對中國傳統道德有三種對立但具有一定一致性的看法:新儒家基于儒家倫理做出的判斷,如錢穆的“道德人生”說;新文化運動以來占主流的“一盤散沙”說;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下的“自我主義”說。“道德人生”即“活在別人心中”的想望。這里的別人,用梁漱溟的話說,是一個個具體的人,而非抽象的社會大家如國家。“道德人生”跟儒家的“禮”勾連在一起,“禮”以血緣即親親和政治等級制即尊尊為基礎,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差序格局”,不同地位的人之間以相應的“禮”相待,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即為此意。這種差序化的“禮治”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秩序,沒有獨立的個體即不存在個人主義,所有個人都處在特定的禮序之中,并依附于特定等級的具體人而存活,社會因此而井然有序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雖然禮崩樂壞的說法延續了兩千多年,但“禮治”文明始終弦歌不絕。
雖然孔子及其后學所想象的“差序格局”的“禮治”是固定的,其所建構的社會群體具有超乎個人的客觀實在性,但在實踐中卻不可規避地出現了流動和主觀的面相。費孝通指出,處在每一個群體中心的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可以主觀地為情感、血緣或者地緣設置邊界,不同人在這個群體中的親疏遠近關系端由他來確定,進入差序格局中的為“自己人”,沒能進入其中的則為“他人”,同為某一群體中的人處于不同的差序,與居圈子中心的人有著親疏遠近的區分。差序格局中人既附屬于這個群體特別是處于圈子中心的人,又相反地表現為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selfishness),如費孝通所說,“為自己可以犧牲家,為家可以犧牲族……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對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內看也可以說是公的。”
由此可見,在差序格局下,“道德人生”與“自我主義”之間、君子與小人之間、義與利之間的邊界不是絕對的,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再造的;而且,由于個人的“義”和“利”沒有明確的界定和邊界,一旦等級制被破壞,不同自我之間爭“義”奪“利”的沖突就難以防止。所以,差序格局既是一個社會牢固的道德紐帶,又十分脆弱,因此,不時聽聞“禮崩樂壞”的嘆息也就見怪不怪了。特別是在社會變動時期,差序格局的邊界可能會不斷收縮,直到只留下一個“自我”,而不同“自我”之間合作又十分艱難,于是“一盤散沙”的局面也就在所難免了。有鑒于此,新文化運動以來,“重要的是教育國民”的國民性改造和教育思想及方案相繼出臺。但是,對國民性中的“自我主義”的改造直到1949年之后才真正全民推廣并切實踐行。
1949年之后的國民性改造的目標是克服民眾的自私性而培植集體主義情操。集體主義對于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它是反儒家傳統的,它要求民眾臣服的不是具體的個人如君或者家長—但在文革中被扭曲為對領袖個人的崇拜—而是抽象的集體和國家;另一方面,它要求個人放棄自己的和小家的利益和權利而完全獻身于抽象的集體和國家即大家。國民性改造是多種方式的齊頭并進:首先是制度建設,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和單位制,徹底消滅私有制,讓私人利益缺失制度的土壤;其次是密集的意識形態宣傳,即馬克思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傳播和教育;再次是階級斗爭,狠抓斗私批修,對有私欲者用各種階級斗爭的手段進行處理;最后是獎勵,獎懲當然是相伴相隨的,樹立各種大公無私的典型,作為全民學習的榜樣。
在上述手段的通力配合之下,國民性改造毋庸置疑取得了一些成功,其直接表現是社會秩序的改善。但是,矛盾的是,在社會秩序變好的同時,無論是企業還是人民公社的生產效率不升反降。癥結在于過分嚴苛的意識形態教育和階級斗爭手段雖然表面上消滅了私欲的溫床,但從細微處反而催生出各種基于私利的“日常形式的反抗”,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彌漫的反抗導致了集體主義努力的終結。因此,一旦文革結束,外在壓力減輕,私欲馬上就像原野上的荒草一樣瘋狂地公開生長。
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動源固然涉及各方面的制度設計和創新,但最為根本的恐怕來自物質欲望的充分釋放。雖然整個集體化時期努力消除私欲和小家觀念而培育集體主義,但傳統家庭形式還是牢固地存續著。倒是改革開放雖然讓農村的生產單位重回家庭,但其對私人欲望的正當化以及社會流動的放松,對于傳統家庭觀念和差序格局的沖擊產生了空前的效果。當致富的欲望如洪水般肆虐,而相關的制度建設跟不上或者得不到有效執行時,正當的私欲恰恰可能成為破壞一切人正當利益和權利的力量,公權力腐敗、弄虛造假、坑蒙拐騙等現象就會普遍發生,甚至傳統的基于地緣和血緣的道德共同體和信任關系也在利益驅動下土崩瓦解。在這個過程中所發生的,并不是獨立、自主、尊嚴和平等的個人,而恰恰是閻云翔所謂的“非道德的個人”,即費孝通所說的“自我主義”形態的。換言之,這是一個“沒有個人主義的個體化”的過程,其與公德的流失、公共性的難產勾連在一起。
個人主義構成公共性的必要但非充分基礎
為什么中國人對個人主義有嚴重的偏見,原因不外乎有二:把個人主義當作利己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中國傳統的與當代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連西方人都在批判個人主義,中國更應該拒斥它。要摒棄這些偏見,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對個人主義及其與公共性的內在關聯展開分析。
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的關系要比簡單地等同復雜得多。利己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工具理性基礎上的利己主義,即前文提及的“功利型的個人主義”,這種利己主義遵守社會的基本法律,但主張只要合法地逐利就能帶來公共性的自我再生產;托克維爾所說的本能的利己主義,其在中國的對應物是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中所內涵的“自我主義”。功利型的個人主義是個人主義在市場和經濟維度過分張揚的結果,后者則是人的逐利本能的社會性闡發,與個人主義沒有多大關系,不能簡單地將之與個人主義等同。正因為后者的存在,無論是傳統的共同體還是幾十年前的公社制試驗,都沒能很好地規避利己主義的存續和活躍以及“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的淪喪,費孝通對差序格局的分析就很好地呈現了中國傳統道德共同體背后活躍的利己主義力量。由此可見,利己主義并非某一理念和制度所獨有,而是嵌入在人類生活中的獨立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個人主義雖然把某些類型的私欲合法化,但正如韋伯所指出的,理性化的資本主義同時構成對為達目的不計手段的逐利行為的限制,由于以私人財產制為基礎,并建立了清晰的法律,明確了私人活動的邊界,也就約束了利己主義無限擴張的可能。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對“團體格局”的分析最可以形象地呈現這一點。另外,個人主義對個人責任的強調,也是限制利己主義的重要力量。總之,這種責權利明晰的社會構成邏輯雖然難以絕對規避托克維爾所謂的“集體個人主義”的弊病,但相比傳統社會中全方位的人身依賴關系有了根本性進步,同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運行邏輯嚴絲合縫。
個人主義是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是公共性的重要前提之一。很多個人主義的批評者未曾認識到,個人主義是各種現代性思潮的共同基礎。韋伯把現代社會秩序的核心界定為“理性化”,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將“理性化”進一步細化為四個模式變量:成就來源的后致性、規范適應的普遍主義、情感的中立性以及義務的專一性。個人主義對個人成就、人格、獨立、平等和自由的訴求同這四個變量本質上是合一的。從這個角度說,沒有個人主義就沒有社會秩序的現代化。有人喜歡拿社群主義對個人主義的批評說事,而忽略了社群主義與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焦點不是要不要個人主義,而是個人主義是否具有自足性,換言之,事關個人主義在主張個人正義和權利的同時能否自動地帶來公共善。個人主義者認為“善”和“公共精神”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而社群主義認為若沒有社群生活的支撐,不僅公共善難以生發,而且連個人主義本身也難以獨善其身,因此,社群主義者不是懷舊式地向往重回傳統,而是要求“在個人主義的時代之中重建共同體”。此外,一些人認為,馬克思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論斷是對個人主義的否定。這些人未曾注意到,馬克思關于“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共產主義想象本質上就是個人主義的,強調的是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人格上都充分自由的個體之間的結合,也不曾注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形式平等和自由的批判并不是否認形式平等和自由,而是批判只有這兩者以及用這兩者遮蔽實質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其真實目的是建立形式平等和自由同實質平等和自由并置的真正的個人主義社會。對于馬克思而言,個人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實現方式是不一樣的,從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關系到私人擁有財產權,再到私人財產權的終結,是一個不斷揚棄的過程,工人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絕不是指個人要讓自己的個性、人格和尊嚴消失在階級之中,而是希望通過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來祛除橫加在工人個人身上的各種壓迫和異化,為個人自由創造條件;當個人最后徹底擺脫財產和權力的控制時,個人主義就徹底實現了。所以迪蒙斷言,馬克思本質上是一個個人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