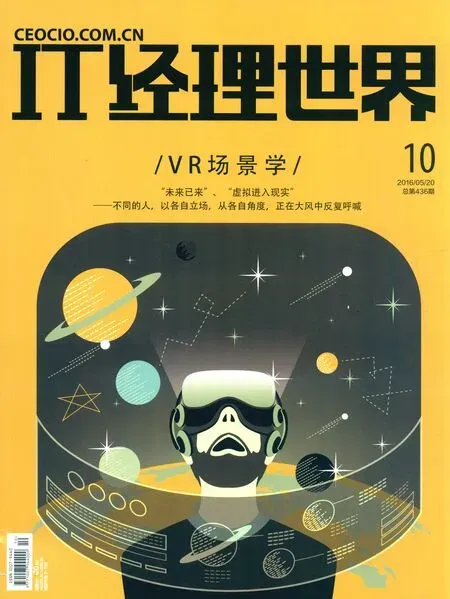無尺度網絡的挑戰
胡泳+郝亞洲
網絡化的個人主義
網絡是由三個關鍵成分構成的,它們自古以來就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存在著,然而卻在最近的幾十年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一個出現的網絡元素是緊密聯系。緊密聯系由我們與周邊的人的強聯系構成。緊密聯系對于我們的情感幸福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僅有緊密聯系卻是遠遠不夠的。一個違背本能的現實情形是,如果我們過度地依賴緊密聯系,甚至具有某種危險性。那些完全或主要依賴于緊密聯系的人往往是孤立的,他們不了解很多有價值的信息,而且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在貧困社區,處處都要依賴于緊密聯系,而富人或中等收入的群體則不是這樣。
與之相對的第二個網絡元素是弱聯系,它的力量僅僅是最近幾十年才變得顯著。弱聯系是我們與談不上是朋友的相識者之間的聯系。他們包括朋友的朋友,疏遠的鄰居,或是過去曾經緊密聯系但現在幾乎失去聯系的人,也包括我們每天偶然遇到或將要遇到的陌生人和認識的人。他們構成了我們生活的背景,但在網絡世界里,弱聯系大量存在,而且是最強大和具有創造性的力量。第三個網絡元素由聯絡樞紐構成。可以把它想象為許多弱聯系或緊密聯系的匯聚地。不同群體的人們因為共同的目的聯系起來,包括家庭、企業、社團、族群和國家。人們可以在生活中加入各種各樣的樞紐中,也有權塑造和改變樞紐,或者啟動屬于我們自己的樞紐。
善用網絡,意味著離開你的正常樞紐,雖然它能夠提供安全與熟悉感,而在你的網絡中經由常常被忽視的聯系,去探索那些跨界和交叉的地方。
個人必須學會面對一個巨大的范式轉變:無論工作、生活或休閑,我們曾經主要靠組織來聯絡——企業、專業協會、俱樂部社團和旅游公司。然而,我們現在的聯絡,正越來越多地依靠個人活動、網上聯系與自發的網下會晤,以及與熟人、朋友的朋友和陌生人之間的偶然碰面。個人積極地規劃自己的生活,獨立于現有機構或組建非正式的團體,社會變得更具流動性、更加不可預測、自由發展、無拘無束。
這個新范式,我稱之為“網絡化的個人主義”。面對網絡化的個人主義者,企業做什么?唯一的出路是:通過營造社區、發放比特來出售原子。海爾的虛實網融合正踏在這樣的路上。
無尺度網絡的連接性與同步性
張瑞敏提出“供應鏈無尺度”,并延展到“用戶體驗無尺度、員工創新無尺度”。在網絡理論中,無尺度網絡是帶有一類特性的復雜網絡,其典型特征是在網絡中的大部分節點只和很少節點連接,而有極少的節點與非常多的節點連接。這種關鍵的節點稱為“樞紐”或“集散節點”。提出“無尺度網絡”的巴拉巴西在1999年與阿爾伯特合著的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模型來解釋復雜網絡的無尺度特性,稱為BA模型。這個模型基于兩個假設:
· 增長模式:不少現實網絡是不斷擴大不斷增長而來的,例如互聯網中新網頁的誕生,人際網絡中新朋友的加入,新的論文的發表,航空網絡中新機場的建造等等。這種增長有時是一種倍速增長。
· 優先連接模式:新的節點在加入時會傾向于與有更多連接的節點相連,例如新網頁一般會有到知名的網絡站點的連接,新加入社群的人會想與社群中的知名人士結識,新的論文傾向于引用已被廣泛引用的著名文獻,新機場會優先考慮建立與大機場之間的航線等等。
這其實為海爾的網絡化組織提出了一個重大挑戰:怎樣涌現更多的樞紐?如果網絡化組織中的每一位員工(或者使用海爾最新的術語:接口人)都是一個節點,那么節點與節點之間的距離一定會拉大。節點好比磁鐵,有的磁鐵具有超強的聚集力,有的吸引力則比較微弱。換言之,每一個節點不是平等的,因此,網絡化組織也絕對不會是平衡的。
假設在一個網絡中移除一個節點,以及與其相關的連接,那么原網絡中的其他點也可能受到影響:原本相連的兩個節點可能不再相連;即使相連,從其中一處到另一處可能需要經過更多的路途。總的來說,網絡的連通性降低了。所以,大大提高每個節點的不可移除性以及連接性,是海爾亟需解決的問題。
還有一個可能是更加關鍵的考驗:無尺度網絡的同步性。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實驗:一個大禮堂中有千余人,實驗者要求大家開始鼓掌,掌聲盡量協調一致。結果發現,雖然沒有人指揮,起初雜亂無章的掌聲卻很快就節奏一致。尼葛洛龐帝研究后也不由感慨:我們對于從完全獨立的行動中所產生的協調行為的認識還非常之膚淺。
“尼葛洛龐帝式鼓掌”現象顯示出網絡的同步性。即便單一節點能力提高,而整個網絡卻不具備協調一致的同步性,那么網絡化組織的打造也終將歸于失敗。網絡動力系統的同步性取決于節點動力系統的特性、節點的耦合方式與網絡的結構。海爾雖然找到了路,同步性卻將是海爾繞不過去的障礙。攻克這個障礙,海爾始得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