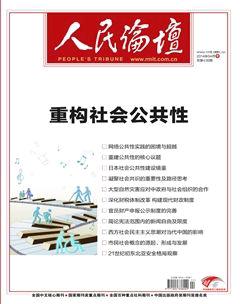日本社會公共性建設鏡鑒
李國慶 戴秋娟
日本社會意識歷經忠誠于天皇制、忠誠于企業和向個人化發展等階段。從日本歷史傳統看,國家主導的“行政的公共性”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從作為文化的社會意識看,日本人傳統的以協作團體主義為實質的“集團主義”存在于社會深層,助推了公共意識的產生。
關于公共性的討論在日本興起是20世紀60年代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以后,公共性問題由此成為日本社會學領域的重要研究課題。研究公共性問題的理論意義在于重新審視社會運行基本規則的變化。①從日本歷史傳統看,公共性是由“官方”承擔的,也就是說由國家的行政管理構成了公共性的核心②,中央政府在事實上壟斷了公共性,這種公共性被稱為“行政的公共性”。進入60年代以后,隨著市民活動的發展,獨立于“行政公共性”之外的“市民的公共性”逐漸引起社會關注。
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認為,與國家、政府支配的“行政的公共性”不同,“市民的公共性”是由作為獨立個體的市民為了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而與其他市民共同合作創造的嶄新的生活世界。③日本政府出版的《生活白皮書》也指出:“我們要創造新的公共性,它不同于國家、地方公共團體等官方組織的形式單一的公共性,而是對福利、城市建設等特定問題感興趣的人們通過自發組織活動創建的、具有多元化特征的公共性。新的公共性應以市民的自發活動為主體。”④從“行政的公共性”向“市民的公共性”轉型,日本社會公共性的內涵發生了質變。
公民活動的興起與發展
從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穩定增長,日本走過了政府主導、以政策手段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道路。由于企業把生產作為第一要務,沒有顧及環境保護,引發了嚴重的產業公害,主要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震動、地面下沉及惡臭等七大公害,對當地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嚴重侵害。20世紀50~70年代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先后發生了四次震驚世界的公害:熊本水俁病(1956年)、新潟水俁病(1964年)、三重縣四日市哮喘病(1960~1970年)和富山縣神通川流域疼痛病(1955~1972年),前兩次為有機水銀排放所致,后兩次則為硫化物與鎘排放。公害問題主要發生在工業領域,企業是主要的加害者。面對嚴重的公害問題,市民自發組織了“反公害運動”、“反環境破壞運動”,批判企業的行為及政府的不作為,保衛自己的生活空間。受害者團體紛紛把排污企業告上法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公害訴訟”。以四大公害訴訟為起點,日本全國發生了大量公害糾紛,僅1972年就發生了87764起。這一時期的公民活動是一種對抗的、利益訴求型的活動,喚醒了滿足安逸生活的社區居民保衛生活家園的公民意識,雖然這一時期日本的公民活動還沒有形成影響持久的公民組織。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開始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地方政府希望發揮市民的聰明才智為地方經濟走出低谷獻計獻策,緩解政府財政負擔,積極倡導市民更多地參與到行政活動中。市民積極回應地方政府的倡議,參與振興地方經濟的活動。最為著名的事例是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提出了“一村一品”,號召居民發掘、創造可以成為本地區標志性的、可以使當地居民為之驕傲的產品或產業項目,振興地方經濟。“一村一品”活動此后在日本全國順利推開,這與廣大市民對活動的認同和積極參與密不可分。這一時期市民活動以“參與·創造型”為主,與行政的關系體現為市民參與地方行政管理。保護環境仍是這一時期公民活動的重點之一,日本各地產生了不少以消除生活環境破壞為目的的市民團體,與70年代的對抗、利益訴求型活動相比,這一時期的環保活動更加理性,市民直接參與保護環境的活動,提出解決辦法。隨著保護生活環境、節約資源、循環再利用、普及環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等活動的開展,市民的環保意識有了長足進步,城市生活環境得到顯著改觀。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因泡沫經濟破滅而進入長達十年之久的經濟低迷時期。隨著居民參與的振興地方經濟活動的深入發展,市民參與地方行政活動的程度不斷加深,市民組織進一步要求地方行政活動信息公開、透明。這一時期日本政府開始推行地方自治改革,倡導地方行政的運營應由地方自治體、市民、企業共同推進,地方行政管理模式開始向市民行政聯動型轉變。地方政府委托市民團體運作的養老服務、綠色消費、社會福利等活動逐漸增加。另一方面,以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市民團體組織的各類志愿者活動開始活躍起來,市民在公益性較高的公共服務供給上不再過度依靠政府,開始嘗試以自身力量謀求解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由于政府救災行動遲緩,各地民眾和非政府組織紛紛行動參與救援和災后重建。整個救災活動中共有來自日本各地的130多萬名志愿者參與救援,高峰時期每天有超過2萬名的志愿者在災區開展各種形式的救援活動。震災催生了大量新的志愿組織,新老志愿組織一道參與救援。“神戶加油村”是震后第三天由聚集在一個公園里的志愿者們自發結成的組織,最初三個月里他們在各個公園架鍋造飯,最多時一天為避難居民提供多達7000份的便當;成立了“假牙救護隊”、“嬰兒救護隊”和“溫心草甸隊”,針對不同需要開展個性化活動,截至1995年12月,參加該組織的志愿者達到1萬人次。⑤災區社會需求多元,志愿者組織的活動也各具特色,人們不再只依賴政府,而是努力尋求自救之路,志愿者建立了組織網絡,保持密切交流,自律發展。
阪神大地震的救援活動和災后的重建活動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啟示,那就是與政府和自衛隊相比,來自全國各地、有豐富救援經驗的救災志愿組織的力量更加可靠。救災對市民活動起到了刺激、鼓舞和促進作用,市民團體的一系列活動極大激發了市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熱情和責任感,1995年作為“志愿者元年”而被載入史冊。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逐漸認識到市民的力量,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的支持志愿者活動的政策。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1998年12月實施的《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在該法律出臺以前,日本法律體系中沒有一個能夠賦予志愿組織、市民組織法人資格的法律,雖然在日本社會自發的市民活動并不違反法律,但是由于沒有法人資格,無法以組織身份簽署任何合同,租借辦公場所、管理組織基金與行政對話均受到了限制,而且難以得到社會的普遍信任。《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的制定為非營利組織活動的開展創造了寬松、積極的環境,降低了公民社團注冊準入門檻,縮短了審批手續,減少了來自政府的限制,加大政務信息公開力度,該法案被認為是日本政府向社會開放更多活動空間的重要標志。⑥endprint
進入21世紀以后,日本社會的少子老齡化、貧富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日本國民參與公共活動的意識也不斷增強,公民活動的發展進入一個穩定、繁榮的時期。特別是《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實施后,市民組織可以通過相對簡單的手續取得NPO法人資格,市民非營利組織數量激增。截至2013年12月,全日本非營利法人總數達48611個。⑦非營利組織的活動領域主要涉及17個方面,即福祉、醫療、街區建設、環境、文化/藝術/體育、地區安全、災害救援、維護人權與和平、促進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培養兒童健康成長、信息化社會建設、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科技進步、支援志愿等領域,覆蓋了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大部分領域,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市民生活中,非營利組織在獨立開展各項活動時,越來越注重處理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嘗試通過自身努力和與政府溝通來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此同時,日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也越來越重視發揮非營利組織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在各種政策措施中增加了以非營利組織為對象的內容,積極向市民提供信息,鼓勵市民參與非營利組織。一些地方建立了地方政府、非營利組織、市民三方攜手合作的運作模式,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系越來越多地轉變成為一種合作伙伴關系。
綜上所述,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行政與市民的關系從“行政主導型”逐漸轉變為“市民·行政聯動型”,市民與行政機構開始作為對等主體,共同參與社區治理。
社區市民活動的組織形式
日本社區的公民活動有多種組織形式,根據活動內容、參與主體的不同,可分為以下四種:一是社區居民自治組織,其中歷史最為悠久的組織是町內會;二是行政職能對接組織,活動與行政活動有密切關系,主要配合行政管理部門開展輔助性活動;三是自主型市民組織,活動涉及政治、經濟、產業、教育、文化等市民生活的各領域,以市民為運營主體,非營利組織屬于這一范疇;四是特定參加者團體組織,組織成員具有某一方面的共同點,例如PTA(家長后援會)是以學生家長為成員的市民組織,本著自愿加入的原則,圍繞“為了孩子、發展教育”這一核心宗旨,協調學生家長與教育工作者的關系,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活動,活動足跡遍布日本全國各地。
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國民收入增加,生活富裕,中產階級人數急劇擴大,國民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逐漸趨同,形成了“一億皆中流”的階層歸屬意識。中產階級一直被視為現代民主、富裕、發達社會的支撐群體,是公共性建設的推動力量,也是社區公民活動的主要參加者。
日本的家庭主婦是社區開展公民活動的重要力量。由于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很多女性在結婚、生育后退出勞動力市場成為專職主婦。由于戰后高等教育的發展,日本的家庭主婦一般都受過良好教育,她們對兒童教育、環境、老人護理、食品安全等自己身邊的問題非常關心,而且有較高的參與熱情,不少婦女以參與社區工作為契機,在自己生活的社區找到了自我發展空間,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此外,身體健康的中老年人參加社區公共活動的熱情也非常高。老年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術,社區活動為老年人發揮余熱提供了平臺,通過參加社區活動他們可以和社會保持密切聯系,保持健康的精神生活。
在日本,町是構成社區的最小單位,類似于中國的街道,以町為單位建立的町內會是日本社區中重要的基層居民自治組織。以居住地為單位形成的“町內”發揮了道橋管理,喪葬服務、治安維護和生活互助的功能。町內會作為社區居民的組織與行政管理部門協作開展活動,成為連接居民與政府的橋梁。居住在町內的居民絕大多數以家庭為單位加入町內會,全體會員民主選舉會長,負責日常組織與管理。
町內會集多元功能于一身,其主要功能可分為以下五大類:一是促進社區居民的睦鄰友好關系的功能,社區的公共活動大多數是以町內會為單位舉辦。町內會不僅負責籌辦各種慶典活動,而且定期組織一些有吸引力的文體活動,如敬老會、茶道會、棒球賽等,為居民提供交流渠道,促進鄰里交往和相互了解,滿足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二是應急功能,在突發事件和自然災害預防與應對方面,町內會承擔著對居民進行防災技能培訓的功能,組織居民共同抵御災害,發放救災物資,培養社區居民同舟共濟、互幫互助的意識,提高社區凝聚力。2011年“3·11大地震”發生后,世界媒體都驚訝于日本災區的平穩有序,這與町內會及時有效的應對不無關系;三是行政輔助功能,町內會通過編輯社區報紙向居民傳達地方政府的行政方針,接受相關行政部門的委托任務,為居民提供保健服務,美化社區環境,維護社區設施,防止犯罪事件發生;四是壓力團體功能,町內會負責征集町內居民對地方行政部門的意見并傳達給行政部門,與地方行政部門之間設有定期的協議會、研討會,參與行政審議會,及時把居民對政府的希望要求、批評建議收集起來轉達給政府,向政府提案并監督落實。同時,町內會把政府的政策意圖和問題處理情況轉達給居民,促進居民對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五是協調町內各種團體的職能,協調社區中的老人會、婦女會、家長會、青年團、各種文體組織和志愿者團體之間的關系。從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町內會兼具社區居民自治與行政輔助的雙重特性,在社區與政府部門的互動中,町內會扮演著上傳下達的角色。町內會既不同于地方政府這類“公”組織,也不同于以民間企業為代表的“私”組織,是一種介于國家與個體之間的中間團體,市民以地緣為紐帶,通過町內會這一媒介,對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表達意見和愿望,與其他有共同訴求的市民一道參與社區公共建設,社區居民的公共性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強化。
日本社會學家近江哲男認為町內會這種日本傳統的地方自治組織是日本型集團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⑧三戶公在《家的邏輯》一書中對日本人公與私的觀念作了有趣考察。在日語中,“我”的漢字表達是“私(わたくし)”。根據《大言海》中的解釋,“わたくし”的詞源“わ”是“吾”,而“わたくし”是從“我盡し”轉換而來的,意思就是要竭私盡公。日語中的“公(おおやけ)”的詞源是“大家”,大家是超越個人的集合體。日本人的“公”可分為三個層次,最基層的單位是家族,中間層是公司、學校或自治體等,最上層的國家是一個完整的單位。每一個日本人都同時屬于這三個不同層次的組織。他首先是某一個家庭的成員,日本的家庭是一個由家長統帥的共同體和集合體;其次,他屬于某一個企業或學校;最后,他又是最高層次的國家的國民的一員。這三個層次的家之間又構成了相互的公私關系,國家是最大的公,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企業相對于家族是公,而相對于國家則是私。三戶公認為,對“我”的正確解釋是,作為個人,他首先屬于家、公司直至國家,私家首先要竭盡力量報效于公家。從日語中“我”的字源就可以看出公的觀念在日本文化中是多么根深蒂固。⑨在圣德太子的17條憲法中,特別倡導“背私向公”。這一觀念影響到日本人的決策方式,決策雖然是個人作出的,但其主體實質上不是個人,而是個人歸屬的集體,集體意識優先于個人。endprint
在一般意義上,集團主義是一個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概念,即在處理某一個問題時,其行動原理是優先集體還是優先個人。然而,日本學者濱口惠俊指出日本的集團主義中個人與集體并非一組二元對立的概念,二者并不矛盾,個人與集體之間的互利共生、成員之間的協調發展是日本集團主義的核心概念。集團主義反映在日本人行動中的表現是更多地考慮組織的期待,為了維持組織的正常運轉往往放棄自己的意見,主動投入到組織的懷抱之中。對于日本人為什么如此重視與所屬集團的調和,濱口惠俊認為日本人的意識結構中集體的自律性比個人自律性更為強烈,只有自己所屬的集團在更大范圍的社會體系中得以發展, 個人利益才能夠得到滿足⑩,兩者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集體與個人同等重要。集體對個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企業的發展使其成員得到了自豪感,成員的歸屬感和自尊心來自企業,它使其成員感到自己的利益與企業的未來息息相關。
在日本集團主義文化下,個人往往尋求集體的支持來保證其個人利益的實現,他們積極參與社區公共性建設,希望尋求集體的力量來保證個人在社區生活中的利益。可以說日本的集團主義文化是推動日本社會公共性建設的文化根源。
社區公共領域的條件建設
社區公共領域的硬件建設。當代關于公共領域的思想主要得益于哈貝馬斯。他認為公共領域是介于私人領域和公共權威之間的一個領域,是一種非官方的范疇。它是各種公眾聚會場所的總稱,公眾在這一領域對公共權威及其政策和其它共同關心的問題作出評判。自由、理性、批判的討論構成這一領域的基本特征。公民開展社區活動需要公共領域,例如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對公共政策進行批判,在市民社會形成初期餐館、咖啡廳等經常作為活動場所使用。但是隨著市民活動深入發展,不斷走向成熟,越來越多的市民走出家庭希望參與公共事務、討論公共政策,對公共活動的空間需求也越來越強烈。在日本的社區里一般建有區民館、集會所,這類場所滿足了市民對公共活動空間的需求,其主要功能是給社區居民提供交流、學習、娛樂、休閑的場所和設施。設施內一般設有會議室、學習室、茶室等,社區居民可以在這里開會研究社區公共事務,還可以開展各種學習活動,如茶道、花道、劍道等日本傳統藝術。比區民館、集會所規模大一些的是文化中心,一般每個區都會有幾個區民文化中心,設有會議室、教室、大舞臺,社區居民除了在文化中心集會、學習外,社區居民組織的文藝團體可以在文化中心排練和演出。
區民館、文化中心等社區居民公共活動場所的建造費用由政府專項經費支持資助,日常運營費用則來源于社區居民的籌資和使用費。設施的工作人員除極少的專職人員外,大部分由社區居民自愿服務。區民館、文化中心等公共活動場所為居民商討社區公共事務、參與社區決策提供了空間保障。
社區公民文化建設。公民文化的核心特質是公民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和社會參與意識,高度參與公共活動,遵守各項法律和制度。日本的社區居民一般對社區公共事務比較關心,參與社區公共活動也比較積極,對維護公共秩序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這種積極公民文化的形成得益于日本長期以來的教育成果。
一是兼容并蓄的公民教育。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借鑒和吸收各國文化的民族。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積極學習中國的儒家思想,并將其轉化為維護政治統治需要的倫理規范。日本在儒家文化“仁、義、禮、智、信”的基礎上增加了“忠”這一思想,對公民進行忠誠于國家、集體的教育,對集體的認同正是對整個社會、國家認同的基礎和前提,日本人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也體現了其對集體的高度認同。明治維新后日本深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公民教育既提倡西方文化中的個性和民主的思想,又提倡儒家集體主義的價值理念,強調個體在集體中的價值。
二是注重道德教育。日本將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標定位為公民道德人格的完善和發展,道德教育是全方位的,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塑造等多方面。通過全方位的道德教育培養公民具備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為社會服務、實現社會價值。
三是提高個人修養,構建終身學習型社會。為了提高市民參與活動的專業性,地方政府聯合大學面向普通市民開設了多種形式的社會學習課程,旨在構建終身學習型社會,從而提高市民的個人修養。另外,市民組織非常重視對會員和市民的培訓。一些環境市民組織將環境教育作為主要工作內容,注重環境意識的普及和宣傳,舉辦各種形式的講座、培訓、經驗交流會和實踐活動。有些社區注重對居民宣傳本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以中小學校為基地,充分利用當地的歷史、文化館等開展活動,潛移默化培養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和歸屬感。上述市民組織的社區學習活動屬于公共軟文化建設的范疇,市民通過學習提升了公民素質,是公民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政府只有在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同時加強軟文化建設,才能培育健全的公民文化。
四是從集團主義文化中培育公共意識。日本文化中有著強烈的集團主義要素,當他們身邊的生活受到來自政策造成的威脅時,就會發生居民運動,或者在政治選舉中表現出他們的意愿。1993年發生的導致戰后政治體制崩潰的眾議院選舉就是始于反對消費稅的運動,是選民對政黨政治不滿的體現。此外,1982年的反核運動、1987年的反銷售額稅運動、1998年由于經濟政策失敗迫使橋本內閣下臺的參議院選舉,都是居民參與政治的表現。當周圍發生公害問題、消費稅稅收加重問題和經濟衰退問題時,人們就會以居民、消費者和選舉人的身份來反映自己的意志。從身邊的日常活動中影響和改變公共政治已經成為日本居民參與政治的主要手段。
通過上述日本社會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和全方位的終身學習型教育,日本民眾的參與精神、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治理能力得到了升華,日本社區的公共性在這種公民文化的影響下也獲得了發展。
日本社會公共性建設的特征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日本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強勢政府以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對于市民來說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生活的富裕是最重要的,追求獨立精神和民主生活并不是最大訴求。在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強勢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民多元利益的表達,“行政的公共性”仍具主導地位。但隨著產業化與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無法滿足市民日益多樣化的需求,在此情況下作為中間組織的各種市民團體的出現彌補了“政府失靈”危機,在政府不愿涉足或沒有能力涉足的領域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市民組織的不斷壯大,其對公共政策影響也日益擴大,“市民的公共性”逐漸得以確立。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是第一要務,人們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上。與此同時,城市單位體制的變化帶來原有體制人員規模的大幅度縮小,以往城市人生活在單位體制內,而今留在公有制單位的人已成為少數,而多數人已脫離單位,其身份正從“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依靠政府管理社會的傳統模式難以滿足社會需求,如何在新形勢下引導居民參與社會治理,日本的經驗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鑒。endprint
注重公共性建設的制度保障。在日本,公共性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五六十年代的反戰、民權運動到70年代的消費者保護和環境保護運動,再到90年代中期以阪神大地震的災后重建為契機爆發的居民參與能量的爆發,歷經30余年的發展,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法律制度,推動整體社會有序、良性發展,以市民為主體的“新的公共性”開始植根于日本社會,行政與市民的聯動機制的建立為市民參政、議政提供了通暢的渠道,市民參與治理的社會治理模式逐漸走向成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組織雖然在數量和設計領域上有了一定發展,但是從社會組織參與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的水平還遠遠不夠。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是一個長期過程,其間需要建立各種制度保障、支持居民參與社會治理。
注重政府主導的社會治理。政府在日本市民社會的成長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創建、監督和指導功能。日本的町內會等社區自治組織較為發達,在分擔政府職能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町內會的活動體現了地方行政與公民組織活動的良性互動,市民參與度高,有利于增強社會凝聚力,促進了社會穩定。另外,日本非營利組織的市民活動也非常發達,日本政府在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方面的支持和支援是全方位的,政府在市民團體的職能方面制定了許多規章制度,同時通過財政撥款支持市民活動。可以說日本市民社會的成長有賴于政府的強力支撐。中國的社會組織起步較晚,其組織形式尚不健全,需要政府給予支持和引導。
建設公共活動場所。公共活動場所是開展公民活動的重要條件之一,為了推動社區公共性建設,在日本主要由地方財政支持興建公共活動場所。公共活動場所的功能是多元化的,公共活動場所為鄰里交往提供契機,同時也是開展各種社區公民活動的重要平臺。目前,中國城市社區中還缺少類似日本社區中的區民館、集會所、文化中心那樣的公共活動場所。
注重公共文化建設。除了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進行投資外,日本政府還非常注重公共文化建設。學校教育中注重公民道德教育和對公民政治意識的培養,每一個日本公民從小學就開始接受如何參政議政的教育,學校組織學生定期參觀國會,了解日本政治運行體制,學習如何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社區還會組織各種學習活動,致力于構建終身學習型社會,提高市民的修養。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發展的轉型期,政治、經濟、文化已有長足的發展,在一些大城市的重點中學已開始重視對學生公民意識的培養,在教學中增加了參政、議政的內容,學校還會組織學生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義工、助學活動。以學校的公民教育為起點,以提高公民素質為目標,在社會開展終身學習活動是構建公共文化的重要環節。
從共有意識的培育入手培育公共意識。日本的公共性的形成有著集團主義的文化基礎,個體化的居民首先從發生在身邊的事務,如產業公害和城市生活環境問題等受害者范圍特定問題的關注介入社會事務,逐漸發展到震災救助等對象人群不特定的公共事務。借鑒日本的經驗,中國應首先培育居民的共有思想,例如培育居民對居住小區的共有事務、社區環境、家校互動等共有問題的治理開始,培養社會治理的參與意識,從中逐漸培育出參與收益人群不特定的公共領域的事務治理活動。
【注釋】
①[日]藤田弘夫:《東亞公共性的變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6頁。
②[日]長谷川公一:“NPO與新的公共性”,載于[日]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編:《中間團體開創的公共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2頁。
③[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10~11頁,第58~59頁。
④日本內閣府:《平成16年國民生活白書》,2004年,第154頁。
⑤[日]八木哲郎:《志愿者改變世界》,日本法藏館出版社,1996年,第185~190頁。
⑥Mary Alice Haddad,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Civil Society Landscap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7(7), pp413~418.
⑦https://www.npo-homepage.go.jp/about/npodata/kihon_1.html,2014年4月14日檢索。
⑧[日]近江哲男:“城市的地區集團”,《社會科學討論》,1958,第3卷第1期,第168頁。
⑨[日]三戶公:《家的邏輯》(第一卷)《日本經營理論緒論》,東京:文真堂,1991年,第36~61頁。
⑩[日]濱口惠俊,公文俊平編:《日本的集團主義》,有斐閣,1982年,第14~18頁。
王名,李勇等編著:《日本非營利組織》,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頁。
責編/邊文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