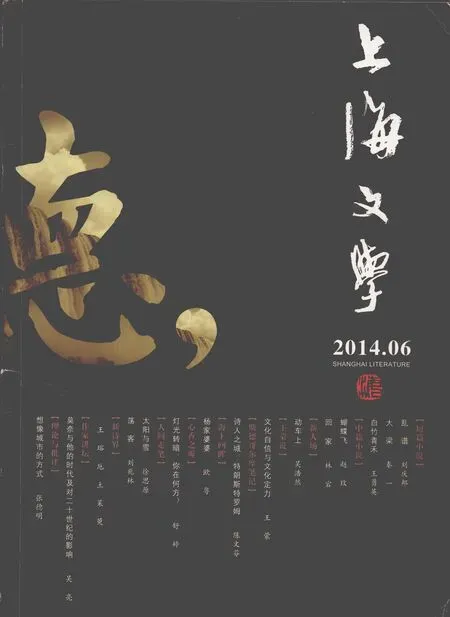詩人之城:特朗斯特羅姆
陳文芬
冷氣,青色,公駒
隱約,出現,霧里
于是,找著,洞穴
洞室,藏有,死人
水磨,慢慢,咕隆
靴子,總不,停止
死人,手在,發亮
風在,天上,逃跑
這首詩是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Tomas Transtr?觟mer,1931-)發表于1949年斯德哥爾摩的青年文學刊物《當月桂樹生長之時》的五首詩作當中的一首。(特朗斯特羅姆在中國簡稱“特翁”,私下我們直呼托馬斯)寫這首詩的時候,托馬斯只有十七歲。他向來是一個非常有判斷力的詩人,極為謹慎地檢查自己作品的質量,2011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前,他發表詩作全集僅一百六十三首。
托馬斯早于第一部詩集《詩十七首》以前所寫的十首詩,從未在全集發表,作家兼出版家Jonas Ellerstr?觟m 2006年前將這十首詩印成一小冊散贈給朋友,以后馬悅然將十首詩翻譯成中文,收錄在托馬斯散文回憶錄《記憶看見我》的中文譯本附錄里。據馬悅然分析,托馬斯早期的詩作已能純熟運用西方古代詩的格律,他高中時讀了羅馬詩人賀拉斯的詩歌,發現有一種形式上的美感,由此懂得詩的形式多么重要。托馬斯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的八十闋,其中十三闋用了古代的薩福式格律,兩闋用了阿爾凱式格律,另有四十八闋使用有五個重音的抑揚格的無韻詩體,其余的十七闋則是自由詩體。托馬斯是1950年代初,瑞典唯一使用古代詩律寫詩的年輕詩人。
托馬斯早期所寫的十首詩當中,這一首詩的格律與中國的六言詩完全相同,以兩個音節為一個沉重的停頓,這是一個偶然,在西方的詩作里頭非常罕見。2012年秋天馬悅然到上海訪問,做了一場中國的六言詩的演講,將托馬斯的詩作里頭的停頓,加上逗號,跟中國唐代的六言詩做了一些比較。《樂府詩集》有唐代張說(667—730)所寫一首名為《破陣樂》的六言律詩:
少年,膽氣,凌云,
共許,驍雄,出群。
匹馬,城南,挑戰,
單刀,冀北,從軍。
一鼓,鮮卑,送款,
五餌,單于,解紛。
誓欲,成名,報國,
羞將,開口,論勛。
張說跟托馬斯這兩個在遙遠時空不同國度的詩人,他們在六言詩里頭的表現,都有相同的美感,不強調敘事,而容有建筑、音樂、繪畫的審美感受。
托馬斯從小在斯德哥爾摩的南區成長。人們認為南區居民才是斯城真正的“老居民”,他們擁有自己的方言。即使住在斯城多年,一旦走進南區,也會感覺到自己是個陌生的外來者。斯城的主體是七座島嶼的連結,1909年頭一位得到諾獎的女作家拉格洛芙曾形容“斯德哥爾摩是漂浮在水上的城市”。南區因地勢很高,可鳥瞰斯德哥爾摩的山水,戲劇家斯特林堡著名的小說《紅房間》第一章“鳥瞰斯德哥爾摩”使得南區的摩西坡成為瑞典最有名的山水:“五月初旬,傍晚時候,摩西山頭的小公園還沒有開放,里頭的花壇連土也沒有翻松過,只有那一簇簇的雪花從來年的積葉底下鉆出來,然而這些雪花也正要結束,它們短促的生命,準備把地位讓給那些嬌羞善感,正向那光禿禿的梨樹企求庇蔭的番紅花。紫丁香只等南風一到就要開花了,而那些菩提樹飽滿的蓓蕾已經開始綻出可愛的毛茸茸的嫩葉,引得那些在樹上用地衣做巢的金翅鳥在它們上面飛來飛去。”(張道文譯,1981年人民文學版。我改了摩西山的譯名。)
南區的摩西坡花壇內外的風景絕美,不曾居住過南區的斯特林堡曾經精心描繪過。我對南區高地的深刻印象來自探險家斯文赫定的傳記,他在十五歲那年站在南區高坡觀看探險家諾登舍德從北路穿過白令海峽到達日本最后返回瑞典,當年斯德哥爾摩全城施放煙火歡迎他歸來,十五歲的斯文赫定登高望遠,立定了志向:有為者應如是。
托馬斯住在南區籬笆門大街,外公外婆住在附近,父親在他幼年時離開,圣誕節以及其他時候會來跟他相聚。托馬斯的父親是一位記者,我在托馬斯的家里看過一本他父親撰寫的《斯特林堡畫傳》。外公卡爾·魏斯特白格生于1860年,是一位領航員,也是托馬斯最要好的朋友,他年長托馬斯七十一歲,奇特的是,他跟自己的外公也有相同的年齡差——他的外公生于1789年:“巴黎的居民猛烈攻擊巴士底,瑞典貴族反叛國王的兵變失敗了,莫扎特寫著他的單簧管五重奏。人類歷史上相等的兩步,漫長的兩步,可并不太長。我們夠得著歷史。”我非常喜歡托馬斯這段描述,他外公的外公跟瑞典最早的詩人貝爾曼是同時代人。貝爾曼也生于南區,成名于老城。
南區高地最早叫漁夫山,后來叫卡特蓮娜山,跟教區同名,國王卡爾古斯塔夫十世為紀念母親,在此建造同名的教堂。國王卡爾古斯塔夫十世是凱瑟琳女王的繼任者,也是她的表哥,原來可能跟女王結婚,因女王宣布退位到意大利留學,成為繼任的國王。
斯德哥爾摩有四十三座教堂,卡特蓮娜教堂的建筑不是其中最宏偉的,但在地理上有一種無法替代的美感,你站在市中心王后街的任何一個位置,都能一眼望見卡特蓮娜教堂。教堂不高,教堂周身的黃色漆墻顏色適中,圓身方底的基座不搶眼,你從老城走過泄水道,來到教堂前面的鵝卵石道路,夏夜的暮靄散發出光芒,照在卡特蓮娜教堂的黃漆墻上,變成一座發光的教堂。
教堂曾遭大火燒毀。最早一次于1723年,最晚一次于1990年,這次大火焚燒大半,只剩下教堂建筑本體跟頂蓋,讓從小在南區長大的托馬斯郁郁不樂。幸運的是,教堂以五年時光重修,使用五萬二千根鐵匠手工制作的釘子,磚頭也使用老的樣式,幾乎跟原來的教堂一樣好。
漁夫山的東北角,17世紀有兩座風車磨坊,最早向法庭申請認證造磨坊的人叫賀坎,法庭認為他老實懂事。兩座磨坊都沒有留下痕跡。南區有一條賀坎街,以他的姓氏為名,賀坎的女兒有個猶太人丈夫,名字叫摩西·以色列蓀,似乎繼承了磨坊的家業。17世紀的猶太人不多,早年瑞典禁止猶太人做買賣,遲至1870年法律才允許猶太人成為公民,這里的高坡早于18世紀就以猶太人之名命名為摩西坡,是尊重常民的歷史印記。摩西坡廣場位于山邊,以前有很多民房,1857年被一場大火燒光了,遂成為廣場的一部分。瑞典的漢學大師高本漢晚年一直居住在摩西坡廣場邊上的樓房。
摩西坡廣場有一個凱旋門,進去是摩西坡露臺,這兒就是游客鳥瞰斯城風景的露臺。摩西坡露臺自18世紀以來就是有名的文化娛樂中心,據說吟唱詩人貝爾曼曾在這兒演唱。1896年建筑師費迪南德·布柏(Ferdinand Boberg)建造摩西坡水塔,高三十二米,水塔八角形的紅色磚墻,凹形細磚與花紋豐富的石紋,成為“國家浪漫主義時期”的著名地標。
托馬斯的母親是小學教師,生活勤儉,她一輩子都從南區走路到東北區的小學教三年級跟四年級。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瑞典的博物館已經具備了世界觀。托馬斯是在博物館成長的一代:自然歷史博物館、鐵路博物館是他跟外公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研究員似乎把他當作“同事”,告訴他怎樣收集跟研究標本。夏天托馬斯在首都的一座小島潤馬島上進行自己的昆蟲研究,那座小小的藍房子,空氣里充滿著乙醚的氣味,玻璃罐裝著已死的昆蟲,一塊用尖針釘蝴蝶翅膀的木板——那里已經是個微型博物館。從十一歲到十五歲,托馬斯收集了許多小蟲,尤其是甲蟲。他對非洲探險、中世紀、海底生物的閱讀興趣大過于藝術,十一歲以前的夏天他在潤馬島上想像自己領導一個探險隊穿過非洲中部,那是一種19世紀的探險隊,用仆人攜帶設備,他曾深入研究瑞典跟北歐人在非洲探險過的區域,幾乎閱讀過所有相關的書籍,他也知道這種旅行早就過時了。非洲改變了,屬于英國的索馬里打仗用坦克車,阿比西尼亞是頭一個從軸心國軍隊解放出來的國家。
南區的“公民大廳”建造于1940年,那是一個立方體建筑物,距離托馬斯的家只有五分鐘的路程。那里有一個公共游泳池跟城市圖書館分部。那里的少兒圖書館是托馬斯常常拜訪的地方,多半時間他想去成人圖書館借書,想借閱諸如《沙漠在燃燒》這一類講述年輕探險家在非洲的慘烈生活,圖書館員對這種超齡閱讀的情況非常警戒,最后他的舅舅出面干涉,把自己的借書證借給他,以幫舅舅借書的借口進入成人圖書館。“成人圖書館在游泳池的隔壁,一進圖書館就感到游泳池的蒸汽,以及氯穿過通風設備的氣味。你也聽得見游泳池人聲遙遠的回音。游泳池的音響效果真奇妙。健康的神殿跟書籍當鄰居,一個極好的主意。”
托馬斯持續好幾年都在公民大廳的城市圖書館分部借書,他認為這個分館比斯威亞路的中央圖書館優秀得多。“那里的氣氛沉重一點,空氣好像停止了,沒有氯的氣味,沒有人聲的回音。書的氣味也不同,讓你頭痛。”這個評價相當具有“南區”居民的主觀色彩。中央圖書館為實用功能主義的建筑師阿斯普蘭德(Gunnar Asplund)建造,入口的窄門階梯層層上升,終而見到視野寬闊環繞三百六十度的圖書館書架。圖書館的方形底座圓形堡壘天頂,是著名的圖書館建筑物,世界各國的建筑名家來到斯城,必須來到這里“朝圣”。托馬斯卻說這兒的書氣味不同,使人會心一笑。
2012年春天馬悅然翻譯《記憶看見我》的中文譯本完成,隨即到首都的國立圖書館找出安迪·安德森居住非洲二十五年寫成的《一個斯德哥爾摩小伙子》等多張他少年時候讀過的書封,收錄在中譯本中,出版后送到托馬斯家里,令托馬斯驚喜連連,大笑不止。
自從我到斯德哥爾摩生活,托馬斯與莫妮卡夫婦不時邀請悅然跟我到他們南區徑山街的公寓吃飯,徑山街離泄水道(Slussen)地鐵站不遠,需要再搭一站公交車,到站過街走上“掃帚匠街”的木梯坡道,那里有一排17世紀紅色老木屋,受法律保護,恒常地在太陽下顯現歷史的珍貴,使南區的鄉村風貌那么自然地在托馬斯居家前面,成為美麗的風景,就像托馬斯在傳記筆下若有似無輕描淡寫說的:“我們夠得著歷史。”
2013年春天,中國作家閻連科發表小說《丁莊夢》的瑞典語譯本,來到斯德哥爾摩,與譯者陳安娜在南區的一家書店演講,出版社邀請我們去聽講,我從來沒到過這家書店,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那時候閻連科跟安娜已經坐在書店的櫥窗邊上,那兩張高腳座椅使得講者背對櫥窗,背后發著來自街上的光,晚來的人遠遠從街角望過來,分外神秘。一進書店,店里有一張好長好長的木桌,擺滿了書,四邊書架環繞,這時候我忽然意識到,這家書店就是《記憶看見我》里托馬斯提起的“漢森與布魯士書店”!這家書店竟然還以南區獨特的文化形象存在,盡管書店的名稱換了,《記憶看見我》這本書中所有關于南區的講述,宛如“文藝復興”時期那種教育背景體制的南區拉丁語學校,歷史的影像一下子就在這家書店中立體化起來,生動而觸景生情地立刻將我所有的感知擊倒在地。之后那一兩個小時的演講,我就在閻連科跟安娜倆人溫柔的話語中,如浴春風般享受了一場非常美好的論述,關于小說寫作與社會現實的寓言故事。即使這一天的主題分明接近加繆小說《鼠疫》,我內心的感動卻完全顧不上加繆了。我非常感動閻連科的來訪把我帶進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詩人之城,一個最為核心的場景是:當年托馬斯跟他的青年同學們在此聚會,討論《當月桂樹生長之時》刊物的作品,那時住在東區跟北區的同齡詩人謝爾·埃斯普馬克,以及稍微年輕兩歲的培爾·魏斯特拜都在這個刊物發表作品,托馬斯當時聚會的朋友后來都成為瑞典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家與教授,這里提到的兩位作家都成為瑞典學院院士,前者擔任1998年至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主席,后者2005年繼任諾委會主席。
《記憶看見我》中托馬斯對于這家書店跟學校的高地只寫到這么一小段,卻使人印象深刻:“我的學校位居斯德哥爾摩南區最高的地方,學校院子的位置比那地區大多數建筑物的房頂還高,學校建筑物的磚頭從老遠的地方都看得到。我平常用半跑的方式,完成到達這令人嘆息的城堡路線。我沿著比恩的花園前面長長的木柴堆——那種木堆是戰爭時期常見的——跑上哥特大街,經過漢森與布魯士書店,向左拐進赫白大街。每個冬天的早晨,都有一匹馬站在那兒咀嚼飼料袋中的干草,碩大而冒熱氣的影子中,我對那耐心的獸及其在潮濕寒冷中的氣味,記憶是非常活躍的。一種既令人窒息又令人安慰的氣味。”
托馬斯小學畢業,上了初中,那時候他的小學同班同學沒幾個人上得了初中,只有他一個人申請進入南區只收男學生的中等學校初中。他其實還是一個“小孩”。下課以后他常到一個名叫帕樂的同學家去玩。帕樂跟他很像,獨生子,爸爸是水手經常不在家。帕樂母親很喜歡托馬斯到家里來玩。帕樂跟托馬斯一樣都有收藏的癖好,為著自己的興趣而活,托馬斯描述自己跟帕樂的友誼,很可能是整本書最富有“童心”的一個段落,從冬天在學校看見馬冒著熱氣的影子到下課與帕樂為伴,使我想起兒童文學作家林德格倫《米歐,我的米歐》中米歐王子跟他的同伴的關系,他們都曾在街上看見運送啤酒的馬兒冒著熱氣給他們帶來的活力與安慰。跟帕樂在一起是使人生變得豐富的一種經驗,不久以后,帕樂終將離開人世。他因長期生病轉到別的班級,托馬斯跟帕樂斷了聯系。帕樂偶然出現在學校,變得蒼白而嚴肅,一條腿被鋸掉。他去世以后,托馬斯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他感覺他應該壓制他們兩人過去所經歷的樂趣的記憶:“我感到我跟四十五年前還沒有長大而死去的帕樂,年齡是相同的……在我的內心,我帶著過去所有的面孔,像一棵樹的年輪。這些面孔的人們,總和就是‘我。鏡子所能照出的只能是我最近的面孔,我認識我所有往昔的面孔。”
《記憶看見我》是我讀過最喜歡的一本書,它使我走在斯德哥爾摩的各處照見托馬斯的記憶,不僅僅是因為他是個好朋友,更是詩人獨特的視角與回憶常常使我看見這個城市的面孔有其內心的年輪。那首他年輕時候所寫的六言詩是一個奇特的內心年輪,我朗讀這首詩的沉重的停頓時,會想起像帕樂那樣一個死去的朋友,迷蒙的記憶實在而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