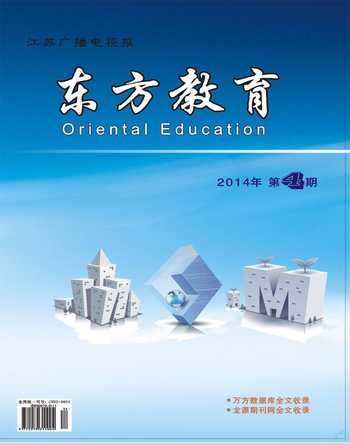淺談話劇的局限性與生長性
李園園
【摘要】地震的公共性限制了話劇《生·活》展開的向度和深度,在很多因素都被預設的前提下,不過,由于很多細節的綻放使其充盈出許多生長的縫隙,才沒有變成一次災難的注腳。但這恰好呈現出一個民族在災難面前的藝術選擇,選擇的內容映射出一個時代的精神底蘊和一個民族對于藝術理解的程度。
【關鍵詞】話劇藝術;表演;現實生活;細節
從某種程度而言地震的公共性限制了話劇展開的向度和深度,已經部分地失去了劇本創作本身的懸念和神秘然而北京人藝還是迅速做出決定,在時間空前緊張的情形下創作關于這次地震災難的劇本。在很多因素都被預設的前提下,話劇《生·活》注定是“帶著鐐銬跳舞”。不過,由于很多細節的綻放使《生·活》充盈出許多生長的縫隙,才沒有變為一次災難的注腳。其實,話劇《生·活》的真正意義不在于具體的劇本內容,也不在于導演的精心指導和演員的深情表演,而在于它是一個典型的范本或案例。因為它恰好呈現出一個民族在災難面前的藝術選擇,選擇的內容映射出一個時代的精神底蘊和一個民族對于藝術理解的程度。
一、“帶著鐐銬跳舞”:如果從歷時性的角度來考察中國話劇,可知它作為一種備受關注的藝術形式,在某些特殊的歷史時刻往往首當其沖,擔當起超出藝術使命的歷史使命。因此,話劇《生·活》的情感訴求遠遠多于藝術訴求。表達災難中堅強的人性是該劇的主旋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場景也是生活的真實再現。對于《生·活》的劇本創作來說,作為編劇不能完全“隨心所欲”,該劇的視角是從一個普通的北京人家切入,講幾個四川保姆和北京人家的故事,來自四川的保姆小菊(陳小藝飾),在她身邊還有幾個川妹子保姆。地震的發生猶如一架浮橋,連接起四川人和北京人;同時,也連接起主演王保年(朱旭飾)和王路石(濮存昕飾)的“前生今世”,親情和愛情逐漸凸顯,但這還是敘事的一條輔線,盡管它們極其富有戲劇元素,但最終不過是表達中心思想的一些步驟而已。所以,話劇《生·活》的創作就有著“先天不足”的劣勢,而且又是在時間空前緊張的狀態下完成的,完全沒有沉潛的時間和機會。
“真實”是衡量話劇藝術的標準之一,那么這種“真實”應該是指心靈的真實,而不是現實的外表,更像是一種靈魂的真實狀態,充滿了豐富的思想和畫面。的確,《生·活》所展示的就是一幅很真實的現實場景,多少四川人為聯系不上家人而膽戰心驚,多少中國人開始捐款捐物,但是作為一種藝術,總讓人覺得有些缺憾。因為作為個體的人在《生·活》中或多或少有些被遮蔽,不是發自內心的主動地探求世界,而是被動地書寫一種現實生活。其實“只要人不能主動發現這個世界的適合于他的思想觀念,人就始終遮蔽著人自身。”也就是說,在《生·活》的創作中,一種潛在的“整體意志”已經基本成型,因此一些“個體意志”就會被忽略,但個體心靈的真實恰恰應該是話劇藝術的重點之所在。
二、在縫隙中成長:我們從王保年身上感受到了充滿選擇和溫情的生活本身,看到了人類掙扎的復雜的精神境遇,這不是對災難的簡單記錄,而是對生活的啟迪。面對親生兒子王延信的告別,他如何的忐忑不安,他不斷地說道:“自己老了經不住事了。”面對王路石關于身世的詢問,他也是坦白地承認自己內心的矛盾和牽掛,也正是因為老人擁有這樣的情懷,才讓我們看到了人生的浩瀚和苦不堪言。小菊的塑造也是比較成功的,她的身上散發著一種純樸恬靜的歌謠氣質,面對家中的災難,她沒有像其他的川妹小保姆,在第二幕第一場的王路石家中,這些川妹子們傾盆大雨式的情感抒發反而有一種華麗掩蓋不住的空洞,尤其是桂枝的詩朗誦實在有些矯情。不過,桂枝在得知弟弟沒了之后的表演真的是挺感人。倒是小菊的默不作聲更有悲劇力量,一個人在默默拖地,一個人又默默準備拆冬天的被子。在地震這個宏大的版圖中,我們從一些具體細節中看到了一些的個性化的伸展。比如,亮亮的遠行和詩歌也使話劇變得饒有趣味,留下了80后們一個灑脫的側影。
對于濮存聽來說,這場話劇并沒有展示出他的精湛嫻熟的表演,因為有些劇情和臺詞限制了他,尤其是最后的誓言讓觀眾覺得可疑,遠赴四川的動力更多的是來自內心一段隱秘而美好的情感。我以為王路石不該輕易把后半生獻給什么,因為他的身后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即將出生的孩子,不要留下太多最終的陳述,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瞬時的解釋。當然,對于小菊和豆豆的照顧也是王路石尋找救贖的一種方式,對于曾經心愛女人付出的感恩和補償。不過,當他顧自走到記憶中的四川時,那段深情的描述看到了一個實力派演員的璀璨之處。“回憶”作為一種插入的敘事,就承載著更多的意蘊,具有雙重性。因為那些留在內心深處的點滴記憶是最自我的表現,也是最真實的影像。更重要的是,個人記憶以話劇的方式獲得了延續,并慢慢融進民族的歷史記憶中,還原了整個民族某個群體的愛情史和精神史。“記得”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太重要了,這或許就是《生·活》在努力達到的一種境界,不僅要記住四川地震,更要記住中國曾經有過的歷史。
盡管這部作品存在很多讓人遺憾的地方,但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呈現出一個民族在災難面前的一種藝術選擇,映射出一個民族對災難和藝術的理解程度,也留下了一個時代精神面貌的側影。無論是作為個體行為,還是作為集體行動,每個中國人都將銘記這段歷史,都有責任將之傳承,但是傳承的方式和角度尤其重要。無論如何,中國人藝藝術家們對于地震參與的行動和熱情遠遠超過了《生·活》這部具體的作品,從這個角度來說,話劇《生·活》的意義是雙重的,是一種“雙重見證”。
參考文獻:
[1]歐陽予倩.話劇新歌劇與中國戲劇藝術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2]吳曉東.記憶的神話.讀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