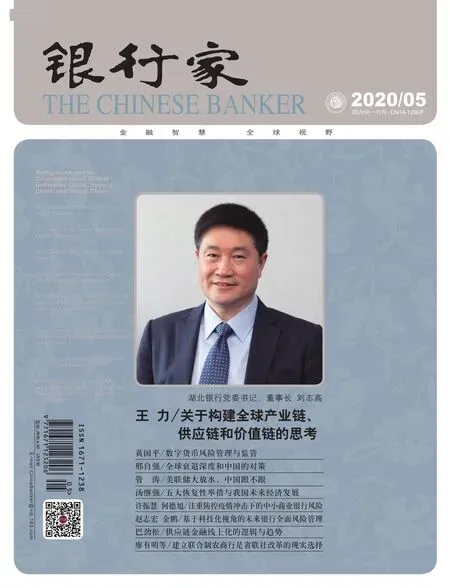再說五四運動
高續增
一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5周年了,但它依然在影響著現代中國的社會生活。我已經記不起寫過多少篇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了,只是記得每一次撰寫都能引發新的思考帶來新的收獲。
開始,五四運動是幾個青年人挑頭鬧起來的,就從它的這個來歷講,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不應當超越公車上書、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那么為什么人們就那么認可五四運動呢?
現在所有中國人都同意這樣一個觀點:五四運動是個分水嶺,它是開啟中國現代史的門檻,是關閉中國封建社會的一扇窗牖。也有學者把早它八年的辛亥革命作為一座分水嶺,但是我認為若以文化轉型為標志,還是讓五四運動來充當分水嶺為好。
作為一個歷史事件,五四運動也有其瑣碎的相關細節,做大歷史敘述時,可以把它們虛擬化,但是如果出于某種原因有意抹殺,就不很合適了。經過閱讀這幾年不斷披露的資料,現在可以有以下這些不為大家知曉的細節公之于眾了。
根據歷史教科書的正統記載和敘述,發生五四運動的5月4日那天,更多地是讓人們見識了幾個反面人物——章宗祥、陸宗輿,正面人物卻都很模糊,其實,向后人敘述歷史時應當盡量全面地展示其全貌。
二
要是真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必然要發生的歷史事件來對待的話,事情還要從五四運動的前一年——1918年說起。
1918年的5月7日,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東京會議所簽訂的《中日兩國防敵條約》侵害了中國的權益,多名中國留學生被日本警察署逮捕,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的極大憤怒,其中的1000多人憤而歸國。在北大第三院舉行的學生大會上,回國的留日學生向與會的1000多名北京各所大學的學生和來自天津的學生代表痛陳他們在東京受辱的情形。5月21日,京津兩地的學生結隊向總統府請愿,反對《中日兩國防敵條約》的簽訂。這場學生運動中最為突出的人物是天津女學生郭隆真,她在徐世昌總統僅派其秘書接受學生代表的請愿書之后,學生們即將散去時,憤然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一場,表示抗議。這一幕成了天津學運史上的高光,北京的大學生們也因此大受刺激。嗣后,北京大學的學生于1919年1月1日創刊《國民雜志社》,其中主要的積極分子有易克嶷、張國燾、許德珩、陳鐘凡、黃建中,發起人是易克嶷。《國民雜志社》的社員們后來成了五四運動的發動者和組織者。
1919年5月2日晚7時,《國民雜志社》召開例行社務會議,在此前,《國民雜志社》已經出版了4期。在第五期編務會議上,與會者不約而同地提到了中國在凡爾賽和會上受到的屈辱,張國燾提議:由《國民雜志社》發起,發動北京各學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游行,向日本使館提出抗議,要求收回日本在山東接收德國的權益,取消《二十一條》。在這次會議上,以《國民雜志社》的名義通告北大全體同學,在次日5月3日晚7時,在北大第三學院召開學生大會,并邀請北京其他高等學校的學生參加,當時就推選易克嶷為大會主席。
第二天晚7時第三學院大禮堂人聲鼎沸,大會主席易克嶷宣布大會開幕后,張國燾、許德珩依次上臺發言,把一天前商定的主張向與會學生進行宣講,謝紹敏同學激動地咬破中指,在一塊白毛巾上血書“還我青島”四個大字,使得大會氣氛達到高潮。大會最后決定第二天,即5月4日上午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游行。
第二天上午,蔡元培校長得知消息出來制止,學生們不顧蔡校長的阻止在一片口號呼聲中浩浩蕩蕩地向著天安門進發了。由于路途關系,北京其他高等學校的同學先行到達了天安門廣場。3000多名北京和天津學生開赴東交民巷向日本使館遞交抗議書。但是,依據有關條約規定,東交民巷不準中國人聚集活動,學生們只好派代表向各國使館宣示示威意圖,大隊人馬則涌向北洋政府內親日派頭領曹汝霖的家——趙家樓。在趙家樓沒有遇到曹汝霖,卻巧遇另一個親日人物、駐日使館公使陸宗輿,陸宗輿避走不及,被學生們痛打一番。學生們看到曹家設施豪華,擺設講究,頓生怒火,最后一把火燒了趙家樓,學生們旋即散去。隨后趕來的軍警把未能來得及離開的32名學生抓捕進警察局。
三
北京在5月4日發生的事件迅速震動全國,這就是對中國歷史具有深遠影響的五四運動,后來發生的其他細節就與公開的史料大致相仿了,只有一件事情,未曾引起社會的注意,那就是對“放火事件”的追究問題。
根據當時已經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的看法,五四運動中學生放火事件必須用法律手段予以追究,不如此不能嚴肅法紀。梁漱溟在就此事所寫文章中表達的意見是:學生打人應當是犯法在先,放火事件在先,這首先就要追究法律責任。具體處理方式應當是判定有罪,政府若以學生愛國義憤為由再特赦之是最好的結果。梁漱溟說:“如果我是這些學生,我寧愿真的坐這個牢,因為我確實犯了錯。”在現在我們許多人看來,梁漱溟先生真是書生氣十足,怎么就偏偏盯住那么一個偉大事件的“陰暗面”呢?
而我以為,梁漱溟先生的這個意見應當不因為時間的遠去而銷聲匿跡,因為后來發生的更大的事件就把這個“陰暗面”無限度地放大了。
五四運動過去47年后的1966年,那些效法五四運動時期的激進分子——紅衛兵,就以“革命運動天然合理”為理由,大搞打砸搶抄抓,無視憲法關于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規定,“掃四舊”、批斗“黑五類”設立“牛棚”關押未經法律程序審判的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這些無不是以五四運動為藍本的過激行為。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人類文化的進步,無論是具有多么偉大意義的歷史事件,也會有它的局限和陰影,真正從人類進步的角度看問題的先驅者,應當全面看待和分析社會進步進程中的所有影響,尤其是那些對歷史進程掌握絕對權力的責任者,更應當有這樣的責任和清醒的認識。
四
五四運動期間,最被人們所忘懷的是社會文化躁動。那時,所有對國家事、天下事予以關注的人和媒體都要對中國未來的走向發表高論,一時間產生了多種多樣的救國論。現在為大多數人所知道的只有科學救國論、產業救國論,實際上還有別的許多救國論,這反映了當時各行各業的有志之士都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力挽狂瀾,積極參與救國運動。而今,國難早已成了過去時,但是把那些救國論翻騰出來還是有意義的,這樣做不但可以用來遙祭五四運動,還能重新發現一些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逝去的某些史料和精神文化成果。endprint
教育救國論。教育救國論者,有足夠的理由起身喚起民眾對教育的重視,因為當時的東鄰日本就是用極其匱乏的國家歲入盡量多地用在國民教育方面的,以至于這個彈丸小國用了不過三五十年的時間,一躍成為可以與西方列強一比高下的新興力量。有一篇署名“云窩”的文章——教育通論,說了一句很有穿透力的名言:“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作者還說,各國之競爭,不在兵戰、商戰、農戰、工戰,而在于學戰。至今思想起來,仍然倍感深刻,令人動容。一位名叫章天覺的學者說的話,好像竟然是針對今天教育界的時評:“須知教育是社會的生命,旁的人腐敗尚不打緊,教育界腐敗那簡直是災及子孫斷送你的后代,使得我們中國永遠不得翻身!”
教育救國論中的極端論者,是“教育萬能論”,更是把教育的社會功能幾乎捧上了天。然而,透過這些看似偏激的言論,人們都能體味出論者那顆拳拳的愛國之心。
美育救國論。持此論者,認為中國人之所以陷入紛亂,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像西方國家的那種美育氛圍。《少年中國學會》發文尖銳地指出:“世界上的紛亂,人類的不安全,大而至于攻城掠地的慘劇,小兒至于睚眥意氣的惡鬧。都是沒有美育的緣故。美育是一個改造人間的福音,鏟除萬惡的利器,是一切教育宗旨里的先決問題。”五四運動時期的重要文化人王統照說:“美育這二字,是將人類引致崇高愉快光明的地方去,將那些無論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煩悶一概排除了去,使人生達到完美安善之地。”
當時最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是主張美育救國論的統軍人物。
地方自治救國論。不少學者思考中國事,都會把中國太大、難以整體崛起視為畏途,于是就產生了地方自治救國論。康有為就是這個論調的大旗。他說:“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勢也。歐美之所以勝于中國者,在以自治而不代治之也。”還有個當時很年輕的愛國者發表了這樣一份言論:“我是反對‘大中華民國的。……我主張中國原有的二十二個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小中國,從湖南共和國做起。”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他還強調:“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中國唯一的法子。”(見1920年9月3日《大公報》)
此外,還有事業救國論、科學救國論、思想救國論、農業救國論、醫學救國論、體育救國論、宗教救國論……。
俱往矣,如今逝去的是生出這些五花八門言論的百花園,留在人們記憶中的是五四運動時期所呈現出的民族青春的活力。
五
我們應當怎樣評判五四運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呢?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的歷史已經被皇權壟斷了兩千多年,民眾沒有對民族和國家大事“說三道四”的權利,歷史怎么發展,文化怎么培育和改造,歷史事件和人物怎么評價,都是“上頭”說了算。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也因此而走上了歧途。在中國傳統線性的哲學思維的引導下,社會上的事情只有“陰”和“陽”兩個對立面,或“是”或“非”,沒有中間可以轉化和變動的余地。于是才有了那黑暗的兩千年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
五四運動的最大意義在于,它標志著中國民眾斗爭有了表達自己意愿的方式和權利,這是受到西方人的人權理論和意識的影響才徹底覺悟到的。但是從具體方式方法上又不可避免地帶著中國人行事的烙印,民眾不成熟的社會意愿的表達沒有現成的社會行為約束體系的規范,于是,五四運動不可能沒有被挑剔的地方。今天,當我們從遠處眺望五四運動的時候,應當意識這一點,這樣做對今后思考社會民主政治的走向是有時代意義的。
我更愿意把中國的五四運動與西方人的宗教改革放在相似的平臺上來認識,只不過西方人的宗教改革從社會知識層發起后,最后成為全社會文化主體的主流精神,而中國的五四運動的宗旨——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則始終未能徹底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
五四運動所開啟的新文化運動更是五四運動的一大功績。
在五四運動以前,在各大學里已經有各種思想激進出版物陸續創刊,但是這些數量很少的思想性刊物,在中國億萬民眾中間的影響非常有限,更像是象牙塔里脫離民眾的金貴藝術品,它們與占人口九成以上的民眾的距離遙遠。但是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的精英都意識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責任感,由此現代社會的中堅——中產階級開始形成。以往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階層和只管自家生計的草根階層為主體的民族人口結構迅速分解轉化,為中國的社會文化轉型預備了必要的基礎條件。
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當時的人們為什么那么強烈地否定傳統社會的精神支柱——儒家學說呢?這就要說說五四運動與舊的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了。
六
五四運動開啟的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砸爛孔家店”,一時間,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激進的口號,甚至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中國的文化傳統面臨嚴重的危機。
即使是現在,擺正傳統文化與外來先進文化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五四運動發生的當時,處于新文化運動領袖地位的蔡元培先生的意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閃著歷史高光的真知灼見,它所標示的北大精神——“兼容并蓄”,就很好地把握了繼承傳統與創新開放之間的關系。當時的北大,既聘請了思想激進的陳獨秀李大釗等共產主義者擔任教授和學長,也延聘了像辜鴻銘那樣依舊堅決保留腦后長辮子的守舊派知識分子,只要他們真的在努力做著學問并有自己的獨特建樹,并不以所謂“思想先進”或“意識落后”作為選人的標準。上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沒有留洋的學歷和驕人的名氣,就因為他的一篇長篇論文——《究元決疑論》受到蔡元培先生的賞識就從一個普通記者的身份轉到最高學府北大當上了講師。人才濟濟的北大隨后就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對中國社會的進步和轉型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重要口號是“砸爛孔家店”,在當時看來,人們不應當苛求這個激進口號的負面作用,因為要把一個新的思想注入中國社會,一定要爭取到一個有效的空間,而儒家學說把持了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話語權,不向儒家文化的總代理——孔家店——索要空間,就沒有新文化容身的余地。但是現在看來,在塵埃落定之后,真正的五四運動精神的繼承者們應當冷靜地看到,五四運動的矛頭所指向的傳統文化,應當在新的歷史時期中也有資格占有一席之地,只是應當把那些披著孔孟學說外衣的皇權政治的產物盡數清除出去。因此我同意一些頭腦清醒的學者的見解:把那個口號改為:“砸爛孔家店,解救孔夫子”,孔夫子其實與孔家店根本沒有什么必然的聯系,是專制社會的御用文人盜用了孔夫子的只言片語在加上一些封建社會的尊卑倫理,才有了孔夫子身后的孔家店。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近一個世紀,中國的社會轉型仍處在進行時中,遠遠未能見到窮期。今天的人們紀念五四運動,更要落實于以五四運動的精神,促進中國社會向著現代化的方向盡快地順利地轉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