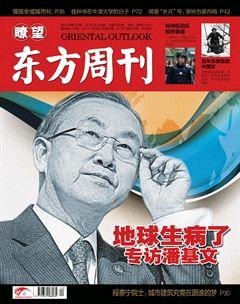中國藥業頑疾纏身
劉武

中國藥業為國為民貢獻卓著,但是,救人卻難救己,多年帶病運轉,自身已頑疾纏身。
2014年5月15日,輿論義憤填膺地曝光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GSK)商業賄賂,5月18日,三精制藥董事長劉占濱被立案偵查期間跳樓身亡。
多數業者心知肚明,目前只是稍稍念了幾句經,整個醫藥業就有些亂套。
注定會鬧烏龍的國際比價
媒體圖文并茂地報道GSK行賄案時,將其瘋狂撈金、大肆行賄的“長城計劃”“龍騰計劃”加以細致描述,GSK的虛偽面目暴露無遺。
但在關鍵細節上,媒體偏偏鬧出烏龍,將在華一盒的價格與國外一片的價格作比較,得出“賀普丁在中國的零售價是韓國七倍”的爆炸性結論。結果引來一片為GSK叫屈的聲音。
這著實讓人難堪。為了證實這是否屬于一次媒體烏龍報道,好事者們很快就從國外不同網站扒來了一組組數據。
其實,這并沒有太大意義。藥品的國際比價看起來簡單,實則知識含量很高,得出的比價結論幾乎必然招致爭議。
藥品比價對數據信息的要求很高、工作量巨大。不同國家和地區,選取樣本藥品的劑型、單位劑量、包裝、樣本匹配準則、價格層次(出廠價、批發價、零售價)、單位價格的確定、價格水平差異量化、貨幣轉換方式、價格權重、藥品消費習慣,等等,都會影響結論。
同一組原始樣本數據,不同的方法學,甚至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2001年,國內專家比較上海與美國23種藥品的平均價格水平,發現如果按當時的匯率換算,則美國藥品平均價格高于上海;如用購買力平價換算,則上海藥品的平均價格高于美國。
對計價單位選取不同,結論也可能不同。比如,一項國外研究中,以樣本藥品每最小用藥單位的價格作比較時,藥品的價格指數日本比美國低37%;而以每毫克有效成分的價格作比較時,則日本比美國高66%,因為日本的藥品單位劑量普遍低于美國。
可能更加令人沮喪的是,藥品國際比價的結果對方法學非常敏感。通過一些方法學做出來的國際比價,最終對反映消費現實有多大意義呢?
2013年8月13日,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中提出,“比較不同國家的藥品價格既挑戰研究人員的智力水平,又給咨詢公司帶來豐厚的報酬,同時也是擺在醫藥公司眼前的一道難題。但不論在富國還是窮國,醫療體系對藥品跨國比價的需求都在與日俱增。”
在中國,上世紀90年代末就已經出現了藥品國際比價的需求。由于當時大量進口及合資藥品出現在臨床藥品目錄中,政府、醫院、企業、患者都很關心這些藥品的價格水平。
于是國內有專家就展開藥品的國際比價研究,比如,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的專家就曾對當時一些臨床常用藥品在中國和歐美亞七國(地區)的價格進行比價,得出的結論包括:進口或合資藥品的價格與發達國家價格接近。
藥業這么亂,有藥治嗎
強調國際比價的現實困難,并不是說GSK轉移定價、商業賄賂就該逃避公眾的譴責和中國法律的制裁。
GSK“撈金術”被詳細披露之后,業內反應不一。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牛正乾評價說:“這只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孤立案件”。
由于具有特殊的專業屬性,醫患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加上現行體制機制的原因,醫患之間經濟利益經常不一致,這就使得在疾病這個共同敵人面前,本來應該是“戰友”的醫患關系變得極其脆弱,人性中“惡”的部分被激發。
近年來,相關部門出臺很多政策來激“善”抑“惡”,大多事與愿違。原因并不復雜——智商發達、技術專業的醫生們,總有用之不竭的招數跟主管部門過招,而因此利益受損的往往是老百姓。
由于一些歷史性的、如今已然不當的體制機制,使得在藥品零售環節,醫院占據80%的市場份額,具有明顯的壟斷地位。對上游商家,醫院處于買方壟斷;對下游患者,醫院處于賣方壟斷。
在一些廠商的思維里,搞定醫生基本就搞定了一切。當然,那些想分羹的官員,也是要搞定的。這種思維根深蒂固。可以想見,整體而言,醫務人員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住這種兇猛攻勢。
據已披露的GSK案情,GSK通過大肆賄賂醫院、醫生、醫療機構、醫藥相關協會組織等醫藥銷售相關部門及其所屬人員推銷藥品,牟取非法所得數十億元。“大客戶團隊”每年公關預算費用近千萬,主要任務是對全國眾多醫生行賄。賄賂成本預先攤入藥品成本。
GSK對醫生的賄賂方式主要是藥品回扣,美其名曰“講課費”。根據近年來查處的涉及國內制藥企業的商業賄賂案件來看,其賄賂手段也大同小異。
“會議+廣告”的銷售模式是當前“中國式”藥企營銷生存之道,雖然效果越來越差,但它就像一劑毒藥。這藥,貌似還停不下來——“廣告+會議”費用的年增速遠超營業收入增速。
去年GSK事件爆出后,業內“會議”短暫平息了一段時間之后又大肆興起,去年不少藥企會議費增長速度超過100%。
2014年4月初,三精制藥發布2013年年報,投資者發現,三精制藥2013年凈利潤同比劇降98.23%,只有646萬元。但是,廣告費支出4.31億,是凈利的66倍。“4億廣告費換來利潤600萬”的質疑隨之而來。有業界傳言,這輪質疑或許對劉占濱自殺影響較大。
再問“誰在扭曲藥價”
理順藥價是醫改理所當然的重點。近來,在抨擊“藥價虛高”多年之后,呈現“虛高”和“虛低”并存的扭曲局面。
2011年5月,本刊曾對“誰在扭曲藥價”進行了調查,生產企業、流通企業、醫療機構都對藥價問題感到沮喪而又委屈。但是,至今整整三年來,文中很多結論一次次被佐證。
曾幾何時,外資制藥企業風風光光進入中國投資,以“原研藥”之名長期享受定價上的超國民待遇。國家相關部門近年來啟動數十次藥品政策性降價,對擁有單獨定價權的外資“特權藥”影響甚微。“特權藥”已是醫藥行業頑疾。
某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揚子江制藥企業董事長徐鏡人痛陳“特權藥”現象,“總好像低人一等”。
“特權藥”不但高價格,還占據高市場份額,在一線城市的二三級醫院占比近70%,整體占據全國接近30%的市場,在心血管治療藥等醫院常用藥中,占比遙遙領先。
外資藥企堅持“原研制藥品應該依照國際慣例定價”。這次GSK案件中披露的轉移定價手段,不知屬于哪種國際慣例?2010年12月的一次政策性降價,被業內認為是中國主管部門第一次對外資特權藥動刀。但是,那次的政策卻受到強勢的外資藥企近乎羞辱性的對待。
一些機構預計,外資企業原研藥銷售額占其總銷售額80%以上,要“特權藥”降價,就意味著可能明顯傷害財務報表。外資藥企拒絕降價常常軟硬兼施,一方面向政府提交數據,證明其在中國出廠價的合理性。另一方面,間接以在華投資作籌碼。
同時,他們還善于將訴求的“合理性”傳達給政策制定者,請相關部門的官員、醫療專家出國考察。
有時外資藥企也不含蓄,直接提要求。比如2004年6月,歐美制藥企業向中國政府提出單獨定價的要求。事情由頭是我國價格主管部門在2004年及以前的多批次降價,引起諾華、羅氏、惠氏、默沙東、德國先靈等幾十家外資藥企不滿。
取消外資藥特權待遇只能分階段實施。因為其中一個尷尬的現實是,一些中國制藥企業甚至恐懼外企產品降價——一旦外資藥品降價,中國企業的仿制藥不僅質量沒有優勢,連價格也沒有優勢。
扭曲藥品市場價格的,不單是部分外資制藥企業。事實上,涉及藥品的多個環節都發現過價格違法行為。究竟誰才是藥價扭曲背后的推手?是廠家、中間環節,還是“以藥養醫”。
國內藥品生產企業很委屈,據說它們的含稅利潤一度只有10%;流通企業早在2006年就嚷嚷進入 “微利時代”;醫院和醫生更委屈,而且醫改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仰仗醫生的積極性。
目前,國際有影響的藥品價格管理模式都有優勢,也存在弊端,還沒有一種藥品價格管理模式是完美的。當然,無論政府主管部門還是市場主體,沒補齊的短板就得抓緊補齊,不補齊就永遠會有過不去的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