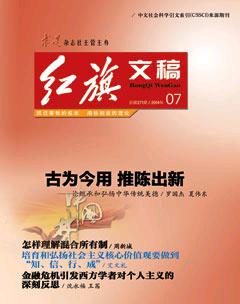“高粱:為什么私有化不是國企改革的方向”等8則
高粱:為什么私有化不是國企改革的方向
理論界的一種流行意見,主張國企應該實行徹底的產權改革即私有化。理由是:私有企業才是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國有制的效率必然低于私有制。而對現實中國有企業效益的提高、在各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則找出種種理由予以貶低或否認。但事實是國有企業能否在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關系到國家發展的方向、道路,關系億萬人民未來的命運。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必然表現為國有制。由政府機構具體管理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必然提出用何種形式保證全社會所有的實現、防止公權私用的問題。就一般意義看,國有企業是國家推行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的最有力的組織保證。我國1978年后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其主要動因,一方面是“文革”的后遺癥(工業管理松弛、干部職工積極性下降);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本身的原因。二是多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演變的基本特點是“國退民進”,不存在“國進民退”問題。三是對各種所有制要理性分析,國有經濟支柱作用不可否認。四是國有骨干企業是推進發展戰略的中堅力量。
(來源:《經濟導刊》2014年3月號)
姜勝洪:不甘寂寞的西方“普世價值”觀
一直以來,有一些人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 “普世價值”觀混為一談,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普世價值”觀,而絕不是中國特色。有人歪曲說:十八大報告“第一次提出了肯定普世價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普世價值列入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范疇”。在“普世價值”信奉者看來,黨的十八大倡導培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他們一貫所說的 “自由、民主、人權”等概念。而實際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以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為代表的西方“普世價值”觀有著本質的不同。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根本內涵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歷史性、具體性及現實性,我們講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既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涵的規定性,又有社會主義法律的規定性。而“普世價值”觀的內容具有抽象性、虛幻性甚至殖民性、侵略性,“普世價值”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的階級性不同。前者屬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后者屬于資本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普世價值”觀宣揚的價值內容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宣揚“社會本位”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所謂“社會本位”是指以國家、社會、集體的價值滿足為衡量價值和判斷道德的準繩。“普世價值”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宣揚“個人本位”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體現極端個人主義、專制主義、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24日)
羅先進:社會正向效應的形成機制
社會正向效應一般是指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社會實踐活動,努力做好人好事所產生的一種健康樂觀、積極向上的社會動能,所創造出的一種催人奮進、給人力量的社會效果,也是國家、民族素質的體現。同時,這種良好的社會效應又反哺個體的成長,從而形成個人與社會的正向互動。一是 人民大眾的涵養實踐,是形成社會正向效應的基石。人民大眾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主體,也是推動社會形成正向效應的主體。二是黨員干部的垂范引領,是形成社會正向效應的關鍵。領導干部的垂范引領,不僅是促進作風建設的關鍵,也是推動形成社會正向效應的關鍵。三是黨委政府的統籌協調,是形成社會正向效應的組織保障。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3月19日)
王東維 高曉彬:“中共自始至終將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視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
延安時期,以埃得加·斯諾等為代表的一批國外記者,以及美軍觀察團等外國人先后來到延安,他們以局外人的視角觀察根據地的黨群關系。從人民群眾的角度講,能否帶領他們過好日子是贏得他們最終支持的關鍵。對此,杰克 ·貝爾登這樣評價:“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因而能夠奪取政權。共產黨是靠踏踏實實爭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談的政治哲學獲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是靠喚起人民內心的希望、信任和愛戴,不是靠空談道理而贏得人民對他們事業的支持。”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土改運動、大生產運動等,努力解決老百姓吃飯、穿衣、衛生、婚姻等問題,切實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對此,馬克·塞爾登總結到:“中共自始至終將維護農民的物質利益視為安身立命的重心所在。”除了物質利益,共產黨也關注群眾的精神文化利益。尼姆·威爾斯說道:“能讀能寫似乎把紅軍戰士提高到不同的思想水平。中國人民總是可憐巴巴地急于想抓住任何一個學習機會。為了送兒子上學,一個農民幾乎不惜犧牲一切。這就是共產黨所以得人心的一個原因。”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2期)
張濤甫:“西化”限制中國傳統的推陳出新
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崛起的過程就是國家自信重建的過程。近代一百多年積貧積弱,包括中國淪為西方列強半殖民地的遭遇,是中國人集體心理不夠強大的真正根源。直到今天,那一個多世紀陰影對中國社會的籠罩仍沒有完全散去。徹底解決中國人的自信問題,需要一段很長時間的努力,這個時段將比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更長。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首先要看精英群體的作為。但是,長期以來,中國精英們的文化自卑感幽靈般如影隨形。特別是我們的知識精英,從理智到情感,被西方文化套牢。余英時認為,知識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為范式,并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來重建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不但沒有獲得其應有的位置,而且愈來愈被看作是“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動者對文化傳統的憎惡便隨之更深一層。這一心態的長期發展終于造成一種普遍的印象,即以為文化傳統可以一掃而光,然后在一張白紙上建造一個全新的中國。這種“西化”意識阻礙了知識界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正確定位,也限制了中國傳統的推陳出新。
(來源:《社會科學報》2014年3月6日)
賈振:陽光辦事打破“熟人關系”
當下,辦事“找熟人”是不少人崇尚的行事方法,辦事“唯親”是少數干部的一種慣性行為。這就導致了“走后門”的歪風在一些地方盛行,甚至出現了一邊痛罵“走后門”、一邊又設法“找關系”的怪圈。這是現實社會的無奈,也反映了權力運行的失范。不鏟除這種根深蒂固的熟人社會歪風氣,教育實踐活動如何能讓干部真入心、讓群眾真信服?第二批活動正在蓬勃開展,是時候動手解決少數干部“合意則取、不合意則舍”的錯誤傾向了。沒有熟人也能辦事、辦成事,有熟人而不合規定,就辦不成事,我們的社會才能不為熟人所困,不為人情所累。一方面,活動應感化干部的內心世界,通過“心有公平秤、辦事水端平”的案例,引導他們生成“敢破關系網、熟人圈”的勇氣和魄力,真正做到“心為民所思,身為民所行”。另一方面,要實打實地改善窗口服務質量,盡可能簡化辦事手續,著力推進陽光公開,讓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公平正義。用群眾的他律促進干部的自律,才能真正在全社會形成“不找熟人找法律”的辦事風尚。
(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3月21日)
楊承軍 蔣政:烏克蘭首先在網絡被瓦解
烏克蘭危機,網絡輿論也是左右政局的推手之一,西方尤其花了很大心思。這給我們留下諸多警示。自烏克蘭暫停“聯系國協定”的各項準備工作后,歐美國家對此極度不滿,隨即加大了對烏克蘭當局進行網絡監督和控制的力度。一是引導并操控社會輿論,這次烏克蘭劇變,歐美國家重視運用網絡手段制造和傳播政治謠言,采取了竊取、攔截和攻擊等多種技術方式,使烏克蘭主流網站輿論幾乎一邊倒,充滿對政府的批評和攻擊,使國民不滿情緒迅速蔓延。二是實施網絡監控和信息攻擊,歐美國家強化監控烏克蘭政府和軍隊網站,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病毒攻擊。據稱自2013年9月份以來,烏克蘭政府官網和國家安全局網站近百次地受到境外黑客攻擊。三是歐美國家對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和相關網絡信息,使反對派對當局的動向和軟肋了如指掌,最終導致官方網站的徹底癱瘓,為顛覆政權奠定了基礎。
(來源:《環球時報》2014年3月21日)
馬凱碩:西方應向中國取經
有人注意到了西方10年來一連串的地緣政治失敗嗎?盡管采取了大規模軍事與金融干預,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在走向失敗。三年前,美國宣布:“為了敘利亞人民的利益,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臺的時候到了。”可阿薩德仍在執政。而如今,西方幾乎要把俄羅斯變成敵人,這無異于為中國送上一份地緣政治大禮。這些失敗的原因何在?原因簡單得令人驚訝。在保持了兩個世紀的成功之后,西方領導人想當然地認為,他們的角色就是維持西方勢力的擴張。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充分意識到一個不可否認的新現實:西方的真實挑戰在于應對衰落。所以,西方應當如何應對自身的衰落呢?三個簡單步驟就能產生很大效果。第一,停止推廣民主的意識形態“十字軍東征”。實際上,西方在烏克蘭的慘敗,直接源于西方鼓動烏克蘭民眾上街抗議、而非鼓勵對立陣營政治妥協。第二,接納俄羅斯,并且是有意識地這樣做。第三,西方應當研究和學習中國。中國沒有動搖世界秩序便成為了世界第二號大國,這幾乎是一個地緣政治奇跡。
(來源:《觀察者網》201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