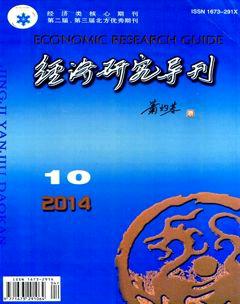解讀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
張科
摘 要: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問題歷來是研究馬克思哲學和黑格爾哲學和探討馬克思哲學與西方哲學發展史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思想繼承、質疑、批判的過程中完成的,分析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對于理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馬克思;黑格爾;關系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0-0008-02
一、“依附性”關系
把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看成是“依附性”的關系,就是傾向于強調馬克思對黑格爾的依附性,強調馬克思思想始終是在黑格爾的拐杖的扶持下向前發展。甚至有人認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馬克思與黑格爾是完全一致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把馬克思黑格爾化了,或者說,使馬克思成為了一個黑格爾主義者,具有這種觀點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杜林和盧卡奇。
杜林在評述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1867)時寫道:“這一歷史概述,在馬克思的書中比較起來還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拋掉博學的拐杖,而且也拋掉辯證法的拐杖,那或許還要好些。由于缺乏較好的和較明白的方法,黑格爾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靠它的幫助,未來便從過去的腹中產生出來。”[1]按照杜林的理解,馬克思在敘述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時,借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拐杖”,特別是讓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在這里執行助產婆的職能”。杜林對馬克思和黑格爾關系的理解顯然是錯誤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馬克思確實使用了“否定之否定”的提法,而馬克思對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趨勢的診斷究竟是在黑格爾辯證法的“助產”下作出的,還是通過對經濟學方面的獨立研究作出的?恩格斯為馬克思做了申辯:“當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為否定之否定時,他并沒有想到以此來證明這一過程是歷史地必然的。相反,他在歷史地證明了這一過程部分地實際上已經實現,部分地還一定會實現以后,才又指出,這是一個按一定的辯正規律完成的過程。……那么這些論斷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純粹的捏造。”[1]在恩格斯看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思想之間存在著差異,他堅決反對杜林把馬克思曲解為黑格爾主義者的錯誤的見解。恩格斯的申辯是有說服力的,因為馬克思在考察一切歷史現象時,都是堅持從具體的歷史出發。
盧卡奇從學理上強調了馬克思哲學的黑格爾深淵,從而對理論界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談道,“不是經濟動因在歷史解釋中的優先性,而是總體的觀點,構成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決定性的區別。總體性范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優先性,是馬克思取自黑格爾并獨立地轉變為一門全新的科學的基礎的方法論的本質。”[3]從總體上看,盧卡奇闡述的正是馬克思和黑格爾在思想上,特別是在方法論上的共同點。但是盧卡奇在理解馬克思和黑格爾關系也不是合理的,其實,他已在《歷史與階級意識》“再版前言”中把馬克思思想黑格爾主義化的錯誤傾向做了自我批評,他承認“我對黑格爾的非批判的態度當時還沒有被克服”。到1930年,盧卡奇在參與對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整理時,他唯心主義傾向有了清醒認識:“在閱讀馬克思的手稿過程中,《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所有的唯心主義偏見都被一掃而光……,然而,這樣的事情并沒有發生,顯然是因為我一直按照我自己的黑格爾主義的解釋來讀馬克思的。”[4]他致力于尋找和發現馬克思與黑格爾在思想上的共同點,在把馬克思黑格爾化的同時,他也把黑格爾馬克思化了,在理解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上,仍然是不合理的,不是依附性的關系。
二、“斷裂”關系
雖然馬克思曾經是一個青年黑格爾主義者,然而,他的思想在1845年前后與黑格爾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之后,馬克思與黑格爾就完成分道揚鑣了。 “斷裂論”者認為,只有讓馬克思從黑格爾哲學的陰影中完全擺脫出來,才能正確地把握馬克思哲學的實質。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
阿爾都塞從“科學和意識形態的對立”的區分原則出發,研究馬克思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關系[5]。在他看來,科學和意識形態是完全對立的兩個不同的總問題,馬克思的思想經歷了從青年時期的意識形態總問題向成年時期的科學總問題的“認識論的斷裂”的轉變,從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因此他反對將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人道主義化的做法。他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是通過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顛倒而來的,是在剝去了黑格爾體系的神秘外殼后發現其合理內核而創立新世界觀的。他批評這種看法是一種折衷主義的表現,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并不能說也不能想象“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旦被剝去外殼就可以奇跡般地不再是黑格爾的辯證法而變成馬克思的辯證法”[6]。辯證法和黑格爾的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有根本區別的,“明白地說,這就意味著,黑格爾辯證法的一些基本結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同一、‘揚棄、質轉化為量、矛盾等等,到了馬克思那里就具有一種不同于原來在黑格爾那里的結構。”[6]他認為馬克思和黑格爾辯證法的不同主要體現在其辯證法內在的總體性和矛盾觀是有根本區別的。他既批評盧卡奇等人只看到馬克思和黑格爾思想的聯系而忽視二者的本質區別,又反對那種把馬克思的歷史觀看作是黑格爾歷史觀顛倒的觀念。他認為,馬克思創造性地使用了兩類嶄新的范疇:一類是結構方面的,它包括經濟基礎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范疇;另一類是上層建筑方面的,它包括國家、各種法律形式、政治形式和意識形態形式。馬克思把整個社會歷史比作一座大廈,經濟基礎歸根到底決定上層建筑,但它只是最后的決定因素。由此他斷然否定馬克思和黑格爾思想的聯系,認為馬克思正是通過和黑格爾完全決裂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endprint
阿爾都塞的“斷裂論”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使他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即否定了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和黑格爾的任何思想的繼承關系。他這樣寫道:“在馬克思的概念體系和馬克思前的概念體系之間,不存在繼承關系。我們把這種無繼承的關系、這種理論差別、這種辯證的“飛躍”叫作“認識論斷裂”和“決裂”[6]顯然,阿爾都塞的解釋把馬克思思想和整個傳統完全割裂開來了。因此,阿爾都塞對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解釋也不是合理的。
三、“批判繼承”的關系
“批判繼承論”者認為,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系應當是“批判繼承”的關系,一方面,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整個哲學體系,另一方面,馬克思又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在這一觀點的持有者中,我們來考察柯爾施的觀點。
柯爾施敏銳地意識到了馬克思主義與哲學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須充分闡明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哲學緯度的重要性,闡明馬克思在哲學研究領域中的獨創性和偉大的貢獻;另一方面必須弄清楚馬克思哲學思想的來源,以便對馬克思的理論革命作出準確的評價。柯爾施尖銳地批評了當時資產階級學者和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關系的漠視。他指出:“實際上,正是許多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上去非常正統地遵循導師的教導,然而卻以同樣隨意的方式對待黑格爾哲學,甚至整個哲學。舉例來說,梅林不止一次簡單地描述過他自己關于哲學問題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即導師們(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的前提就是對一切哲學幻想的拒斥。”[7] 在柯爾施看來,像梅林這樣的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著作中的哲學思想幾乎完全缺乏準確的理解和認識。而柯爾施卻看到馬克思主義與哲學關系的重要性,在他的晚期著作《卡爾·馬克思》中專門討論過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批評繼承關系,但是他和梅林一樣,未能超越“倒立著的”和“倒過來”的比喻。柯爾施還指出,馬克思不光顛倒了黑格爾理論的結構,甚至還顛倒了他關于發展的理論:“在馬克思那里,黑格爾的“發展”概念也經歷了“倒立過來”的同樣的過程。馬克思以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發展基礎上的社會現實的歷史發展取代了黑格爾的“觀念”的超時間的發展。”[8] 在柯爾施看來,馬克思和黑格爾在許多哲學觀念上存在著相似性,而“批判繼承”的關鍵只在于馬克思倒轉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立場:“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的模式中明確無誤地顯現出來的,是在變化了的現實層次的結構中黑格爾和馬克思之間的差別和對立,而在馬克思的關于物質生產力的真正發展和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所說的概念“概念”發展之間,在對黑格爾的模式做了唯物主義的倒轉之后,仍然存在著許多類似性。”[9]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到,柯爾施率先意識到并提出的如此重大的一個問題,即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問題,尤其是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關系問題,但是卻沒有在他那里結出果實來,這無疑是個遺憾。
綜上所述,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系是“批判繼承”的關系,應該堅持用辯證的方法來理解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強調馬克思對黑格爾思想不同方面或見解既有批判和清理,又有繼承和弘揚。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在具體的分析和闡釋活動中,能準確地區分馬克思所批判或拋棄的黑格爾思想中的糟粕和馬克思所保留或繼承的黑格爾思想中的精華,在這個方面,我們還需要努力。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477.
[2]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3]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he MIT Press,1971,p.27.
[4]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he MIT Press,1971,p.xxx-vi.
[5] 拙文.科學·哲學·意識形態—阿爾都塞唯科學論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論題述評[J].江漢論壇,1996,(9).
[6] 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69-261.
[7] Karl Korsch,Marxism and Philosophy,New York and Lendon:NLB,1970,p.31.
[8] Karl Korsch,Karl Marx,Hamburg: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81,S.160.
[9] Karl Korsch,Karl Marx,Hamburg: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81,S.161.
[責任編輯 吳高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