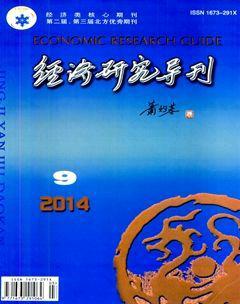產業升級:實踐選擇與理論認識
凌寧
摘 要:三十年來,產業升級一直是中國各級政府努力推動,又成效不甚顯著的工作。這一過程中,有一些理論認識問題需要解決,核心是產業升級內在規律是什么。圍繞這一問題,從產業升級的實際經驗及理論認識兩方面展開討論,以期尋求中國在產業升級中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選擇。
關鍵詞:產業升級;結構調整;經濟改革;企業創新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9-0044-02
一、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的演變
20世紀末,美國各界籠罩著一股憂慮情緒,對美國高科技產業的主導地位的前景感到非常擔心。原因是在全球一體化、新興國家崛起背景下,海外研發、制造業的競爭力迅速提升,美國出現了科技人才、研發活動外流的現象。這些年的情況表明,這種憂慮得到了部分驗證。全球高科技產業格局確實出現了一些變化,但是也有一些沒有改變。變化的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一些傳統領域和地位開始受到挑戰,主導地位在被弱化;沒有改變的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基礎仍然雄厚,其地位并沒有受到根本動搖。
在計算機、軟件產業,全球計算機產業的格局是,計算機部件(概念設計和產品規劃)的研發活動集中在美國、日本;計算機應用研發及新平臺開發(尤其筆記本)集中在臺灣;成熟產品(臺式計算機)開發及主要制造及維護活動在中國。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仍占據產業的高端位置。目前,雖然全球這個產業的創新活動很活躍,但是基本仍然在美國微軟、英特的框架內開展。軟件業產業的基本格局是:美國在軟件包、軟件服務中占據主導地位,但是有逐步下降的趨勢。軟件服務提供商主要在印度,軟件邏輯、布局及開發主要在愛爾蘭,產品開發及研發在以色列。但是,目前創新性軟件開發活動(以專利衡量)仍然集中在美國。
在制藥及生物技術產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制藥產業的研發投資出現外流現象,主要流向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生物技術興起、國外同業競爭加劇,產業創新活動(研發投資和專利衡量)開始活躍。美國、歐洲和日本是這些創新活動主要源發地。隨著中國、印度等國家科技工程能力增強,以及產業組織垂直專業化的深化,創新活動也開始向這些地區擴散。這種擴散主要集中在制造過程、診斷試驗管理領域。目前的制藥業研發活動的擴散與20世紀90年代軟件業的情況類似。但是迄今為止,在全球制藥產業的研發、創新活動中,美國公司仍然占主導地位,標志是研發投資規模,市場吸引力在全球居首位。生物技術產業的基本格局:產業涵蓋生物醫藥、工業制造、農業生物技術諸領域,生物醫藥是主導產業。產業分布以美國及西歐國家為主。
二、對產業格局演變的實踐總結
在全球經濟格局巨變,美國高科技產業遭受前所未有挑戰的情況下,是什么因素導致美國的產業地位得以維持,甚至繼續引領全球產業升級的方向呢?美國政策部門對其中的“變與不變”進行了分析。他們指出,“變化”來自四個方面,首先是海外創新能力提高,表現在:(1)新產品設計及開發能力提高;(2)科技及工程技術人員數量增加;(3)制造業(如汽車、計算機等)在全球市場地位凸顯;(4)若干研發中心(如班加羅爾、上海、新竹)影響提升。其次是海外制造業擴張。這些擴張有些由美國公司主導,更多則是當地自主研發的結果。前者體現在生物、半導體等行業,后者體現在汽車、計算機等行業,尤其在中國、臺灣、韓國地區。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客觀上都帶動了這些行業在當地的發展。第三是海外高科技產品需求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在東亞地區最為顯著,表現在消費需求范圍擴大和成熟度提高。最明顯的是軟件、半導體和計算機產業產品,其中一些產品的需求市場已經超過美國,甚至有更高級的特點。第四是產業組織的創新。最突出的是垂直專業化的擴大和深化帶來更多的聯系和機會。“不變”的是導致美國競爭力的基礎仍然穩固,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21世紀后,在全球高度一體化下,一國產業的格局及走向,需要在全球視野下進行觀察和評價。因為一國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不僅是國內軟硬件實力的綜合反映,也是各國間綜合實力對比的體現。所以,體現在產業上的水平和提升,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軟實力的綜合配合。
三、產業格局及其走向的理論解釋
那么,一國的產業是如何走向高端的?又是如何保持持續的升級能力的?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此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什么是產業升級、產業升級的路徑是什么、如何衡量產業升級的進程。第一個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內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Porter、Gereffi、Humphrey等。Porter(1990)認為產業升級是一種要素轉移,使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獲得充裕的資源稟賦,依托比較優勢發展的過程。Gereffi(1998)將產業升級定義為,企業向高利潤或資本、技術密集型實體發展的過程,并總結了升級的四種形式:產品從簡單向復雜的轉化;經濟活動從貼牌、自主品牌向自主設計方向的發展;產品高附加價值化,以及供應鏈前后聯系的加強;企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變化。在此基礎上,Humphrey(2004)從企業的生產流程、產品、在價值鏈中的功能、價值鏈上各部門關系四個角度提出了企業升級的不同方式。第二個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路徑。這方面研究大多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討升級的動力、驅動因素、機制機理等內容。代表人物有Gereffi、Pipkin、Lall、Pickles et al 等。這些學者從企業和制度層面開展研究。在企業層面,Gereffi(1999)研究提出了影響企業從而產業升級的三個因素:主導企業的學習效應;社會需求的驅動效應;有勝劣汰的擠出效應。Pipkin(2008)提出企業信譽、經營穩定、制造能力是升級的三個前提條件;而國際貿易條件、教育、社會體制是升級的三個要素。在制度層面,Lall(1994)指出產業升級依賴于政府目標,以及為產業及企業制定的扶持和管制政策。Pickles et al等學者通過對歐洲、北美和南亞等國的研究,也看到了體制結構、政策環境對產業升級的意義。第三問題涉及產業升級的衡量。這項研究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指標及指標體系,確定產業升級的位置或水平、及預測未來的升級趨向。Kaplinks(2005)等提出產品指數的概念,以此來衡量產業升級。公式為:PUQ(產品升級指數)= dp%X(X部門產品價格變化與價格平均變化的偏離率)+ MSX(X部門市場份額的變化率)。若兩個變化率同時上升,則表示產業處于升級中。有的研究從產業結構的角度出發,有代表性是Hoffmann(1931)系數,錢納里和賽爾昆(1975)的產業結構模式。endprint
歸納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幾點:首先,產業升級需要一個非常復雜的支撐系統。這個系統需要具備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的諸多良性互動的因素。這些因素的核心是制度,其功能是為產業升級提供土壤或環境。在這種土壤或環境中,會形成一系列文化和法則的力量,自然衍生出無數的經濟體及其行為,以及這些經濟體和行為的自我優化過程。由此,行業、產業不斷優化、升級。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升級需要從上而下的拉動。其次,企業始終是產業升級的核心,因為企業始升級的行動者。產業由眾多的經濟體或企業組成。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勇于、樂于向產業高端挺進的時候,該產業也就處于不斷升級中。而企業向產業高端挺進過程及結果,實際是企業尋求自我生存、發展,走向成功的復產品。所以,這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產業”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業升級又是自下而上推動的結果。第三,在全球產業升級過程中,沒有各國普遍適用的統一的模式。這是由各國的歷史,尤其是文化淵源不同造成的。但是,這并不是說在產業升級中,可以隨心所欲,沒有需要遵循的普遍規律和規則。綜合各國實踐可以看到,市場體系是共同需要的東西。在市場體系越成熟的地方,產業的位置越高,產業升級越容易見效;在市場體系不完善的地方,產業大多處于較低位置,產業升級也難以奏效。
四、中國產業升級理論的再認識,實踐再檢討
三十年前中國啟動了改革進程。在這一進程指引下,中國經濟創造了全球持續高增長的奇跡,但是與之對應,產業升級卻沒有相應的輝煌,甚至出現舉步維艱狀況。目前,無論從附加值、技術水平、創新力、競爭力等指標的變化看;還是從中國相關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變化看,目前中國產業在絕對和相對水平上都仍然處在較低水平。經濟增速和產業升級的這種不協調與多重因素有關,一個基本因素是我們在理論研究乃至政策實踐方面有嚴重誤區。理論認識上表現為將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混為一談;政策實踐中表現為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忽視產業升級,以結構調整替代產業升級。理論上,產業升級一般被認為有兩個特征:一個是產業由低技術、低附加值狀態向高技術、高附加值狀態的演變。另一個是社會需求變遷始終是主線,產業只是圍繞其前后演變,隨之逐步升級。產業升級本質上是以某一個行業作為研究對象,考察各行業演變所導致的整個產業的演變。產業結構升級則通常是一個產業內的行業構成的變化。通過行業構成變化,行業相互關聯性得到均衡和優化,實現資源配置、使用效率的提升。在結構變化中,行業自身的特質,如技術水平、附加價值也會隨著產業結構的改善而提升。實踐上,這兩個概念業的根本區別。以鋼鐵行業為例,產業升級是通過對軟硬件環境的改造,推動鋼鐵行業不斷提升技術水平、附加價值,適應外部需求的變化,走上新的發展階段。所以,升級過程是行業苦練內功的過程,以行業內在素質的提升帶動產業的升級。而產業結構升級在當下較為流行的做法往往是產業結構調整。這種結構調整的典型就是“騰籠換鳥”,也就是將落后行業替換出去,植入有高技術、高附加值行業,形成靚麗的產業結構。由此可見,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功能不同,兩者并沒有優劣之分,只是不應相互混淆和替代。產業升級更多是一個微觀、市場概念,是一個自下而上傳遞,需要適宜市場及政策環境才能生長的過程。試圖用產業結構調整替代產業升級,試圖用行政的力量替代企業的力量,乃至在產業升級上面臨困境,本質上是因為在推進市場化改革不徹底,而造成的無奈選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