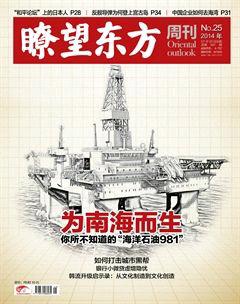中國當代藝術:抄襲,還是學習
魯剛
有關中國當代藝術“抄襲”的抨擊曾經非常流行,這種觀點認為,以F4(張曉剛、王廣義、方力鈞和岳敏君)為代表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創作上以政治題材為主,技法模仿(嚴厲一點稱之“抄襲”)了西方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表現主義或波普藝術的手法,作品形態丑陋、夸張甚至血腥,觀念上以審丑和解構為目標。有的藝術家后期更是不斷重復自己,沒有表現出超越自我的藝術追求和創新精神。
其中不乏一些指名道姓的質疑。如稱張曉剛的《大家庭》肖像讓人想起比利時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雷內·瑪格利特;王廣義的政治波普系列明顯來自于美國波普藝術鼻祖安迪·沃霍爾的創意;張桓的綜合材料、蔡國強的煙火作品中可以找到德國新表現主義畫家安塞姆·基弗的影子;劉小東的畫則模仿了被譽為英國當代最偉大畫家的盧西安·弗洛伊德,等等。
中國當代藝術的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不堪?
與古典藝術相比,當代藝術的創作手法確實比較容易被復制。但手法的借鑒是否就是抄襲?其次,有些關于抄襲的指責,也許放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下去認識,才會得出更為合理的看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美院教學體系仍然模仿蘇聯,以蘇聯馬克西莫夫油畫體系為代表的現實主義一統天下。但當時受西方當代藝術體系影響的一批藝術家,已經意識到一種全新的藝術創作的可能。他們對西方藝術的學習是從模仿開始的。這種模仿,在當時是一種必要的學習。
我們可以指責那一批畫家在技法上模仿甚至抄襲了西方大師,但不能否定他們為了突破歷史堅冰所進行的探索和藝術勇氣。譬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代抽象畫的代表,丁乙幾十年如一日地畫《十示》系列,似乎并沒有什么創新,但他的價值在于重新接上曾被中斷的中國抽象畫派的血脈。應該說,許多像他一樣的藝術家對待藝術創作的態度是真誠的。
值得警惕的是另外一種現象。在創作環境已經寬松許多,資訊共享日益發達的今天,有些藝術家為了迎合資本的需要,不斷進行著重復性的制作。漫步今天的當代藝術展覽,仍然可以看到不少以簡單的拼貼(不同背景元素的拼貼,組合成另外一件作品)和語言轉換(比如將文字轉換為二維碼)為創作手法的作品,一些社會批判性的作品也失之于簡單化。
這種藝術創作手法的陳舊和單一造成的不僅是資源的浪費,也制造了藝術品市場的泡沫。這種模仿,不是突破,而是一種因襲,一種惰性,這才是需要反思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