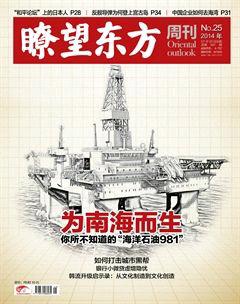葉嘉瑩:詩(shī)詞可使人心不死
鄭秋軼
南開(kāi)大學(xué)西南村。葉嘉瑩的家位于一棟普通的家屬樓里。客廳的三排書(shū)架,放滿了《全清詞》、《全宋詞》等書(shū);恩師顧隨和弟子們的合影置于正中,彼時(shí),葉嘉瑩著淺色長(zhǎng)衫,梳兩條短小的發(fā)辮。墻上一塊匾,上書(shū)“迦陵”,那是她的號(hào);旁邊一幅《班昭續(xù)固圖》,是畫(huà)家范曾為其八十壽辰所作。
多年來(lái),這間略顯狹小的客廳,還兼作教室。葉嘉瑩在此給研究生上課。一些幾十年前聽(tīng)過(guò)她課的學(xué)生,后來(lái)又不斷出現(xiàn)在這里。他們說(shuō),這叫“鐵打的營(yíng)盤鐵打的兵”。最近兩年,因?yàn)槟晔聺u高,葉嘉瑩才跟學(xué)校說(shuō)不帶研究生了。
從1945年至今,葉嘉瑩執(zhí)教近70年,教過(guò)的學(xué)生無(wú)數(shù)。他們對(duì)葉先生講課的評(píng)價(jià)幾乎一致是“如沐春風(fēng)”。
2009年,席慕蓉在臺(tái)北聽(tīng)葉嘉瑩講辛棄疾。當(dāng)講到《水龍吟》最后幾句“問(wèn)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yáng)纜”時(shí),席慕蓉幾乎驚叫起來(lái),她已不知不覺(jué)進(jìn)入了辛棄疾的蒼涼人生。
席慕蓉一直在想“何以致此?”后來(lái),她在《心靈的饗宴》寫(xiě)道:“葉老師在臺(tái)上像一個(gè)發(fā)光體,人和話語(yǔ)合而為一。她就是‘要眇宜修的那位湘水女神。她的衣著,她的笑容,她的聲音,是一種出塵秀雅的女性之美。”
葉嘉瑩說(shuō)她天生是吃教書(shū)這碗飯的。跟老師顧隨一樣,她上課也喜歡“跑野馬”。比如她講溫庭筠的詞,“懶起畫(huà)蛾眉”。通過(guò)各種典故,詳解了“懶起”和“蛾眉”之后,在聽(tīng)者思緒脫韁之際,她話鋒一轉(zhuǎn),又把你拉了回來(lái)。
今年,葉嘉瑩90歲,但根本不像90歲的人。4月,她剛?cè)ケ本﹨⒓恿藘蓤?chǎng)活動(dòng);88歲時(shí),仍在開(kāi)車;每晚2:30睡覺(jué),早上6:30起床。有人問(wèn)她有什么養(yǎng)生秘訣?她說(shuō),詩(shī)詞就是我養(yǎng)生的秘訣。也許,還應(yīng)該加上一份豁達(dá)。
曾有記者問(wèn)她:“聽(tīng)說(shuō)你的愛(ài)情比較缺失?”葉嘉瑩爽快回答:“啊,愛(ài)情,你說(shuō)得一語(yǔ)中的!也沒(méi)什么遺憾的。我說(shuō)過(guò)‘采之欲遺誰(shuí),所思云鶴侶。所以一個(gè)學(xué)生說(shuō),老師你沒(méi)有找到對(duì)象是不是?我說(shuō)對(duì)了,我沒(méi)有找到可以跟我應(yīng)和的對(duì)象。”
“師尊”拈花,“迦陵”微笑
1924年,葉嘉瑩出生在北平,自小受到嚴(yán)格的詩(shī)教。父親教她認(rèn)字、背唐詩(shī),讀的第一本書(shū)就是《論語(yǔ)》。“現(xiàn)在很多人認(rèn)為,小孩子不懂這些。但是小孩子腦筋好,從小誦讀一些古典的精華,可以終生受用。”
伯父是她詩(shī)詞的啟蒙老師。見(jiàn)葉嘉瑩少有慧根,格外歡喜。后來(lái),葉嘉瑩南下結(jié)婚,伯父十分不舍,作詩(shī):“有女慧而文,聊以慰遲暮。明珠今我攘,涸轍余枯鮒。”
在輔仁大學(xué)國(guó)文系,葉嘉瑩遇到了一生至關(guān)重要的人:文史大家顧隨(號(hào)苦水)。顧隨學(xué)養(yǎng)深厚,講課也相當(dāng)精彩。“顧先生講課喜歡上天入地,注重詩(shī)歌的興發(fā)感動(dòng)。”葉嘉瑩還記得顧先生講“夕陽(yáng)無(wú)限好,只是近黃昏”兩句,他說(shuō),這就如同說(shuō)“吃飽了不餓”,但實(shí)在是好。
許多同學(xué)覺(jué)得老師講得好,只顧聽(tīng)得高興,而葉嘉瑩不僅認(rèn)真聽(tīng)了,還把老師所講全部記錄下來(lái)。“實(shí)在可以這么說(shuō),顧先生教的不止我們一個(gè)班,也不止教過(guò)一個(gè)學(xué)校,只有我心追手寫(xiě),埋頭做筆記。沒(méi)有一個(gè)人像我這么完整地記下來(lái)的。”她對(duì)《瞭望東方周刊》說(shuō)。
顧隨對(duì)這個(gè)女弟子也非常滿意,常認(rèn)真評(píng)改葉嘉瑩的習(xí)作。一次,顧隨看了葉嘉瑩填的幾首詞,批道:“作詩(shī)是詩(shī),填詞是詞,譜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當(dāng)善自護(hù)持。勉之,勉之。”
1948年3月,葉嘉瑩赴南京結(jié)婚,不久又渡海赴臺(tái)灣。“一路奔走中,很多東西都掉了,但是我知道老師的筆記是宇宙間唯一一本。老師講課這么好,如果我不保存好就失去了這個(gè)寶藏。”70年代末,葉嘉瑩回國(guó),把顧隨講課筆記交給他女兒整理,在《顧隨文集》中出版。
葉嘉瑩大學(xué)畢業(yè)后,曾收到顧隨給她寫(xiě)的一封信。葉嘉瑩從書(shū)櫥中找出信,對(duì)本刊記者念道:“年來(lái)足下聽(tīng)不佞講文最勤,所得亦最多。假使苦水有法可傳,足下已盡得之。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別有開(kāi)發(fā),能自建樹(shù),成為南岳下之馬祖,而不愿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
顧隨是把葉嘉瑩當(dāng)“傳法弟子”看待的。葉嘉瑩南下時(shí),只帶了一些隨身衣物和顧隨講課筆記,以為很快會(huì)回來(lái),沒(méi)想到一去三十年,與大陸失去了聯(lián)系。“文革”后期,終于有機(jī)會(huì)回來(lái)。那時(shí)葉嘉瑩已蜚聲海外,但當(dāng)她匆匆趕回來(lái)時(shí),伯父和恩師早已不在。
轉(zhuǎn)蓬萬(wàn)里傳詩(shī)音
1948年11月,葉嘉瑩和在海軍供職的丈夫輾轉(zhuǎn)到了臺(tái)灣,很快在彰化女中找到教職。次年8月,大女兒出生。
1949年前后,臺(tái)灣“白色恐怖”時(shí)期,很多人被懷疑為“匪諜”。1949年年底,葉嘉瑩丈夫被抓走。不久,她和幾位老師,連同校長(zhǎng)也被抓去審問(wèn),有多位老師被送去了臺(tái)北警備司令部。葉嘉瑩雖然沒(méi)被送去臺(tái)北關(guān)押,卻失去了工作和宿舍。
此后,葉嘉瑩寄居在親戚家。晚上睡在客廳走廊上,別人午休時(shí)只得抱著孩子在樹(shù)蔭下徘徊。后來(lái)搬出親戚家遷入臺(tái)南一處住所。那時(shí)期,她寫(xiě)的詩(shī)充滿悲苦和憂傷:“轉(zhuǎn)蓬辭故土,離亂斷鄉(xiāng)根。已嘆身無(wú)托,翻驚禍有門。覆盆天莫問(wèn),落井世誰(shuí)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
幾年后,丈夫被放了出來(lái)。葉嘉瑩和家人去到臺(tái)北。不久,臺(tái)灣大學(xué)、輔仁大學(xué)請(qǐng)她去任課,那時(shí)她已經(jīng)兼了淡江大學(xué)的課。白天三所大學(xué),晚上還有夜間部和電臺(tái),非常辛苦,但她一上講臺(tái)就神采飛揚(yáng)。葉嘉瑩的外甥、臺(tái)灣長(zhǎng)庚大學(xué)校長(zhǎng)包家駒回憶:“舅媽平時(shí)在家就刷鍋?zhàn)鲲垼瑤铝耍炱鹦渥哟鱾€(gè)手套就去清理。”
此時(shí)的葉嘉瑩,生活開(kāi)始安定,少了一些悲愁,也逐漸由一個(gè)教師向?qū)W者轉(zhuǎn)變。
1966年是葉嘉瑩的轉(zhuǎn)折之年。葉嘉瑩被邀請(qǐng)赴美講學(xué)。哈佛大學(xué)遠(yuǎn)東系的海陶瑋教授正研究陶淵明,也邀請(qǐng)她到哈佛研究講學(xué),成就了一段合作著述的佳話。
1969年,葉嘉瑩46歲,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xué)任教,她和家人也定居于溫哥華。最大的問(wèn)題是語(yǔ)言,她要用英語(yǔ)向西方學(xué)子講述中國(guó)詩(shī)詞。每晚做完家務(wù),不得不查字典到凌晨?jī)扇c(diǎn)。
“修辭立其誠(chéng)。盡管我英文不好,但是我很真誠(chéng)地告訴他們我的感動(dòng)。”或許情感是不需要翻譯的,選課的學(xué)生越來(lái)越多。葉嘉瑩講《周易》,一個(gè)洋學(xué)生聽(tīng)了,每天回去算一卦,第二天又來(lái)聽(tīng)。endprint
但是,用英語(yǔ)講中國(guó)詩(shī)歌畢竟只能蜻蜓點(diǎn)水。葉嘉瑩時(shí)時(shí)被這種“束縛感”困擾。1970年,她寫(xiě)了一首絕句,表達(dá)了這種苦悶:“鵬飛誰(shuí)與話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馀生。”
誰(shuí)知散木有鄉(xiāng)根
1977年,葉嘉瑩回大陸旅行,沿途見(jiàn)有人讀唐詩(shī),導(dǎo)游也能背誦名篇佳句,她大為驚喜,慷慨賦詩(shī):“構(gòu)廈多材豈待論,誰(shuí)知散木有鄉(xiāng)根。書(shū)生報(bào)國(guó)成何計(jì),難忘詩(shī)騷李杜魂。”
她覺(jué)得,祖國(guó)的中興之日到了。一回到加拿大,就給國(guó)家教委寫(xiě)信,申請(qǐng)回國(guó)教書(shū)。
那是一個(gè)春日的黃昏,斜暉脈脈,落英繽紛,葉嘉瑩穿過(guò)馬路,把信投進(jìn)了郵筒。“當(dāng)時(shí)的景色喚起我年華老去的警惕,滿林的歸鳥(niǎo)也增加了我的思鄉(xiāng)之情,讓我感到回國(guó)教書(shū)應(yīng)盡快實(shí)現(xiàn)。”
1979年,愿望終于實(shí)現(xiàn)。葉嘉瑩先到北大講課,后來(lái)南開(kāi)的李霽野教授以師輩情誼相邀,于是她到了南開(kāi)。
南開(kāi)校友們都還記得葉嘉瑩第一次講學(xué)的盛況:“文革”剛結(jié)束,學(xué)生們?nèi)琊囁瓶剩旖蛟S多學(xué)校的學(xué)生都趕來(lái)聽(tīng)課。一間可容納300人的教室,臨時(shí)增加的椅子排到了教室門口,葉嘉瑩想進(jìn)教室都很困難,講完了學(xué)生還不愿意走。
時(shí)光流轉(zhuǎn),如今學(xué)子的熱情尤似當(dāng)年。西南石油大學(xué)青年教師陳建軍曾在南開(kāi)求學(xué),葉嘉瑩的講座,他每回必聽(tīng)。“古典詩(shī)詞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有一年回家,跟同學(xué)聊天,我隨口說(shuō)了句‘孤篇壓盛唐,因?yàn)槲也皇强瓢嗟模阉@住了。他問(wèn),哪里學(xué)來(lái)的?我說(shuō),聽(tīng)葉先生的講座啊,不會(huì)作詩(shī)也會(huì)吟。”他對(duì)本刊記者說(shuō)。
葉嘉瑩的學(xué)生,從幼兒園小朋友到耄耋老人都有。近年,她一直倡導(dǎo)“詩(shī)歌吟唱”,還與人合編了兒童古詩(shī)讀本《與古詩(shī)交朋友》。2010年,揚(yáng)州有個(gè)活動(dòng)邀請(qǐng)她,聽(tīng)說(shuō)與“兒童和母語(yǔ)”有關(guān),她推掉幾個(gè)會(huì)議就直奔揚(yáng)州而去。
30年來(lái),葉嘉瑩每年往返于天津和溫哥華之間,其余時(shí)間在世界各地講學(xué)。1997年,她在南開(kāi)大學(xué)創(chuàng)辦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以老師的名號(hào)設(shè)立“駝庵獎(jiǎng)學(xué)金”,如今已頒發(fā)了十七屆。
以前有人問(wèn)她,像這樣飛來(lái)飛去飛不動(dòng)時(shí)有何打算?她答:不行就回加拿大住進(jìn)養(yǎng)老院。
現(xiàn)在,她不用去養(yǎng)老院了。南開(kāi)大學(xué)校內(nèi),數(shù)學(xué)大師陳省身故居旁,一個(gè)500平方米的四合院已經(jīng)封頂,這是海外熱愛(ài)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的友人與南開(kāi)大學(xué)合資為她修建的“迦陵學(xué)舍”。 一生奔走各地,積極推廣古典詩(shī)詞的葉嘉瑩說(shuō),這回終于要有自己的“家”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