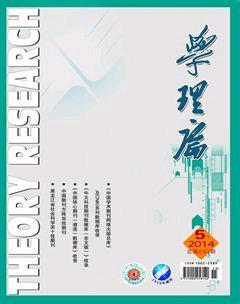從《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坐標系看公平缺失問題
石爍
摘 要:公平是人類社會發展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也是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重要議題。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探討了“克己利他”問題,即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為何會控制其自私利己的沖動,完成利他的實踐。同時,《道德情操論》中也試圖解答“克己利他”行為對于社會道德的構建到底具有怎樣的影響,從而為公平問題的評判提供了重要標準。
關鍵詞: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公平缺失;克己利他;道德哲學
中圖分類號:B5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5-0035-02
一、問題的提出
人,作為連接“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的橋梁,負責著整合世界的工作,是維系“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微妙平衡的關鍵力量。我們不能說道德哲學完全擔當了定義、解釋和說明人與人關系的任務,但人與人關系很大程度上需要道德哲學來概括、解讀和指引。亞當·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任道德哲學教授時必然認識到了這份責任與擔當,所以才會“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理論體系,系統地闡明生存在宇宙中的這個無限而又聯系著的人類活動體系的整個過程,以及人類社會這架大機器的運行機制;揭示作為自然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終極目的、過程和形態”[1]8。《道德情操論》正是亞當·斯密所構想的龐大理論體系的一部分,簡明扼要地說,該書負責“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1]3。更簡單地說,該書就是在定義,解釋和說明一個內容:克己利他。
二、“克己利他”與道德坐標體系
克己不是損己,利他是為了更好地利己。首先,在亞當·斯密看來,利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樣做的話是恰當和正確的”[1]101。其次,因為“對他來說,自己的幸福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幸福重要,但對其他任何一個人來說并不比別人的幸福重要”[1]102,所以,盡管所有人都毫無疑問地奉行著利己主義,但是利己要有限度,“他會發覺,其他人絕不會贊成他的這種偏愛,無論這對他來說如何自然,對別人來說總是顯得過分和放肆”[1]102,這就是所謂的“克己”,就是要“收斂起這種自愛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壓抑到別人能夠贊同的程度”[1]102。不過,亞當·斯密沒有說克己就要犧牲自己,因為這是與人的利己天性相違背的。最后,這樣的克己行為,就使得他人主動贊同個人的利己行為,從而使利己變得更有效率,“他們會遷就這種自愛的傲慢之心,以致允許他比關心別人的幸福更多地關心自己的幸福,更加熱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1]102
在保護社會利益的立場上,亞當·斯密提出了犧牲個人利益,甚至是生命的觀點,“他只是把自己看成是大眾中一個僅僅有義務在任何時候為了大多數人的安全、利益甚至榮譽而去犧牲和貢獻自己生命的人”,“這種犧牲顯得非常正當和合宜”[1]295。可是,犧牲個人利益畢竟與人的利己天性相違背,“雖然人天生是富有同情心的,但是同自己相比,他們對同自己沒有特殊關系的人幾乎不抱有同情”[1]106,這就需要有一種外力保障人們行善,首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必要時能夠犧牲自己利益,保護大多數人利益,因為正如亞當·斯密所言,社會的存在不會因缺少利他行為而消亡,但卻一定會因為人過分的利己而崩潰,所以“有必要利用人們害怕受到懲罰的心理來保障和強制人們行善”[1]106。這個強制力的執行者就是正義,“強迫人們尊奉正義,造物主在人們心中培植起那種惡有惡報的意識以及害怕違反正義就會受到懲罰的心理,它們就像人類聯合的偉大衛士一樣,保護弱者,抑制強暴和懲罰罪犯”[1]106。
至此,亞當·斯密建立了一個道德坐標體系。它的縱軸是“同情”,作為構建道德的必要元素,貫穿道德的各個方面,“被稱作感情的東西,實際上只是一種習慣性的同情”[1]284。對他人行為贊同與不贊同,或者是對合宜性的評價,也就是道德的評判,都源自是否可以同情,正如亞當·斯密所言“我們對行為合宜性的感覺起源于某種我將稱為對行為者的感情和動機表示直接同情的東西”[1]91,同時“我們對行為不合宜性的感覺起源于缺乏某種同情,或者起源于對行為者感情和動機的直接反感”[1]91。這個坐標體系的橫軸是“合宜性”,或者可以稱作“合宜感”,作為把握道德的重要尺度,由亞當·斯密所說的“公正的旁觀者”所掌握。當衡量個人道德水平時,“合宜性”表現為“謹慎”;當衡量社會道德水平時,“合宜性”表現為正義與仁慈。
三、公平缺失是道德缺失的重要誘因
《道德情操論》中亞當·斯密認為,真正值得尊敬的應該是“智慧與美德”,真正需要輕視應該是“罪惡與愚蠢”,而“富裕”與“貧窮”、“有地位”與“軟弱”不能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智慧與美德”或者“罪惡與愚蠢”的標準,也就是說富人和大人物也會具備我們理應輕視的“罪惡與愚蠢”,窮人和小人物也會擁有我們理應尊重的“智慧與美德”。
在亞當·斯密看來,人們的可悲之處在于,他們不關心富人與大人物們是否真的具備“智慧與美德”,而只在乎財富與顯貴,而且“往往是不具偏見的欽佩者和崇拜者”[1]73;可悲之處還在于,“罪惡與愚蠢”對富人與大人物的影響小,對窮人與小人物的影響大,“上流社會人士的放蕩行為遭到的輕視和厭惡比小人物的同樣行動所遭到的小得多”,“后者對有節制的、合乎禮儀的規矩的僅僅一次違犯,同前者對這種規矩的經常的、公開的蔑視相比,通常更加遭人憤恨”[1]73,所以人們更加的欽佩富人與大人物,輕視窮人與小人物。
亞當·斯密認為這樣的道德缺失狀況是可以得到糾正的,因為“取得美德的道路”與“取得財富的道路”對于中低等階層來說,是一致的,并且中低等階層可以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獲得財富美德雙豐收,即“在所有的中等和低等的職業里,真正的、扎實的能力加上謹慎的、正直的、堅定而有節制的行為,大多會取得成功”[1]74;而對于較高階層來說,“取得美德的道路”與“取得財富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追求財富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往美德的道路”[1]76。
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兩個明確的結論。首先,“富裕與顯貴”的人擁有“智慧與美德”的概率更大,而世俗世界辨別外在的“富裕”與“貧窮”、“顯貴”與“軟弱”顯然要比辨別內在的“智慧”與“愚蠢”、“美德”與“罪惡”更為容易,所以同情與尊重“富貴與顯貴”的辦法理所應當地更為有效,這樣的現象也理所應當更為普遍,這顯然不是道德缺失,反而是一種為了正確評判道德而產生的正常現象。其次,想要獲得同情,或者說獲得尊重,最有效的辦法不是作為“貧窮與軟弱”的人獲得同情與尊重,而是作為“富裕與顯貴”的人獲得同情與尊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導致了亞當·斯密意有所指卻沒能闡述明白的“道德缺失”呢?我們不應該強求所有人都能平等對待貧窮與富裕、卑賤與顯貴,因為這么做需要整個社會擁有極高的道德修養。我們真正應該擔心的是公平的缺失,也就是那些沒能獲得足夠尊重的、貧窮卑賤的人們沒有機會躋身于富裕顯貴之列,從而永遠地告別了有尊嚴的生活。假若公平得到充分保證,那么即便眼下貧窮卑賤,也終能通過亞當·斯密所說的“真正的、扎實的能力加上謹慎的、正直的、堅定而有節制的行為”,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變得富裕而有地位,獲得同情與尊重。這樣一來,誰又會對貧窮與卑賤抱有相當大的蔑視,乃至仇恨的態度呢?一句話,公平缺失正是道德缺失的重要誘因。
現實情況是,雖然我國在促進民生、保障公平上已經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中國社會中,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的差距還有相當大的調整空間。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在發展過程中過度強調效率,忽視了公平。為此我們應該完善現有的公平機制,如果封閉了公平的上升渠道,大量的人積壓在社會底層,“智慧與美德”的廣泛普及從何談起?道德的缺失又怎能有效避免?建立有序的、負責任的道德社會應當充分考慮公平的重新構建,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體系中維護社會弱勢群體的正當權益。當個體利益得到社會的容納,具備良好的發展空間時,個體對于他人以及集體做出貢獻的積極性才能夠得到充分釋放,道德秩序便會重新生根發芽。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3]休謨.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