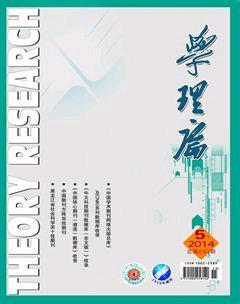實踐范疇的語言哲學分析
燕永奇
摘 要: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觀點。馬克思以后的研究者對其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研究,并提出了自己對于“實踐”的理解。從列寧到西方馬克思主義再到新馬克思主義,即從實踐在認識論范疇內的分析到實踐本體論的產生和完善。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實踐”范疇的轉變,我們該如何把握關于實踐問題討論的發展脈絡?將從語言分析角度對“實踐”觀點的發展做簡單的闡述。
關鍵詞:馬克思;列寧;實踐派;語言哲學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5-0039-02
一、馬克思對實踐范疇的確立
馬克思對于實踐最為經典的論述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他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1]在《手稿》中進一步提出:“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2]在這里,馬克思強調的是理論和實踐的對立。實踐是相對于理論而存在的主體之于客體的一種作用方式,是人類的一種活動,一種在其過程中不斷影響人的活動,一種能夠證明思維真理性的活動。
從馬克思以上觀點中,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闡述實踐問題上時,并沒有給實踐下確切的定義。他只是在闡述思維真理性問題上用到了自己關于實踐的思考。在理論和實踐的對比中確立了實踐的位置。而在下面這句話中馬克思可以說對實踐以類似于定義的格式加以闡述。“……只是從客體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3]在這里,雖然馬克思沒有直接說“實踐是感性的人的活動”,但通過語義理解,“感性的人的活動”作實踐的同位語,即實踐即感性的人的活動。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對于實踐的最確切的定義為:實踐是感性的人的活動。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馬克思在一開始是把實踐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來理解的。但這句話是有歧義的。第一種解釋把“感性的人的”當作一個摹狀詞。即“感性”是對人的限定,“感性的人”是對活動的限定。那么這句話可以簡化為:實踐是人的活動。(因為“感性”是限定人的,在對實踐的定義中,不必要存在。)第二種解釋把“感性的”“人的”當作兩個摹狀詞,是分別對活動作限定。但還有一點需要闡明。“感性的”在先,“人的”在后,順序不可更變。從某種角度說,“感性的”是對“人的活動”的整體描述。即“人的活動”仍有感性理性之分。若顛倒順序,則成為“人的感性的活動”。“活動”直接被限定為感性的了,有曲于原意。
而對于這些理解。以后的大多數馬克思研究者對于其中一點是非常贊同的。他們對馬克思實踐觀的看法都是基于實踐是“活動”的基礎之上的。
二、列寧對實踐范疇的理解
列寧對于實踐的觀點,則是縮小了馬克思實踐概念的范疇。“如果把實踐標準作為認識論的基礎,那么我們就必然得出唯物主義,而人類實踐也不斷證明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正確性。”[4]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列寧是從認識論范疇內討論實踐,他看到了馬克思所說實踐對于思維真理性檢驗的作用。所以,把實踐理解為認識論的基礎。此外,列寧僅僅將實踐理解為“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綜合來看,列寧對于實踐的定義可概括為:實踐是作為認識論基礎的(人的)有目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列寧將實踐的定義細化,使摹狀詞增加。也可以認為他對馬克思對于實踐定義的大膽改動。對于“活動”增加了以下限定詞:“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列寧并沒有對他對于實踐的理解做詳細解釋。但我們可以大致了解這些摹狀詞使實踐定義所產生的新變化。“有目的的”說明這是人的理性活動。“改造世界的”說明活動的目的性“物質活動”則說明了活動的性質。
從馬克思和列寧對實踐的理解來看,他二人都認同:實踐是人的活動。“人的”這一摹狀詞成了二人最基本的對于活動的限定。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和列寧,尤其是馬克思,對實踐的理解是建立在主體基礎上的。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人,就沒有人的活動,也就沒有實踐。
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一元論
在20世紀60年代,以盧卡奇,葛蘭西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于馬克思的觀點有了新的闡釋。盧卡奇認為,“主體只是因為創造了它的客體才認識這個客體,但這個主體不再是個人‘我,而是‘我們,這不是一個已經并且還將存在的主體,而是一個將在創造性過程的結尾出現的主體。”[5]盧卡奇在這里已經開始強調主體創造客體的過程,這里使用“創造”,也說明了他對于客體的理解和列寧的區別。列寧將客體理解為客觀存在物。而盧卡奇開始認為客體是作為主體的創造對象而存在的。沒有主體的創造,就沒有相對于主體的客體存在。這一點也被盧卡奇之后的大部分“實踐派”哲學家認可。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盧卡奇將主體闡述成“是一個將在創造性過程的結尾出現的主體”。也就是說他認為主體是在創造客體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主體的。而所謂的“創造”則可以理解為實踐。因此,盧卡奇已經開始傾向將實踐理解為關鍵,在實踐中主體成為主體,客體成為客體。但仍然沒有明確指出主體,實踐的具體關系。而從語言分析角度,我們只能大致描述出,他對于實踐的理解:實踐是使主體創造主體,主體創造客體的活動。從這里,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盧卡奇已經沒有再堅持“人的”這一對于活動的摹狀詞。這說明了他所闡釋的實踐與馬克思,列寧的有了極大的區別。他把實踐的范疇從“人的活動”擴延到“活動”。也就是說活動的主體已不再局限與人這個范疇內。這一轉變對實踐觀的發展有重大意義。當活動的主體不再僅僅是人的時候。人在實踐中便不再僅僅是主體地位,不再僅僅是創造者,也成了被創造者。正如上文所說“主體是一個將在創造性過程的結尾出現的主體”。盧卡奇已經將實踐從人的附屬位置上抽離出來。這為實踐本體論的提出邁出了第一步。
四、南斯拉夫“實踐派”對實踐本體論的完善
和西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相同。南斯拉夫“實踐派”首先對列寧的觀點進行批判。而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他們對于斯大林也進行批判。此外,我們不得不看到,南斯拉夫“實踐派”的的確確受到了現代西方哲學的影響。尤其是以海德格爾,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這點對了解南斯拉夫“實踐派”觀點的產生意義重大。
南斯拉夫“實踐派”對于實踐的主要觀點如下,“第一,實踐派認為,實踐是人的本質規定,是人的本質存在方式。第二,就實踐本身而言,它作為人的存在的本體論結構,包括了人存在的所有方面,是人的各個活動和各個方面的總體或統一體。第三,實踐也是人的世界的基礎。”[6]從這里,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其關于實踐的觀點是綜合了盧卡奇“總體性”的觀點,以及西馬葛蘭西實踐一元論的觀點。是對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成果的總結和提煉。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實踐派”對于實踐的觀點:對于第一點,說明實踐是人的本質。第二點,說明實踐是人存在的本體論結構。第三點,實踐是使客觀對象化,成為人的世界的根本途徑。當然,“實踐派”仍不否認實踐是一種活動。這一點,他們從未背離馬克思。
五、基于語言哲學的分析
通過以上的闡述和介紹。我們通過”定義式”的分析可以得出馬克思、列寧、盧卡奇及南斯拉夫“實踐派”各自對實踐的理解。
馬克思:實踐是感性的人的活動。
列寧:實踐是作為認識論基礎的(人的)有目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
盧卡奇:實踐是使主體創造主體,主體創造客體的活動。
南斯拉夫“實踐派”:實踐是人的本質,實踐是人存在的本體論結構,實踐是使客觀對象化,成為人的世界的根本途徑。實踐是一種活動。
運用分析哲學中的主詞和謂詞的相關理論,做以下分析。馬克思對于實踐的理解可以用外延理論來說明。在這里,實踐和活動之間可以看作是個體與類的從屬關系。列寧對實踐的理解也可以通過外延理論闡明。但我們通過觀察摹狀詞可以發現。從馬克思到列寧,摹狀詞愈來愈豐富。也就導致外延理論的局限。而內涵理論更適合解釋。即“實踐的內涵是……”而概念的定義正是反映其內涵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概念的定義的完善過程。而南斯拉夫“實踐派”對于實踐的理解則是屬于另一個理論范疇。“實踐是人的本質”從這個命題來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更符合實體屬性理論。即“人的本質”是作為“實踐的屬性”被闡釋的。同樣的“人存在的本體論結構”也可以看作實踐的一個屬性。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實踐派”闡述實踐的方式和馬克思,列寧有很大不同的。而這點正是使得現代實踐本體論和近代馬克思,列寧對于實踐理解不同的語言根源之一。
而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表述差異,原因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看待實踐的角度和馬克思列寧截然不同。正是因為他們將實踐當作本體而不是僅僅當作人的產物來看待。所以必然要改變原來的闡述方式。這一點,在語言分析中的主詞謂詞領域則表現為外延內涵理論向實體屬性理論轉變。
但我們還可以看到另外一點。自始至終,所有對實踐的討論都直接或間接地承認實踐是一種活動。而從語言分析角度來看,活動是有執行主體的。而其執行主體必定是人。因為不論從哪個角度,實踐都離不開人。所以,不論是在主客二元對立下的實踐觀,還是實踐本體論下的實踐觀。人的主體地位是不變的。而所發生變化的是由在主客二元對立下的主體主導實踐到實踐本體論中的實踐創造主體同時主體進行實踐,主體和實踐交互作用。而這可以從主詞和謂詞角度來闡釋。主體和實踐的關系便猶如主詞和謂詞的關系。不是主詞決定謂詞,而是主詞謂詞相互作用,相互建構。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對實踐的研究并沒有使實踐的范疇向其外圍擴延,而是在被限定范圍后,其內涵逐漸細化。也就是說實踐的邊緣是在其內部,在內部逐漸擴大,直到將自身填滿。其次,實踐和主體關系的變化,更進一步說是看待實踐的視角變化促成了“實踐”觀點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3]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C]//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4]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9-100.
[5]徐崇溫.西方馬克思主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85.
[6]衣俊卿.人道主義批判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