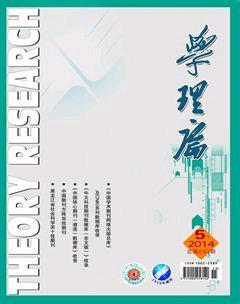王弼和郭象的自然觀的比較研究
王一帆
摘 要:通過對比王弼與郭象在本體論和名教與自然的關系上的異同來比較研究二人的自然觀。王弼哲學上的核心思想“以無為本”是立足于本體論而建立的。而郭象則對本體論進行了消解,認為自然而然才是萬物的本質。在名教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上,王弼主張自然的即是合理的,名教本于自然。而郭象則主張合理的即是自然的,名教出于自然。著重論證了“合理即自然”到“自然即合理”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王弼;郭象;自然觀;本體論;名教
中圖分類號:B2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5-0049-02
中國哲學中的自然觀指的是自然存在,自然本性和自然境界。本文中的自然觀主要涉及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自然世界怎樣產生,涉及宇宙論。二是何為自然,涉及本體論問題。與此同時自然觀還要回答屬于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本性和人的自然屬性的問題。王、郭二人都是魏晉玄學的集大成者。王弼天才卓出,善談明理,晉人何邵為其做傳稱“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王家世代業儒,王弼自幼受儒學的熏陶,這對他創建儒道兼綜的玄學理論有很大的影響。郭象的才學和名氣也很高,據《晉書·郭象傳》記載:他“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時人稱其為“王弼之亞”。二人的自然觀雖不相同甚至對立,但在其對立中有統一的內在聯系,我們能從“自然即合理”向“合理即自然”的理念過渡的同時發現這種聯系。
一、對本體論的發展與消解
王弼和郭象都超越了兩漢的宇宙生成論,王弼立足于本體論建立了“以無為本”的哲學體系,而郭象則宣稱萬物“獨化于玄冥之境”,對本體論進行消解。王弼在《老子注》中,對《老子》的自然觀進行了超越性反思,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自然觀。建立了一個“以無為本”、“崇本息末”、“舉本統末”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崇本以息末”是指排除具體事物對于本體的干擾和影響,以便把握認識本體。“圣人不以言為主,則不韙齊常,不以名為常,則不離其真,不以為事,則不則其性,不以執為制,則不失其原矣。”王弼也將這一觀點運用到政治思想中,“用賢而不尚賢”,就如同燈可照明米可充饑一樣自然而然。“■者易折,皎皎著易污”。“因為不為,損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所謂物極必反,王弼認為只有“以無為本”才能克服具體事物對本體的影響。
《老子》中常出現“自然”一詞,如“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王弼對《老子》中的“自然”是這樣解釋的:“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圓而法圓,于自然無所違也。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也。”(《老子注》二十五章)在對“道”的理解上,《老子》中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可見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道”也常有一種神秘的色彩,例如《老子》中的:“道之為物,為恍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二十一章)“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七十三章)。這里的“道”又具有了一種形上的神秘的力量,人是無法左右的。因此,人們對于《老子》中的“道”帶有一種敬畏的心理,“道”代表封建社會的古典理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老子》中的自然觀念到了王弼這里,發生了本質的轉變,王弼建立了一個全新的自然觀。他首先對《老子》的宇宙論進行了解構。王弼說:“凡有皆始于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老子注》一章)他認為,“無”是宇宙萬物的根本,萬物皆是由“無”而來的。“道”只是指萬物產生于“無形無名”。王弼的“無”,就是這種“無形無名者”,明顯沒有實體的含義。在王弼的宇宙論中,萬物生成之前,并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宇宙本源或最高本體。宇宙的本源或最高本體是一個邏輯前設。“道”實質上也就是“無”,不是一種獨立的存在物。
從根本上來說,宇宙不存在一個實體性的最高本體,沒有超自然的主宰,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才能真正是自然而然的。在王弼的自然觀中,并不存在對于自然力量的崇拜和敬畏的心理,而屬于真正意義的自然而然。對于“若沒有一個超自然的主宰,那么萬物生存的根據是什么”的問題,王弼認為事物的生成和發展,都是按照其自身的規律進行的。他所謂的“自然”就是對事物自身內在規律的肯定。王弼把萬物之中的一種秩序和規律,稱之為事物之“理”,此“理”即“道”。他把他的宇宙論思想推進到本體論的高度,認為萬物皆始于無,這個“無”是萬物生成的本源。對于每一個具體事物來說,“無”不僅是它的生成之源,還是它的根本,即本體。將欲全有,必反于無。但是,“無”也不能離開“有”,王弼的“無”和“有”,既不能在時間上分先后,又不能在空間上分彼此。“無”不是在“有”之先,與“有”相對而存在的某個實體,“無”和“有”是一種本末、體用關系。王弼的本體論是“即體即用”、“體用不二”。
由此可見王弼對《老子》中的自然觀進行了改造,并從簡單的宇宙論思想上升到思辨的本體論高度,他雖然不承認有一個實體性的本體存在,但至少承認是有一個形上本體的,此本體即“無”,也稱為“道”或“自然”,他的自然觀是立足本體論的。
郭象的自然觀思想主要是通過《莊子注》一書表現出來的。《莊子》中也提到了“自然”一詞,如“無為而才自然矣”(《莊子·田子方》),這里“自然”的含義,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意思。然而,哲學上的自然觀,首先與宇宙論和本體論相關。《莊子》認為,創造宇宙萬物的本源是“道”,是非常神秘的。這個“道”只有圣賢才能體悟。
郭象的本體論是一種徹底的“自然主義”。他把《莊子》中作為宇宙萬物本源的“道”,進行了徹底的消解。他說:“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莊子·知北游注》)在郭象看來,“至道者”就是“至無”,就是沒有。“無”中不能生“有”,“有”也不能變成“無”,“無”的意義只是抽象的。“無”就是沒有,“無”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是一種宇宙生成理論中的邏輯符號,也就意味著作為創生宇宙萬物的最高本體不存在。在郭象看來宇宙萬物就是自然而然產生的。“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莊子·齊物論注》)。“自生”就是自然生成之義,萬物自然生成,沒有所謂的造物主。郭象認為宇宙萬物都是自然生長的,即“獨化”。這種自然的生長也不是任意的,無規律的,而是合乎一種“理”的。事物存在有存在的理由,在具體事物的背后,不存在某種神秘的依據。萬物的存在根據,就是一些看起來很簡單的道理。事物的生成、發展、死亡,有它內在的根據,這就是事物的“理”。
二、名教與自然
王弼和郭象的自然觀還突出地表現在社會倫理制度領域。在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王弼主張名教本于自然,郭象則主張名教出于自然。但這僅是提法不同,在這方面二人的觀點不謀而合。
老子認為,與客觀世界相對的一切人為的倫理政治制度都是違反自然的。《老子》抨擊儒家的禮治思想,認為人類的理想社會當是無知無欲的遠古自然社會。而王弼則有不同看法:人類社會不僅需要一種制度和規范,而且理想的制度和規范也是自然的,合理的。也就是說“名教”與“自然”是一致的。在此,“自然”的含義就是合理。王弼由哲學本體論的本末之辯進入到社會生活的名教和自然之辯,不僅是他學術的延伸和發展,也是他的學術目的所在。王弼之所以認為名教與自然是一致的,是因為名教不是人們任意建立的,而是由“道”自然生成的。他說:“樸,真也。真散則百行出,殊類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為之立官長。”(《老子注》二十八章)“樸”即為“道”,“樸”散為“器”,這是“道”的運行法則,是一種自然生成過程。社會倫理制度雖然是人類制定的法則,但王弼認為這是“自然”的。社會倫理制度本來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上的,這就是所說的“名教本于自然”。意思就是合理的社會倫理制度反映的應當是人類最本然的東西。
《莊子》對于儒家的禮制是深惡痛絕的,反對一切人為的東西,任何人類對自然的改造活動都是不合理的,名教是違反自然的。而郭象則對儒家現存的倫理制度持肯定態度,并為之做了合理性的論證。郭象認為,人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自然生成的。人是肉體和精神的結合體,因此,人在肉體和精神兩個方面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人感官享樂的追求應當受到禮的節制。但是,天理和人倫應當是和諧的,仁義禮制也應與自然之性相一致。郭象把人的一些自然本能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要求都看成是自然之“理”。這些要求與儒家的名教并無矛盾,可以說,名教是包含于人的這些自然本能之中的。名教本來就出于自然。無論是圣人還是凡人,只要率性自然,就符合禮儀。這樣,名教與自然就統一了。
三、從“自然即合理”到“合理即自然”
郭象和王弼對以往哲學的超越體現在“理”在“自然”含義中的比重逐漸增大,最終成為主流和決定因素。這是理性思辨的本體論哲學對于魏晉哲學自然觀產生的直接的內在影響。
自然存在物存在的根據到底是什么?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一種哲學自然觀是否成熟的一個標志。王弼和郭象都很明確地承認自然物的存在是符合“理”的。
王弼說:“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則莫不由乎道也。”(《老子注》五十一章)“所由”即是“道”,也即是“理”。可見在王弼看來,自然萬物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萬物以自然為性,故可因而不可為也,可通而不可執也。”(《老子注》二十九章)。王弼把自然物的內在目的看作自然物存在的最后根據。
郭象也持同樣的觀點。郭象提出“自生”論,認為萬物都是自己生成的。“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莊子·齊物論注》)。郭象還認為自然的運動和生滅不是任意的、無規律的,而是合乎一種“理”的。這個“理”就是事物自身內在的目的和規律。自然,就是對于這個“理”的契合。因此,人們對于萬事萬物的認識以及態度,應該遵循這個“理”。
可以看出,從王弼到郭象,二人在論自然的內涵時,“理”的成分逐漸增大,最終認為“合理”即是“自然”,以“合理”取“自然”之意而代之。這標志著魏晉玄學上升到了思辨哲學的高度,是對以往哲學的超越。
參考文獻:
[1]湯一介.郭象與魏晉玄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42-70.
[2]許航生.魏晉玄學史[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77-123.
[3]徐斌.魏晉玄學新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