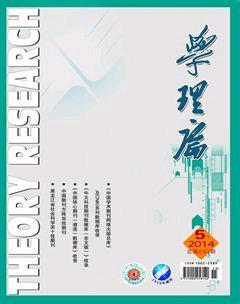淺談《中庸》首章核心概念的英譯
邢玥
摘 要:《中庸》是儒家學說中一部極為重要的經典,探析其核心概念的英譯有助于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表達《中庸》深邃的哲學意蘊。通過對比辜鴻銘和理雅各的《中庸》英譯本,探討首章“性”、“道”、“教”、“中和”四個核心概念的英譯,試圖說明在翻譯典籍時充分理解源語文本文化的重要性,從而進一步促進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
關鍵詞:性;道;教;中和;對比研究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5-0168-02
引言
《中庸》作為一部歷史傳世文獻,是儒家經典中最具哲學意蘊的一篇著作,它上總結先秦儒學,下開啟宋明理學,體現了儒學一脈相承的人文精神,向來成為中國學者的重要論題。它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思是人的本性是上天賦予,本自圓成的;依循本性而處世做事叫作正道;修明循乎本性的正道,是教化的功能[1]。《中庸》第一章是全書的綱領,闡明了“性”、“道”、“教”的內涵和相互關系,把“中和”作為中庸的價值取向。因此,本文選取辜鴻銘和理雅各的《中庸》英譯本,著重探討“性”、“道”、“教”、“中和”四個核心概念的內涵及其英譯,以期更加準確地理解和表達《中庸》的哲學意蘊。
一、“性”的英譯
“生”與“性”同源替用古已有之。“性”通常指代人性,并賦予“天道”等意蘊。先秦時期孟子主張“性善”論,荀子提出“性惡”論,告子主張“生之謂性,性無善惡”。人性問題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爭論的焦點。“性”字在《中庸》里共出現11次,它不僅關系到思想與生命,還關系到天與人。例如:(1)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2)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1]。
在《中庸》的英譯本中,辜鴻銘和理雅各兩個英譯本特色鮮明,辜鴻銘先生將“性”翻譯成the law of our being,moral nature或ourmora lbeing[2]理雅各則將“性”翻譯成nature.[3]很明顯,辜鴻銘的翻譯,重在體現中國的道德文明。事實上,中西方“性”的含義是不相同的。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性”和西方的human nature并不完全對等。“西方的human nature帶有天賦、靜態的品性意味,而中國古代的‘性分先天和后天,是動態、發展、可創造的,是人的本質規定。”[4]因此,《中庸》里的“性”是指人的本性,即便翻譯成human nature,也要理清中西方對其不同的文化詮釋。
二、“道”的英譯
“道”的由來甚古,最早見于金文,其原義是指“道路”,后又被引申為主體所遵循的道理、準則、道德、規律、道義等等。“道”是中國哲學的核心范疇。“道”與“天”聯系,謂之“天道”;與“人”聯系,謂之“人道”。在中國文化中,天道更多地與自然、宇宙相聯系,例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系辭上》)這里“道”作為形而上者體現了存在的統一性,世界千差萬別,不斷變化發展,“道”亦被理解為世界發展的法則。除天道外,“道”還兼指人道。人道表現為人與人的活動,社會組織關系等。它體現在社會文化、政治、道德等各個方面,闡明了人應當“做什么”,“如何做”的問題。
相比較而言,孔子之道,更多側重于“人道”,人倫之道;老子之道,更多側重于“天道”,自然之道。“道”字在《論語》中出現87次,在《道德經》中出現了73次,道家之道與儒家之道旨趣大異。蔡元培在其《中國倫理學史》中說:“老子所謂道,既非儒者之所道,因而其所謂德,亦非儒者之所德。”[5]馮友蘭認為:“古時所謂道,均謂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6]翻譯時如果不注意這些差異,就可能誤解原文內涵而導致誤譯。
“道”在《中庸》里共出現59次,《中庸》從天道、人道和修道三個角度闡述了教育的前提、內容和方法,書中也對“天之道”和“人之道”進行了區分。例如:辜鴻銘將“道”翻譯為the morallaw;前后譯文一致,旨在弘揚中國文化,有效傳達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形象。但“道”在“率性之謂道”中,更多指方法論的問題,即method.理雅各將“道”翻譯為the path.僅取了“道”的表面意思,而忽略了它的內涵,似有不妥。西方也有不少譯者在翻譯中國古典哲學和文化時,將“道”直譯為theWay.Way在語義上似乎過于狹窄,意思也很模糊,表達不出“道”的豐富內涵。由于“道”是一個文化負載詞,翻譯時往往很難在目的語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與之對應的詞匯,可以嘗試用音譯加注的方法翻譯為Dao(道)。
三、“教”的英譯
“教”通常被翻譯為education或teaching.根據《說文》,“教”的意思是“上所施,下所效也。”[7]由于“教”字本身是由“孝”和“文”這兩個部分構成,因此也有“先生施教,弟子是則”的意思。“教”是《中庸》里的又一核心概念。儒家思想一貫重視對百姓的教化,這里的“教”就是教育、教化的意思,傾向于修養和對文化的適應。
辜鴻銘先生將“教”翻譯為religion,與“教化”意思相去甚遠。中國古人所謂的“教化”,其實就是從蒙昧到開化的教育和發展過程,通過教育達到提高人們道德水準、思想修養和文明禮儀的目的。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宗教的意識很模糊,中國也從未形成國教。因此,將“教”翻譯成religion,似乎難以理解。理雅各將“教”譯為instruction,意思與“教化”相近。其實,把握好“教”在《中庸》里的“教化”之意,將其翻譯成education,似乎更為貼切。
四、“中和”的英譯
根據《說文》,“中,正也”。故“中”意為恰到好處,符合一定標準。從字源角度看,“和”有三種意義:一為聲音相和,二為稼禾成熟,三為五味調和。[8]“中和”與“中庸”,都是以“中”為本,“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質。
在《中庸》文本中,“中”字共出現22次,《中庸》首章便解釋了“和”的不斷協調與“中”所提供的這種和諧穩定的關系:“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1]事實上,“和”在早期中國的各種文獻中,就有優雅和諧之意。由于內在能維持不偏不倚的“中”,外在又能事事合于“和”,最終可以達到“中和”的境界。在《中庸》的兩個英譯本中,辜鴻銘先生將“中”翻譯為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理雅各先生將其譯為the state of Equilibrium.相應地,辜鴻銘將“和”譯為the moralorder;理雅各將其譯為the state of Harmony.通過以上對比可以看出,辜鴻銘的道德主線貫穿文章始終,在翻譯核心概念時,他始終強調道德的重要性。理雅各則是從狀態描寫“中”與“和”,雖然比較淺表,但輔以適當的注釋,讀者不難理解“中和”的實質意義。“中和”本身是就“性”而言的,作者子思賦予了“中庸”更深層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恪守“中”道,實現“天命之性”。
五、結語
《中庸》雖然篇幅不長,但其所蘊含的思想豐富。翻譯是原作生命的延續和補充,充分理解源語文本文化是翻譯的前提和根本。辜鴻銘和理雅各的《中庸》英譯本對中國典籍的西傳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辜鴻銘精通中西方語言文學,熟諳中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他所翻譯的儒家經典風格獨特,旨在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理雅各以基督教傳教士身份成為中國文化的傳播者,他的譯筆嚴謹忠實,所譯的儒家經典是近代漢學的開山之作。總之,無論譯者文化身份如何,在進行典籍翻譯時,只有充分理解源語文本文化,才有可能表達出深邃的哲學意蘊。
參考文獻:
[1]王國軒.大學·中庸[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黃興濤.辜鴻銘文集:下[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3]Legge, J.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Ⅰ)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4]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
[5]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8]張貴英,姚丹.晏子與孔子“和”“同”觀之異同[J].陜西教育:高教版,2009(2):72-74.